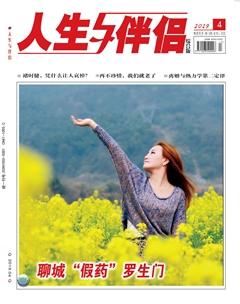褚時健,憑什么讓人哀悼?
周樺 金貽龍
2019年3月5日,原紅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褚橙創始人褚時健于玉溪市人民醫院辭世,享年91歲。
褚時健有許多耳熟能詳的稱謂:亞洲煙草大王、中國橙王、創業教父。他年輕時扛槍打仗,二十出頭就當上地方領導;中年躋身商海,讓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的玉溪卷煙廠一躍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煙草行業的佼佼者、年納稅利超過200億的大企業。
在企業最精彩之時,他鋃鐺入獄,人生歸零;待到走出監獄時,已過古稀之年。按中國人的常理,他應該就此退隱,打發晚年。但他卻拖著病軀與妻子包山種橙,十年后,竟然種植出了中國“最好吃”、“最暢銷”的褚橙。
從農場到糖廠,再從煙廠到果園,他創造了許多商業奇跡,時任萬科董事長的王石曾發文說,“我有很多粉絲,但我是褚時健的粉絲,他是我們這些企業家的驕傲。”
1/任何事上了心,很難做不到
云南,這兩個字幾乎是褚時健名字的前綴。云南人大都“家鄉寶”,安于彩云之南的生活,小富即安,不富也安,少有出門闖蕩的血液和基因。褚時健亦是如此。
除了少年時在昆明讀書的幾年,褚時健的工作生活甚至都沒離開過玉溪地區。但他卻并非世代云南人,他的老祖,也即褚時健父親的祖父,清朝年間從河南到云南服兵役,由此而在玉溪地區的華寧縣和昆明地區宜良縣的交界處扎根下來。
王石見到褚時健第二面時,半開玩笑說:“古代時河南曾經聚居過一支猶太人,您如此擅長商業,會不會是猶太人的后裔?”褚時健笑笑,用云南話說:“怕是不會。”
看褚時健年輕時的照片,高鼻深眼,的確有些異族人的長相,但也有人說,褚時健的母輩或有彝族血統,只是年月長久,從未有人去考證這一家族出處。少年時候,因為父親過世,母親忙于家務和地里的農活,家里的小小酒坊就經常要靠褚時健來操持。這個釀酒坊釀出的酒,承擔了褚時健和弟弟妹妹們的學費和生活費。
褚時健除了上學,把時間基本都花費在了這里。他印象最深是十四五歲時,每年地里收上來七八百斤苞谷(玉米),就要全部用來烤酒換錢。周末放假在家,他必須和母親一起先把苞谷用水泡過,然后再把它們放到甑子(西南地區特有的一種蒸具)里蒸整夜,在此過程中要不斷加柴火,還要幾次攪拌甑子里的苞谷,不然就熄火或者燒煳了。
但褚時健從來未因打瞌睡而燒煳過,每兩個小時,他一定會自己準時醒過來。這一本事,他保留到七十年后的現在,無論多晚入睡,第二天需要幾點起,他的生物鐘一定準時啟動,及時把自己叫醒。
他解釋這一現象為:心里有事。因為燒糊一甑子,自己的學費就沒有了。“其實誰都做得到,就是有沒有責任心的區別。任何事上了心,很難做不到。”他說。
做得到,還要比別人做得好。褚時健的酒在出酒率上也比別人高,即便那些“別人”都是釀酒多年,而且是教會他釀酒的大人們。
一開始,大人們只提醒他發酵時要關上門,也不說為什么。褚時健琢磨是溫度的緣故,因為他觀察到,靠近灶火邊的發酵箱發酵程度總是好一些,酵母菌長得好,出酒率就高。相應的,瓦缸糖化過程也一樣。靠近門邊的瓦缸糖化結果總是沒那么理想,出酒率要比屋里的瓦缸少20%~30%。
幾次下來,褚時健開始用自己的方法,他把灶臺里燒剩下余柴用破鐵盆裝了,放在遠離灶臺的發酵箱下面和門邊的瓦缸邊上,使環境溫度升高。結果,別人家三斤苞谷烤出一斤酒,褚時健只需兩斤苞谷甚至更少。
因為酒的成色也很不錯,拿到市場上很受歡迎,他又留了點心思,每次帶到市場上的酒都不太多,很快就賣完。因此,大家都記住了“褚家老大的酒好喝又好賣”,下次的銷售就一點不操心了。
2/沾手的事情就要做好
如果不是堂哥勸褚時健要多讀書,如果不是因為戰爭讓褚時健接觸到了新興的思想,如果不是因緣際會幫游擊隊劃船渡江而接近了革命隊伍,如果不是戰亂紛擾的年代,褚時健大概就會一直生活在云南省華寧和宜良交界處。
他在1949年初參加革命隊伍,成了一名游擊隊員。一次在云南潞西戰斗激烈時,一個炮彈落到褚時健和戰友中間,戰友瞬間踢走炮彈,緊接著褚時健就聽到了爆炸聲。生死就在一線之間。幾乎就在同一時期,褚時健的一個弟弟被土匪捆綁后扔下大橋,不到18歲的生命慘烈結束。
作為長子帶來的責任感、必須把日子過好的能力、戰火下冶煉的無畏,這些,都形成了褚時健的人生底色。
當進入和平年代,生活平靜了一段時間后,他被打成了“右派”,下放農場勞改。隨后的3年時間里,他在云南大山深處,每天重復著開荒、種菜、養豬、江中撈木柴的生活。突然有一天,農場合并的消息傳來,去哪兒成了一個問題。
當時新平縣的縣委書記普朝拄問他:“縣里的曼蚌糖廠缺個副廠長,這個廠虧得一塌糊涂,你要不要去?”這些年來,褚家幾乎沒有值錢的東西,女兒也到了上小學的年齡,渴望穩定下來,褚時健堅定地說:“去!”
這是一切的開始。
糖廠平時有100多號人,榨季來到時會外招臨時工,但效益極差,每年虧損20多萬元,工資經常發不出來,員工們餓得面黃肌瘦,往往要靠省里的撥款才能維持財政平衡。
褚時健做事很有一套。生產會上,他直截了當地說:“企業注重的是效益,沒有效益做什么企業?技術、機器都不達標,能不虧損嗎?”廠里的技術人員不服氣,“廠里年年虧損,沒有資金,拿什么改造機器?”
褚時健想了一個辦法一一先從改灶和改燃料開始。那段時間,他整日穿著背心短褲在灶邊烤火,觀察生產流程中的每一步。很快他發現,曼蚌糖廠虧損的一大問題是燃料成本太高,他決定用甘蔗渣發酵做燃料。
少年時代的烤酒經驗,讓他想起甜的東西發酵后可以產生酒精,他就和員工把甘蔗渣堆積起來發酵,改變過去“高溫煮——高溫蒸發”的生產方法,把生產白糖的原理引用到紅糖生產中,用于包裝的草紙也變成了光滑的辦公用紙。
創新的效果是顯著的。褚時健當上副廠長的第一年,曼蚌糖廠的產糖率增加了三分之一,產生了八萬的利潤。輕工廳下來檢查時感嘆,“看來你們創造了奇跡!”
在新平嘎灑16年的時光,應該算是褚時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他的兒子褚一斌就出生在這一階段,在繁忙的工作同時,也能盡享家庭的天倫之樂,盡管妻子馬靜芬不時抱怨他工作太忙不管孩子,但轉頭也經常正告女兒和兒子:“要尊重你們的爸爸,他的右派帽子是別人亂扣上去的。”
家里的小日子馬靜芬負責,褚時健則負責工廠里的大生活,生產之外,他也帶著工人們種菜養豬捉魚,在毛澤東“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語錄“保護”下,糖廠職工每周殺一頭豬的殷實生活,著實把全新平嘎灑的人民羨慕了個夠。
褚時健從未對人講過新平糖廠對自己有多重要,也許是后面一段煙草事業的過于輝煌,沖淡了這一段生活的記憶。然而,他在新平糖廠的16年,基本是一場漫長的演練,給他下一段玉溪煙廠的生活奠定了堅實基礎。
這段時光最有價值的是,褚時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定位:企業經營者,他的商業思維,他行事作為的風格,他的成本意識、對產品質量的窮究精神,在糖廠的工作里找到了最踏實的對應點,而且回報甚豐。回憶這段歲月時,他說:“我一直有一種意識,那就是:人活著就要干事情,沾手的事情就要做好。”
3/一代煙王
1979年,褚時健離開新平嘎灑糖廠,前往玉溪煙廠任職。那時,紅塔集團還只是一個建在小山溝里的玉溪卷煙廠,工廠內部分“派”嚴重,生產環境也差,工人上班一身汗,下班一身灰,員工年均收入不到300塊,很多員工一大家人擠在一間十多平米的土坯房里。用他的話說,“整個一爛攤子。”
有過管理工廠的經驗,褚時健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深有體會,他從經營理念到企業內部管理,對玉溪卷煙廠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最引人關注的就是貸款2300萬美元,引進德國的MK 9-5型煙支卷接機。當時許多人都覺得他瘋了,“這么大的數額,你一個人賠得起嗎?”
他把工廠負責一線生產的車間主任都叫到一起,給大家算了一筆賬:MK9-5型煙支卷接機每分鐘卷煙5000支,效率是原來設備的5~6倍,單箱卷煙耗煙葉45公斤,能節省超過15公斤,如果每公斤5元,一箱就節省75元,不到三個月就能把貸款還上,并且收回投資。
在《褚時健新傳》一書中,有人猜測,這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筆設備引進項目了。這次“逆天”行動產生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更多中國人開始吸上濾嘴香煙,70萬箱年產能保證了經濟正在騰飛的中國人在吸煙上的體面追求。
有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玉溪卷煙廠生產的“紅塔山”、“紅梅”、“阿詩瑪”等品牌的香煙,占據了全國市場將近80%的份額,到了1992年,玉溪卷煙廠超過日本煙草公司,成為亞洲第一大煙草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