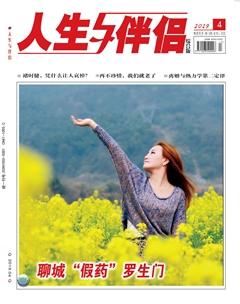進工廠,還是送外賣?
王凱
2015年6月,當20歲的梁多像從老家肇慶農村走出來的時候,“快遞小哥”柴閃閃還沒有當上人大代表,大眾點評還沒有被美團給收購。在街面上,餓了么、美團外賣、百度外賣正處于跑馬圈地的混戰時期。
和很多年輕人一樣,工廠是梁多像第一個落腳點。他在順德一個加工廠做了三年,從普工到拉長(指班長,比組長大)。正在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他選擇了離開。在廣州、清遠、深圳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順德,不過,這一次他做的是外賣騎手。
2019年1月,美團發布了一個《2018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美團外賣騎手的上一份工作,最多的就是去產能行業做產業工人,占比達到31%。
互聯網行業催生的不斷擴大的“零活市場”,正在跟傳統制造工廠伸手搶人。
自由、錢多
倒退二十年,從農村出來的廉價勞動力,只能一批批奔向珠三角、長三角的制造業工廠,締造了中國制造業的輝煌。
離開工廠9個月后,梁多像依然能夠清晰回憶當初在工廠做工時的場景。
2015年剛進工廠時,他被派在生產線的最前端,那是整條生產線上對速度要求最高的一個地方,如果做得慢,就會拖慢后面的速度。很多年輕的新員工都會被安排在那里鍛煉,熬過去了,就能適應后面的工作,熬不過去,就只能另謀出路。
梁多像每天早上7點起床,7點半打卡,工作到11點45分,中間休息1小時45分鐘,再工作到下午6點。實際上,經常會加班到8點。
他所在的工廠是一家A股上市公司,以生產家用小電器為主,員工超過20000人,梁多像就是這20000人之一。他當時在滴漏式咖啡機的生產線上,每天的工作是將塑膠殼夾在咖啡機的鐵片上,鐵片有十幾個孔,需要每個孔對齊,然后再用螺絲刀的刀把捶平整。
拉長要求他們13秒做完一個,但是很多人都完成不了,就延展為20秒做完一個,每天要做800個左右。
他的那個工種是坐著工作的,因此他每天最期盼的是中午在食堂吃飯時能夠站一會兒。
梁多像在工廠打工時,新興的互聯網公司正在催生大批門檻低但收入并不低的工種——開滴滴、送外賣、送快遞、做代駕。
95后,甚至00后們,需要新的打工場域。在記者的采訪中,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凡是離開了工廠的年輕人,就沒有再想著回去。
時間自由,是那些新工種最主要的標簽。無論是騎手,還是司機,都是在為自己打工,外賣、網約車平臺,對他們并沒有太強的約束力。根據美團的報告,離開上一份工作和選擇做騎手,最主要的因素都是時間靈活性。
收入高,是另一個誘惑。多位從業者向記者講述,只要夠勤快,在一二線城市,外賣、快遞小哥的月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滴滴司機的月均收入在7000元以上,代駕的收入在10000元以上。
相對來說,工廠的收入多在3500元~5500元之間。
42歲的易山曾經在一家制造業工廠做過多年技術工人,到了40歲時,工資還在6000元左右。
2017年底,因為創業失敗,他來到東莞“躲清靜”。為了養活自己,他本想去工廠找一份鉗工的工作,那是他最拿手的活兒。但是找來找去,以他的資歷和技術,也只能拿到四五千的工資,同時,還要承擔和20歲出頭的年輕人一樣的工作強度。
如今,在做美團外賣騎手一年后,他每個月到手的工資已經接近1萬元。
不對等的工資收入
流動性大,是新一代打工者的一個顯著特征,對于那些20歲左右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很少能夠在一個地方待上兩年,也很少能夠在一個工廠里待上半年。
24歲的重慶小伙劉勇,變換的工作地點就像在地圖上兜了個大圈。17歲那年,高中讀了一半,他就輟學跑到新疆學修車,短暫回到重慶后,又直奔鄭州的富士康,成為蘋果手機流水線上的一名質檢工人。
沒過多久,475公里外的太原富士康缺人,劉勇就主動申請調動,主要原因是可以獲得一筆還不錯的車補和工資補貼。
2017年,劉勇受夠了富士康那種不自由的工作狀態,就南下到東莞,在一家五金工廠上班。他目睹一位工友在操作沖壓機時受傷,當時那工友在看手機,沒注意到沖壓機壓下來,重重地砸向了他的右手,幸好他躲得快,只把手機給壓碎了,要不右手就廢了。
工作半年后,他離開東莞來到惠州,徹底告別制造業,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事。有一次收貨時,他把一件據說成本價要一萬多元的工業用膠弄丟了,幸虧后來又找到了,但依然被罰了500塊錢。2019年初,他離開惠州,來到廣州,做了外賣騎手。
由于沒有太高門檻,外賣騎手這個新工種正在接納這一批流動打工群體,只要有輛電動車,辦一張健康證,能用手機,會使導航,就可以上崗接單。當然,如果要做專職騎手的話,需要跟一些騎手站點簽署勞務合同。
除了外賣騎手之外,網約車司機、代駕等互聯網催生出來的新工種,也在吸納不少產業工人轉型,甚至也吸引了不少管理者、白領。
42歲的外賣騎手易山曾經是國企員工,還創過業做過老板;在廣州珠江新城做代駕的吳師傅,2002年從廣東藥學院畢業,曾經在世界五百強的外資藥企做醫藥代表,后來做過醫藥批發的生意,2017年開始做代駕;在廣州天河北商場做代駕的鐘師傅,曾經開過肥料廠,2018年年底工廠倒閉后,做了代駕。
“這是市場自由選擇的結果。”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潘毅向記者表示,服務行業能夠提供更高的收入,就會吸引更多的人進來。在過去二十多年,潘毅一直在研究中國的產業工人群體。
根據潘毅的研究,服務業提供的工作崗位已經超過了制造業所能提供的崗位,制造業提供的崗位約占35%,而服務業提供的崗位則有40%。在她看來,制造業如果想要留下更多的人才,可能需要付出更高的工資。
在德國,職業技校畢業的技工們,收入并不比高校畢業生低,但是在中國,這顯然達不到。
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2015年發布的報告《全球制造業的經濟大挪移》稱,從2004年到2014年,中國制造業的年均工資已經持續10年增長率在10%~20%之間,遠超其他經濟體的2%~3%,這也使得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大幅下滑。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說起給工人們漲工資,佛山某家電加工廠的招聘負責人張文杰皺起了眉。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一個工人到手工資是3500元,但是工廠實際上至少要付出5000元,這其中包括450元的餐補、680元的各類保險、免費的宿舍、無法計算出來的培訓費用,未來公司還要為工人辦公積金。
相對來說,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他們所獲得的高工資,主要由消費者來支付,比如,外賣小哥送一單快遞5塊錢,這5塊錢就是消費者叫外賣時所附加的費用。他們的收入再高,對于平臺公司來說,并不會直接造成人工成本的壓力。
缺乏保障的工作
令潘毅擔憂的是,由于這些新工種的從業者很少簽署正規的勞動合同,從業者們更像是個體戶,要自己繳納各種保險,但往往又會選擇不繳,一些本該有的權益很難得到保障。
“以物流行業為例,整個行業的從業人數有七千萬人,快遞小哥只是一部分,還有汽車司機、倉庫人員、客服人員等,新聞里經常會出現一些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的問題,很多人大代表也開始提議,要保護這些群體的正當權益。”潘毅向記者表示。
做騎手這一行,雖然沒有像工廠那樣危險就在眼前,但是騎著一輛電動車穿梭在繁忙的街道上,也有不少潛在的危險。
南京交警部門曾經公布過一些數據,2018年下半年,南京交警共查處外賣騎手交通違法4503起,日均查處25起;而在更早的2017年上半年,涉及外賣送餐電動車各類交通事故3242起,共造成3人死亡,2473人受傷。
梁多像出一次車,要去四五個店里取貨,再送往七八個不同的地點。外賣平臺上給的路線圖,橫穿幾條馬路,比打工時見到的磨具圖還要復雜。
有一次,為了趕時間,在一個沒有紅綠燈的路口,他加大了油門沖了過去,只聽到后面傳來刺耳的剎車聲。等他回過頭來的時候,發現后面一輛紅色的保時捷差點撞上路邊的護欄,車后是長長的黑色剎車印。那一刻,他最怕的是車里下來兩個大漢,把他揍一頓。
在珠江新城做代駕的吳師傅,有一次幫客人開了一臺蘭博基尼,準備開出停車場時,客人提醒他要注意減速帶,盡量側身通過,不然會刮到底盤。當車子開到指定地點時,身上的衣服都濕透了。他回去查了一下,那一款蘭博基尼在整個廣州市只有兩臺,萬一不小心刮了一下,自己可能一輩子都賠不起。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專職的外賣騎手一般與站點簽署簡單的勞務合同,兼職騎手則很少簽署這些合同;網約車司機、代駕,也大多是這種比較松散的管理模式;外賣平臺、網約車平臺與他們的騎手、司機,并沒有緊密的雇傭關系。
當這些騎手、代駕、司機的權益受損,或者出了“工傷”,應該找誰,這還是一個問題。
仍未消失的“光環”
“產業工人轉向服務業”,這并非是一個新課題。2011年,摩根士丹利亞洲主席史蒂芬·羅奇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就曾說過,在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中,傳統產能的退出,將會導致產業工人向服務業轉型。
如今,這些互聯網公司催生出來的服務行業,正在加速這種轉型,中國的產業工人也正在從“工廠挑工人”向“工人選工廠”轉變。
事實上,一些大的制造業工廠已經加大了自動化,用機器來代替人工,從而減少對人工的依賴。但是絕大多數的中小型公司,依然依靠龐大的、流動的勞動群體在維持著生產,他們將繼續面臨著人工成本不斷增加的壓力。
但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的轉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很多中小制造企業還沒有真正感受到切膚之痛。
在記者采訪中,多位工廠老板、招聘負責人并不認為,外賣、快遞這些新的行業在跟他們搶奪工人。
“我們工廠里很多離開的工人,下一站幾乎還是工廠,很少聽說有去送外賣的。”張文杰向記者表示。他的工廠要雇傭七八百名產業工人。
他向記者分析,工廠招募的工人大多是18~45歲之間,其中主力是30~40歲之間,這些人有家室,更喜歡工廠的穩定性。而外賣騎手的年齡在18~28歲之間,這些人正好是工廠里流動性比較大的群體。
“真的有那么高的收入嗎?反正我是不信。”1998年出生的陳銘一臉不屑,他不認為送外賣比在工廠里掙得多。
陳銘所在的工廠,正是梁多像此前打工的地方。他衣著講究,留著很干練的短寸頭,臉上還涂了一層有香味的油。他有自己的規劃,高中畢業的他,希望能夠做管理上的工作。在生產線上工作三個月后,他就轉做行政專員了。
他認為工廠是年輕人步入社會最好的落腳點,一個拖著行李連房租都付不起的年輕人,只要找到一家工廠,就能獲得免費的食堂、宿舍。
陳銘的不相信,并非沒有道理。不是所有的外賣小哥、快遞小哥都能掙到七八千塊錢,新手們、懶惰一點的以及那些做兼職的,很多人到手也就一兩千塊錢。
他自己心里也有一筆賬,如果送外賣一個月6000元,租房子400元,吃飯700元,到手其實也就5000元。而在工廠,管吃管住,還不用風吹日曬,工作時間長了,當上組長甚至拉長,工資就可以達到六千多元。
對于梁多像來說,雖然他再也不想回工廠打工,但在工廠的那三年,卻是他攢錢最多的三年。工廠里,除了工作就是吃飯睡覺,幾乎沒有開銷的地方。
在梁多像老家,在工廠打工依然還是一個很有面子的事情,尤其是在工廠混成一個小領導的時候。
在他當拉長那段時間,老家的叔叔伯伯們有時會給他電話,問他有沒有工作推薦,能不能帶帶自己家的小孩,這讓他覺得很有面子。
易山說服自己安心地做一個外賣騎手的時候,也用了很長時間。剛開始選擇送外賣,主要是想從頭開始,有個臨時賺錢的地方。但是有一次回到老家,朋友們在一起聚餐,當別人知道他是送外賣的時候,他能明顯感覺到并不友好的目光。
即便是收入少一點,但在他的那些朋友們看來,在工廠里做高級技工、做師傅,才是一個更有前途的職業。(應受訪者要求,張文杰、陳銘為化名)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