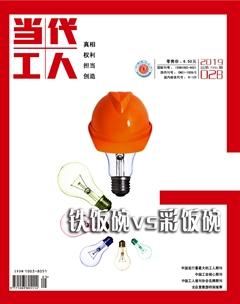最后一公里怎么走
悅納
如果我是讀者,大概不會關心《當代工人》編采人員春節放了幾天假,發行量是否保持行業全國第一……我關注的點會很簡單:這個月的雜志咋還沒來?
作為記者,經常跟著采訪對象下礦井、出海港、進車間。盡管大多數地方我都是第一次去,只要在這些地方看見《當代工人》,我都會有一種親切感。我發現,不論是被翻到皺巴,還是被整齊收好的雜志,當期的很少,大多是一個月前、半年前、一年前的舊雜志。
每次被問道“你們雜志怎么出這么慢”,我都會很尷尬。
編輯按時交了稿,印刷廠一刻沒耽誤,郵局的卡車凌晨時已經在路上……可雜志還是遲到了!唯一的解釋是,我們慢在了送到讀者手上的最后一公里。
它們被堆在廠門口的收發室、單位車庫、工會辦公室。因為沒有人取,所以只能趴在那兒,由新變舊。
我在礦區采訪時聽工友們說,看《當代工人》是他們唯一的消遣方式。我感到驚訝,在這個手機長在身上的時代,一本雜志怎么會是唯一選擇?他們的回答很中肯,礦區里手機沒有信號,尤其是晚上收工之后,住在礦區的臨時房里,就盼著新雜志快點兒來。
我不想辜負讀者的期待,更不想自己原本冒著熱氣的鉛字變冷。可這從礦區門口到班組的最后一段廠路,誰來走呢?
“誰想要,誰來取。”這是收發室大爺最簡單粗暴的解決方法。說實話,有些時候這很有效,雜志會被哄搶而去。不過,它們的歸宿是個人家或是廢品回收站。原本說好的職工福利,被少數人賤賣,雜志社還背上了投遞不到位的鍋。真是冤啊!
出于這個原因,2019年雜志社對一些單位仍采取自辦發行的方式,雇傭專人投遞,用這種方式把從雜志社到讀者的最后一公里連接起來。與此同時,雜志社的電話、微信公眾號都受理訂閱服務,任何投遞問題可以直接留言,我的同事會努力協調解決。
我們不是在做一本只能看不能說的雜志,而是一個互動交流的媒體。如果最后一公里路必定存在,那我們能做的,就是讓它不要成為雜志與讀者心理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