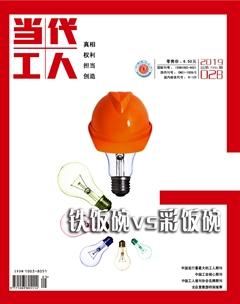當鐵飯碗不值得去盤
于濤
這個春節,李師傅過得很憋氣,大年初一還把電話給摔壞了。
生氣原因和家里無關,是因為徒弟們。52歲的李師傅是遼寧省一家大型國企的數控鏜床高級技師,因為廠內技工短缺,他同時帶了3個徒弟,都是職專畢業的年輕人。李師傅是實誠人,帶徒弟仍沿襲老一輩傳統,不但教技術,還關心孩子們生活,總領著徒弟們聚餐,講人生道理。
到了春節,按傳統徒弟們該給師傅拜年,可大年初一卻不見人影。大徒弟突然來了個電話,拜過年,就和師傅說他已打算辭職,不要國企身份,春節后去江蘇一個民營企業上班。
李師傅心里一涼,但這種事徒弟必然是考慮好了才說,何況對方給的工資高,如何阻攔?李師傅只能委婉地說,可惜了國企培養他兩年多。
大徒弟說:“師傅,我們仨起初也很珍惜國企身份,可總想著還年輕,多賺點兒,何況到那邊直接挑大梁……”
“我們仨”這三個字讓李師傅心頭一驚,問還有誰?徒弟囁嚅著說:“本來是想挨個和您說,我兩個師弟也都去那個企業面試過了,這次,打算一起辭職走,怕您不高興,都不敢說。”
“啪”一聲,李師傅把電話摔在地上,隨即又撿起來,沖著電話大喊:“你們三個混蛋,合著伙騙我是吧!覺得自己本事夠了是吧……”喊半天,才發現電話已經壞了。
他的三個徒弟沒聽到師傅后來的怒吼。春節后,他們整理行裝南下闖蕩屬于自己的世界。只剩李師傅孤零零一個人坐在車間的板凳上。三個徒弟一起跳槽,讓他的身影看起來是那樣孤單。
本來,每年春節后是民企藍領白領跳槽的高峰,根據“國際在線”的調查,每年春節后,農民工藍領中有40%以上選擇跳槽,民企白領普遍選擇在拿到年終獎(春節后)另覓新職位。但從2018年開始,春節后跳槽大軍中越來越多出現國企職工的身影——隨著國企職工年輕化,以及民企對技術工人開出的價碼越來越高,不斷有國企職工放棄曾經珍貴的鐵飯碗走向市場。這其中究竟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說到跳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民企能夠開出更高的薪酬。這似乎確有關系,但在談及薪酬問題之前,我們更需探討一些新的現象——年輕職場人的訴求變化。
這是國有企業不曾關注,但又真實存在的一個問題。在2018年10月舉辦的2019屆高校畢業生秋季招聘會上,由于求職的畢業生多數已是95后,招聘過程中很多新情況讓各家公司的HR都始料不及。例如有大學生求職時,薪酬倒還其次,竟有很多學生詢問公司是否有健身房,是否有下午茶時間,是否給員工充分的拓展團建經費。
很多公司的招聘人員當場被問蒙,憑他們的經驗,不先談錢,不談未來發展空間,怎么先提及這些不靠譜的問題?
他們似乎忘記,“薪酬至上論”是當年80后進入職場時帶來的觀念——在2000年初時,應聘者一般不敢問招聘企業薪酬,或是不好意思問。但隨著80后進入職場應聘,開始大膽問工資,當時的招聘者也不習慣,指責“你們這些年輕人,不談能為企業創造什么價值,先要問企業給你們什么,太過分。”當時的80后則反問:“我們來工作是賺錢,為什么不能問薪酬,問問都不行嗎?”
這件事在當時引發社會爭論,結局自然是新生力量戰勝傳統觀念,時至今日,薪酬、崗位、前途已成為職場招聘中的核心議題。
隨著90后,尤其是95后進入職場,新的職場需求正在被確立。其中的原因也簡單,90后年輕人的父母多數是65后乃至70后,是目前社會的中堅力量,且由于我國經濟多年發展積累,這一父母群體經濟實力明顯強于上一代,能夠為子女提供較為優渥的生活條件。當這些被“富養”長大的90后年輕人進入職場時,并不像80后那樣要面臨買房、供養農村長輩、負擔整個家庭開支的壓力,他們不再薪酬至上也就不難理解。
另外,很多90后年輕人在接受采訪時都表示,他們已經意識到,在同等學歷、能力條件下,獲得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往往意味著更多的勞動付出,比如更多的加班或業績考核壓力,這并不是他們所期望的。相反他們對應聘企業的食宿條件、工作條件、工作壓力、工作氛圍格外看重。用他們的話說,開心是第一位。
面對這種追求“品質”的求職潮流,國有企業顯然準備不充分。一位國有企業人力資源部經理對記者說,目前,除了一些壟斷性國企能夠給予職工優厚的福利之外,絕大多數國企單位(尤其是制造業)的福利待遇都較差,所謂每年一次集體旅游、舒適寬敞的換衣間、星級食堂和值班室,這些都和歷史悠久的制造業國企無緣。尤其是東北的制造業國企,車間廠房陳舊、設施老化,工作環境較差,企業自身又缺乏團隊建設意識,職工文化形式主義,都讓年輕員工產生疏離感。
這種情況不僅僅局限于大學生群體,在廣大的年輕藍領群體中也同樣存在。一位國有礦山機械生產企業人事經理對記者說,“我們企業目前技術工人的平均年齡在45歲左右,年輕人基本斷層了。很多技術學校畢業的年輕人,上班一看環境太差,工作不體面,就找各種理由不來上班了。企業提出辭退,他們也不在乎,有的人干脆直說,寧可換一個收入少但不累的工作,也不要這個所謂的鐵飯碗。”這位人事經理說,他曾和很多同類型國企的人事經理交流,大家都有類似的慨嘆。
年輕求職者關注工作軟硬件環境勝過薪酬,國企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下降,這其實只是國企面臨技術人才流失的諸多原因之一。
“在過去,國企對求職者最大的吸引力不是薪酬,而是穩定,一旦入職,基本不會裁員。”營口市一家船舶設備制造企業人力資源經理說。本來,越是在北方,人們越看重“穩定”二字,如果一邊是月薪3000元的國企崗位,另一邊是月薪5000元的民企崗位,很多東北人會選擇前者,原因恰是國企“穩定”二字的含金量。
但近兩年來頻繁出現的“秒辭”和“裸辭”,投射出人們對工作的衡量發生巨大變化,也預示著人們越來越忽略所謂的穩定。
秒辭,指剛剛上班就立刻提出辭職,甚至上午報到,下午遞交辭呈。裸辭,則是指尚未找到下家,就決然提出辭職,絕不拖泥帶水。這兩種辭職方式并不是只在年輕人當中流行,80后乃至70后跳槽過程中,也開始廣泛出現這種“絕不將就”的態勢。根據前程無憂“2018年第三季度求職跳槽意愿度調查”結果顯示,有54%的受訪者表示,最近一次的辭職是“裸辭”。
說到原因,則在于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社會崗位出現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人們可以同時嘗試多種職業。一名女工可以上班時是流水線上的質檢員,下班后則成為美妝直播網紅,同時還能經營一家化妝品網店。一名開龍門鏜床的高級技師,同時還兼具寵物店合伙人、狗糧代理商的身份。這種“斜杠”人生,使這些“斜杠青年們”不再維系于一種工作。
鄭雨婷今年33歲,剛剛從國企辭職,她并不急于找新工作,只想安靜下來思考一下未來的發展方向。“在國企里做了7年的車間調度員,起初很珍惜這份工作,夢想是一直干到退休。但后來看身邊很多同齡人都離職,有的拜師去學木藝雕刻,有的挑戰自我去做銷售,還有的自己小打小鬧地創業,過得都非常充實。我忽然意識到,時代不同了,我完全可以去做自己喜歡的事直到退休。”
面對這種多元化的發展,國企穩定的金字招牌有些黯然失色。一家國有企業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說,現在企業里有很多人都有第二甚至第三職業,導致對工作的重視程度降低,一言不合就要摔掉鐵飯碗,這既打亂了企業培養職工梯隊的規劃,也給管理帶來很大難題。
一方面是“富養一代”對工作的挑剔,另一方面是國企穩定金字招牌的褪色,讓國有企業的人力儲備倍感艱難。當談及薪酬、發展空間這一傳統話題,似乎更有些讓國企人才加速流失的意味。
根據智聯招聘發布2018年跳槽指數調研報告顯示,40%以上的跳槽者是因為對薪酬不滿,另外有超過20%跳槽者是因為對企業發展前景或個人發展前景感到擔憂。
在制造業領域,同一個技術崗位,國企能夠提供的薪酬與民企之間的差距正在越來越大。一個典型的案例來自東北一家國企的一位優秀焊工,這位姓梁的技師在氬弧焊、埋弧焊的數控編程方面具有極強的能力。他在國企每個月收入約4000元,而福建一家同行業民營企業給出的薪酬則高達1.5萬元,衡量再三之后,37歲的他選擇離開國企,去民營企業闖蕩。而像李師傅的三位徒弟,不僅僅是因為跳槽到民企薪酬翻倍,更因為可以成為各自工作組的領頭人,快速成為車間頂梁柱。
實際上,在這一輪經濟下行和產業結構調整之前,國有企業的技術人才并未出現明顯的流失狀況,國企始終是多數求職者首選的目標。根據前程無憂發布的《離職與薪酬調研報告》,國企技術人才流失、離職率上升的拐點出現在2016年。當經濟下行壓力呈現之后,非壟斷國企中的制造業企業、服務業企業盈利能力均出現明顯下滑,職工薪酬增長速度低于優質民企,繼而才讓國企技術人才流失的勢頭有所上揚。而前文提及的新生代求職者需求異化、社會發展弱化單一職業等因素又成為疊加因素,進一步加劇國企技術人才的流失。
人才是企業發展的關鍵,當國有企業人才流失的情況逐步凸顯時,社會上曾出現各種譴責聲音,有的譴責當下的年輕人貪圖享受,虛慕體面,不肯腳踏實地;有的指責時下流行的“斜杠人生”理念讓人們身兼數職,失去了專一本職工作的耐心與恒心;還有的觀點指責頻繁跳槽者缺乏長遠眼光,只顧眼前利益。如果拋棄這種“傭工方視角”,站在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客觀視角去審視,會發現國企技術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國企并沒有正視職場需求的變化——求職者與跳槽者的要求往往源于時代的發展,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并與人力資源市場的供需關系緊密結合。如果國企忽視時代的變革,忽視人力資源市場的供需變化,仍將穩定當成百戰百勝的優勢,甚至不肯注重職工的個性化需求,那么技術人才的流失恐難以得到改變。
“在爭搶技術人才方面,國企已經不能再延續高高在上、墨守成規的態度,應該低下頭來調整自身,適應新的趨勢,才能避免陷入人才困局。”一位東北制造業國企負責人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