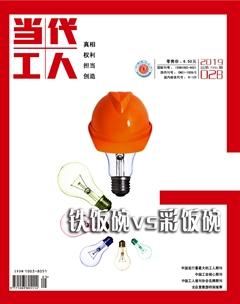人生所向,與若干自己相遇
夭夭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它不會(huì)因任何人的消極緩慢而停止。
時(shí)代拋棄你時(shí),連一聲再見(jiàn)都不會(huì)說(shuō)。于是,越來(lái)越多的傳統(tǒng)品牌開(kāi)始順應(yīng)潮流,嘗試跨界。大白兔奶糖的潤(rùn)唇膏、瀘州老窖的香水、六神花露水風(fēng)味的雞尾酒、老干媽的新潮時(shí)裝……傳統(tǒng)品牌搭乘跨界的快車,正重新煥發(fā)出市場(chǎng)活力,不僅收獲了大量忠實(shí)粉絲,也推動(dòng)了國(guó)貨崛起。
物是怎能人非。作為歷史最為悠久的品牌——工人,在融合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過(guò)程中,也紛紛脫下“傳統(tǒng)”的標(biāo)簽,尋找新的時(shí)代定位。
沈陽(yáng)熱電廠燃料分場(chǎng)機(jī)車班運(yùn)行值班員劉國(guó)壯就是其中的一員。
上世紀(jì)20年代,在北京作寓公的英國(guó)詩(shī)人奧斯伯特·斯提維爾寫過(guò)一篇《北京的聲與色》,把走街串巷的小販用以招徠顧客而做出的種種音響形容成街頭管弦樂(lè)隊(duì),還分別列舉了哪是管樂(lè)、弦樂(lè)和打擊樂(lè)器。他特別喜歡聽(tīng)串街的理發(fā)師(“剃頭的”)手里那把鉗形鐵鉉。用鐵板從中間一抽,就會(huì)“刺啦”一聲發(fā)出帶點(diǎn)兒顫巍的金屬聲響,認(rèn)為很像西洋樂(lè)師用的定音叉。此外,布販子手里的撥浪鼓和珠寶玉石收購(gòu)商打的小鼓,也都給他以快感。當(dāng)然還有磨剪子磨刀的人吹的長(zhǎng)號(hào)。他驚奇的是,每一樂(lè)器,代表一種行當(dāng)。坐在家里的主婦一聽(tīng),就知道街上過(guò)的什么商販。
這是蕭乾《吆喝》中的片段。蕭先生文中提到的“樂(lè)器”,在老百姓的口中也稱做“響器”。在過(guò)去,有些行當(dāng)靠吆喝,有些行當(dāng)卻不能吆喝,只靠響器,俗稱“八不語(yǔ)”,意指賣撣子、修腳、绱鞋、劁豬、[鋸] [局]碗、行醫(yī)、剃頭、粘扇子均不語(yǔ)。
“要是剃頭的大喊‘剃頭嘍,修腳的吆喝‘修腳嘍,賣撣子的叫賣‘好大的撣(膽)子……不好聽(tīng)更不禮貌。”
2018年最后一個(gè)工作日的晚上,遼寧文保志愿者劉國(guó)壯和他的“流動(dòng)民俗博物館”來(lái)到了沈陽(yáng)市皇姑區(qū)北行新華書店,舉辦了一場(chǎng)別開(kāi)生面的公益講座。
講臺(tái)上,劉國(guó)壯左手拿起一個(gè)細(xì)長(zhǎng)鐵棍,右手持著一個(gè)類似鐵夾子的大物件,鐵棍從夾子中間穿過(guò),因摩擦和碰撞發(fā)出清脆悠揚(yáng)的響聲,“這叫鐵喚頭,人們聽(tīng)到這響聲就知道剃頭匠來(lái)了,代替了不禮貌的吆喝。”
一盞油燈、一臺(tái)桿秤、繡花毯子、葷油壇子,放下鐵喚頭,劉國(guó)壯又拿起一件件老物件,時(shí)而細(xì)細(xì)訴說(shuō),時(shí)而與圍坐的孩子們熱烈互動(dòng),在一猜一問(wèn)一答中,讓孩子們了解了蠟炬成灰淚始干、半斤八兩、一升一斗、無(wú)商不奸等民俗趣事。
這不是“流動(dòng)民俗博物館”的首秀。從2017年初至今,劉國(guó)壯的流動(dòng)民俗公益講座走進(jìn)社區(qū)、高校、養(yǎng)老院、書店和幼兒園,透過(guò)一件件具有時(shí)代特征的老物件,近百場(chǎng)活動(dòng),讓近3萬(wàn)名參觀者感受不同時(shí)代背景下的鄉(xiāng)愁,甚至民俗文化的根。
“從小就喜歡老物件,尤其在姥姥去世后,她曾用過(guò)的老物件更激發(fā)我產(chǎn)生收藏的想法。”劉國(guó)壯回憶,起初,家人都不理解,認(rèn)為是在“撿破爛兒”,費(fèi)時(shí)費(fèi)力還費(fèi)錢,甚至還有人說(shuō)他傻。“怕被家人發(fā)現(xiàn),只能藏在車子的后備箱里,走到哪兒拉到哪兒。后來(lái)東西越積越多,藏不住了,只能和家人攤牌。”
在劉國(guó)壯的堅(jiān)持中,家人慢慢也理解了,閑暇時(shí),還會(huì)陪著他去舊貨市場(chǎng)、村鎮(zhèn)大集淘寶,足跡遍及吉林、內(nèi)蒙古、山西、山東等地。
目前,他所收集到的老物件已有200多件。為了更好地展示這些老物件,去年,劉國(guó)壯的父親特地租了一個(gè)不足10平方米的倉(cāng)房和展示架,送給劉國(guó)壯做禮物。“過(guò)去的城市和生活正在消失,老物件作為一種文化符號(hào)卻沉淀下來(lái)。老爸覺(jué)得很有意義,想用這種方式支持我做出個(gè)樣子來(lái)。”
“被遺忘在角落的老物件,即使被收藏了,沒(méi)能將其隱含的文化傳播出去,仍是廢物。要做的更應(yīng)該是變廢為寶。”3年前一次偶然的機(jī)會(huì),劉國(guó)壯把老物件帶到女兒就讀的幼兒園做展示,引發(fā)了新思考,也為他的職業(yè)貼上一個(gè)新標(biāo)簽:“流動(dòng)民俗博物館”公益講解員。
“做好事要趁早,老人沒(méi)有時(shí)間等待,只能與時(shí)間賽跑。”
7年前的一天,劉國(guó)壯回農(nóng)村老家探親。回城車站剛好設(shè)在一家敬老院門口,等車時(shí),他不小心蹭聽(tīng)到幾位在院門口乘涼老人的聊天。
“老王頭昨兒走了,連張能作遺像的像樣照片都沒(méi)有,可憐啊。”
“別說(shuō)他,我都20多年沒(méi)照過(guò)相了。”老人們的聊天有些沉重。
“大姨,我會(huì)照相,給你們照相行不?”劉國(guó)壯沒(méi)忍住熱心腸,和老人們說(shuō)出了自己的想法。
“太行了。只要你能來(lái),我們都舉雙手贊成。”
臨時(shí)起意竟一拍即合,第二天劉國(guó)壯就背著新買的二手單反相機(jī),來(lái)到了敬老院。因?yàn)槔先藬?shù)量較多,老人們被分成兩支隊(duì)伍,行動(dòng)方便的和不便的,分別進(jìn)行拍攝。第一天拍攝行動(dòng)方便的,老人們精心打扮后,自覺(jué)排成長(zhǎng)隊(duì)等候,有的還低頭偷偷練習(xí)微笑。
拍攝結(jié)束,回城后的劉國(guó)壯又自掏腰包,為每位老人都沖洗了兩張照片,3天后送回養(yǎng)老院,并開(kāi)始為行動(dòng)不便的老人進(jìn)行拍攝。“有的老人臥床多年,光屋里的味道就刺鼻難忍,更別提其他了。”劉國(guó)壯脫掉鞋子,一只腳踩在椅子上,一只腳搭在床邊,或踮腳或俯身地拍攝,從一個(gè)房間馬不停蹄地轉(zhuǎn)戰(zhàn)到另一個(gè)房間。
然而這次拍攝,卻成了劉國(guó)壯心中永遠(yuǎn)的痛。“上次是3天后就送回照片,這回有事耽擱了,加上自己也沒(méi)太著急,半個(gè)月后才把照片送回去。”
送照片那天的情景,劉國(guó)壯一輩子都不會(huì)忘。工作人員接過(guò)照片后,開(kāi)始頭也不抬地分揀,其中有幾張照片,被工作人員很自然地撕碎扔進(jìn)了垃圾桶。原來(lái),就在照片被送回的前一天,有兩位老人離世,照片已無(wú)用武之地了。“工作人員越自然地表露,我就越揪心,更責(zé)怪自己為什么不早點(diǎn)兒來(lái),哪怕早一兩天也好。”
發(fā)照片的情景也深深刻進(jìn)劉國(guó)壯的心里。在工作人員分揀時(shí),很多老人就已焦急地守候在一旁,拿到照片后,不少老人都流下了激動(dòng)的淚水,更有個(gè)別老人突然就號(hào)啕大哭起來(lái)。“很難想象,在科技普及程度很高的現(xiàn)代社會(huì),仍有很多老人10年、20年,甚至30多年沒(méi)照過(guò)相。”劉國(guó)壯坦言,對(duì)于這些老人來(lái)說(shuō),激動(dòng)的不是照相這個(gè)新鮮事,而是通過(guò)照相感知他們被關(guān)注和關(guān)懷,“我覺(jué)得我這個(gè)事做得特別有意義,應(yīng)該堅(jiān)持下去。”
說(shuō)到就做到。從2012年開(kāi)始,劉國(guó)壯給敬老院的老人免費(fèi)拍攝照片,至今拍攝近千人。“以前是自掏腰包沖洗照片,從2018年開(kāi)始,咱也玩眾籌了。”劉國(guó)壯展示已獲得的6000元眾籌款及各項(xiàng)目花費(fèi)報(bào)表。“眾籌能滿足一些有心卻無(wú)空閑做公益群體的需求。而且,做公益的關(guān)鍵不在于錢多錢少,而在于人多人少——引起社會(huì)共鳴、營(yíng)造社會(huì)氛圍,這樣被公益的群體才能最大限度地感受公益。”
兩份公益職業(yè)傍身的劉國(guó)壯,并非不食人間煙火。
“我是兩個(gè)孩子的父親,柴米油鹽醬醋茶樣樣都要錢來(lái)買……誰(shuí)家只出不進(jìn),都難以為繼。”于是,劉國(guó)壯為自己制定了清晰的職業(yè)規(guī)劃:春秋兩季主做民俗講座,冬季多去敬老院拍照片,夏季賺錢。“不僅為貼補(bǔ)家用,也為公益做積累。”
劉國(guó)壯賺錢不是唯利是圖,而是唯興趣是圖。他是野戰(zhàn)部隊(duì)的退伍軍人,旅游尤其是去戈壁草場(chǎng)探險(xiǎn),仿佛讓他回到了當(dāng)兵時(shí)的崢嶸歲月。為保持這種空間上的聯(lián)系,13年前,劉國(guó)壯因興趣加入一個(gè)戶外探險(xiǎn)群,從每年固定參加3次沙漠、草原探險(xiǎn)活動(dòng),到如今自己做向?qū)ЫM團(tuán)探險(xiǎn),他的足跡幾乎遍布整個(gè)東北地區(qū)。
“開(kāi)始時(shí)只是單純愛(ài)玩,沒(méi)想過(guò)賺錢。但大家都挺愿意和我玩,沒(méi)事就讓我設(shè)計(jì)路線、安排行程、組織活動(dòng),是大家把我給職業(yè)化了,我也很樂(lè)意接受這份向?qū)У穆殬I(yè)。”
別人都做的事他不做,要做就做最酷的。劉國(guó)壯對(duì)待新職業(yè)很用心,從他設(shè)計(jì)的接地氣的“早知通遼有沙漠,何必遠(yuǎn)行去敦煌”廣告語(yǔ)就能看出。
“靈感來(lái)自于王維的《使至塞上》。去真正的沙漠里聽(tīng)風(fēng)吹過(guò)、聽(tīng)沙流過(guò),一直是生活在水泥森林里的你我,內(nèi)心最渴望的旅行。”劉國(guó)壯從自身感受中尋找靈感,幾經(jīng)周折打聽(tīng)到通遼奈曼旗有大片的原生態(tài)沙漠,經(jīng)朋友幫助聯(lián)系上當(dāng)?shù)仫曫B(yǎng)駱駝的牧民。
在東北,沙漠騎馬常有,騎駱駝則很是難得。為打造全新戶外理念,創(chuàng)新戶外項(xiàng)目,劉國(guó)壯決定開(kāi)展沙漠騎駱駝穿越活動(dòng),在原始沙漠里感受落日、晚霞、孤煙,還有駝鈴悠揚(yáng)。“眼前是夕陽(yáng)映上,耳邊是駝鈴回蕩,嘴邊有蒙古餡餅、拔絲奶豆腐、蕎麥撥面……美食伴美景,我和游客都體驗(yàn)到了。花錢的開(kāi)心,賺錢的也踏實(shí),我對(duì)得起這份職業(yè)啦。”
無(wú)論是民俗講解員、攝影師,還是沙漠向?qū)В@都是不是劉國(guó)壯的本職。
“工人才是我的根,不能丟。”劉國(guó)壯坦言,無(wú)論自己做什么,都得以不耽誤本職工作為前提。
1999年,退伍后劉國(guó)壯來(lái)到了沈陽(yáng)熱電廠燃料分廠,成為一線工人。“上班沒(méi)多久,就趕上2000年鐵西大下崗,當(dāng)時(shí)很慶幸也很自豪,自己能在大企業(yè)有一份穩(wěn)定的好工作。”
剛進(jìn)廠時(shí),劉國(guó)壯是一名檢修員,過(guò)著早8晚5三點(diǎn)一線的生活,輕松但略顯單調(diào)。后因工作調(diào)整,他成為一名運(yùn)行值班員,開(kāi)始了長(zhǎng)達(dá)12年忙碌的倒班生涯。
“做檢修員時(shí),總感覺(jué)一身勁沒(méi)處使,成了運(yùn)行值班員后特別滿足,忙起來(lái)才有價(jià)值。”運(yùn)行值班員上一個(gè)白班能休24小時(shí),上一個(gè)夜班能休48小時(shí),休息時(shí)間比其他工種稍長(zhǎng),但畢竟辛苦熬人,也不能和家人的休息同步,趕上倒班,過(guò)年都得上班……所以大多數(shù)工人都不愿做這份工作,劉國(guó)壯卻樂(lè)此不疲。
鐵道上一列列載煤的火車呼嘯進(jìn)廠后,全靠機(jī)車班將一節(jié)節(jié)車皮解體后送卸煤溝,待煤被卸下后,再將車廂牽出編組好。劉國(guó)壯描繪的工作看似簡(jiǎn)單,實(shí)則辛苦和危險(xiǎn)。尤其在冬季,他所在的沈陽(yáng)熱電廠負(fù)責(zé)2000萬(wàn)平方米的供暖和供電,馬虎不得。
今年44歲的劉國(guó)壯,仍是平均年齡55歲的班組里的年輕人。也曾想過(guò)換崗位,但想到自己離開(kāi)后還會(huì)有其他人來(lái)承擔(dān)這份辛苦,也就斷了念想。
“咱就是普通工人,既然沒(méi)有當(dāng)大領(lǐng)導(dǎo)的遠(yuǎn)大理想,也沒(méi)有當(dāng)技術(shù)大師的超高技藝,那咱就踏踏實(shí)實(shí)工作,認(rèn)認(rèn)真真生活,人生也不比他人差,照樣很精彩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