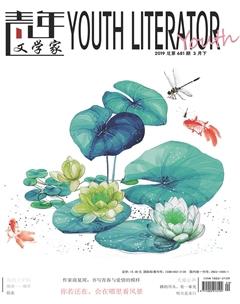文學雜談:十八歲,向戈多道別
鄭劼瑞
明天應該會有大雨,有五六個人記得這場雨,其中有兩三個我在乎的。
我不知道儀式感還有沒有意義,但當我過多的賦予一個時空以過多的意義時,這種對儀式本身的期待會過載,這種“儀式的味道”就會代替回憶內容本身的味道,從而使每一次懷念都變成對儀式內容的懷念。
其實有的時候我不禁懷疑:特定時間與特定空間是否真的對一個人有重大的意義,換句話說,我們所認為的那些『特殊』究竟體現在哪里了?一個人出生到死亡,兩個日期中間的破折號仿佛代替了所有的意義,當后面的日期成為現實時,對于他本人而言,便是世界的終結。
在破折號兩端之間,我們又設置了太多紀念日來為平凡的人生打上標記。我自認為是出于某種恐懼感,就好像是一場知道終點但不知道航程和時間的旅程,向死而生四個字人人都知道,但并不是人人都敢說。
是的,敢于直面探討生命的長度是專屬與年輕人的權利,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只能說服自己長度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寬度厚度與溫度。但即便如此,那些不具有世俗意義上資本成功的人也沒有勇氣在,(放羊-生娃-娶媳婦-生娃-放羊)的生命周期中為生命的價值辯白。
生日,最常見的一種個體專屬的生命長度尺度,我以為生日能促使一個人有盡可能充滿自己生命的沖動,但當這把標尺推著我走了又走我發現,也僅僅是沖動罷了。一方面生活是無法被撐滿的,總有一些時刻,我是將“還未充滿”這樣驚恐的聲音填充進生活,然后帶著驚懼假裝生活;另一方面,除了讓前者產生的恐懼滋生越來越快,“充滿”這個姿態性的動作不具有任何意義,或者可以退一步說,實施“充滿”也不過是另一種小型的空洞紀念,作為一種假裝的儀式,其后果是更加刻意的生活和空洞的自我。
事實上,這種空洞很大程度把持著我絕大多數的時間,甚至現在的我無法描述那些主觀性的時刻。如果你問一個人最感動的時刻或者諸如此類的問題,可能對我而言最先想到的便是狄更斯那一連串的“最”背后的含義——"彼時彼刻,恰似此時是此刻"。“最”這樣的主觀記憶甚至沒有"第一次"這樣的客觀記憶更能引起我情感的共鳴。時間對我而言就好像是一個詛咒,我對他極其敏感,但又極其的漫不經心。
“18歲,或者今天,或者明天,我不清楚”,這樣的荒誕悲劇與我而言和默爾索并無二致,無非是時間節點的不同,但真正重要的不同之處有兩點:這個時間一個關乎言說者本人,而另一個死亡的時間點指向的是言說者的母親;對默爾索而言,他不屑且無能理解假意生活,而我和人間失格狀態下的葉藏有些恰好的相反——他內心對這種生活的假意展現出理解無能同時卻展現出理解的渴望,而我則是在理解這種人人皆從的假意之后,對自己的理解懷抱拒斥和不屑。但到底是殊途同歸,我們仍能在這份假意里祥和的生存下去。
再次追問自己,這種空洞感也是另一種主觀的產物,生活就在那里,他填充著時間涌入大腦成為記憶的部分,他可以是新鮮的,讓那些鮮活世界變得乏味的是"生活不過是這樣"的過度自我總結,抹去了屬于青春和熱血時代的種種。打開一部青春劇,我有能力被那種理想化的象征性的青春而打動,同時充滿遺憾的將之視為和自己錯過的客體,雖然這不影響我在無數個難以入睡的夜晚,用“假如我當初”“假如我沒有”的句型一次次折磨自己被掏走的那部分回憶,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阻止我對“新鮮”之類的真實性的懷疑,讓我跨越思維的那一大筆糊涂賬直接用感情和直覺去體察被自己空洞化之下生活內核。
也許詹姆斯·索特的《光年》對生活的理解是最健康的:“她真正關心的是生活的本質:食物,床單,衣服。其它的毫無意義;總能應付過去。”生活就是那一連串平實的動作,這些動作對于生命里飽滿的人來說足以擺脫“平庸生活”。由此看去,仿佛在空洞和飽滿之間,僅僅是內心頹唐和樂觀的選擇罷了,如果我非要稱這種新鮮的青春生活為一種荷爾蒙的假意,那么有還能有那種生活是真實的呢?恐怕并沒有了,相反,對意義的追趕這樣夸父形象般的追趕,可以同加繆的著名意象一同視作浪漫的象征,也可以視作一種洞察世界無意義后的巨嬰行為,甚至是一種把“追求痛苦”姿態化的世俗精神,而這一點和“假意”又有什么區別呢?
和18歲生日的意義一樣,甚至對于自己而言,這一具體日期可能更具有強烈的時間感和情緒,并且它特殊之處在于它并沒有生日那種對儀式感求而不得的焦躁,無論作為一個日期還是作為100天以來的懵懂,傻笑,故作扭捏,癡迷,失落,反復自省,自怨自艾,絞盡腦汁,多次取舍,有所放棄,得到甜頭,再次上癮:總之此時可以說能帶給自己以生生活的味道,它充滿了感官上的記憶。甚至于它的驚險之處時至今日還在持續,以至于我不能完全誠實的表達這一切。
不過在某種意義上,考察這種誠實,是文字的全部初衷。馬爾克斯活著為了講述,其實沒有人能避免表達,這種被看見的愿望有時甚至超越生死。將真相溶解在幽默里的人往往最嚴肅,最易碎,最難真正地被看見,因為在他們的身上還包裹著一層不希望被看見的事物,這些事物他們自知存在,卻不能知道是為何物,他們希望有人能在他們的表達里幫他們找到,但是又不希望這一點為人所知,在表述沖動不可抑制的激發想象力和創造力時,他們從自己碰撞中的隱喻搜索答案。他們頗有桀驁不馴,但大都在最后欺騙了自己,由于前路渺茫,找尋一塊現成的表達草草的作為戰利品昭告天下,好像得到了結果,但同時他們根本不能欺騙心底作為寫作者的自己。
其實創作者自己應該知道,真正有價值的問題自己無法預設答案,如果隨著創作過程,答案得以流露很幸運,如果沒有,創作就是一層對于生活的表述和再現,終究是不完美的。在我的經驗中,尚沒有一個問題具有唯一的最優解,也就是說,如果說不是騙子,至少是還未曾意識到更好的答案。那些笑而不語寫官方稿件的潦草結尾者和本想深入探討,但中途心力不足而止者,理應更多無奈與自責,不過他們也均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說到底,把創作和生活說成一碼事,注定都是自己的事,真糊涂和假明白的確都是一生,也許問題全都解決不了,事情也都想不明白,本不該錯過的人都錯過了,不妨接受鮮活的世界和自己,讀出文學的態度,勇敢地做自己,為自己的青春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