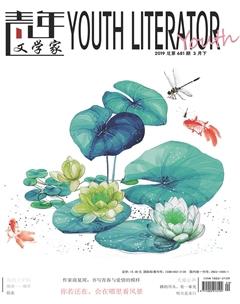新媒體傳播與現代詩發(fā)展的嬗變研究
林振陽
摘? 要:本文用讀者對中國現代詩的接受現狀和評價觀察中國現代詩與大眾間的關系,并對新媒體時代下的中國現代詩歌的內外嬗變做出一次歷史的回溯,結合諸多詩歌現象,回歸新媒體與現代詩結合的歷史場域和具體實際探尋其在“創(chuàng)作者—新媒體傳播—受眾”三重力量下的當下詩歌狀況的必然性,并對中國現代詩的“再經典”和依循當下社會主流精神的可能性做出探討。
關鍵詞:中國現代詩;嬗變與新媒體;讀者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9-0-03
自上世紀90年代起,互聯(lián)網的普及在我國引起了社會的生產方式、思維方式和交流方式的新一輪革新。最為顯要的是,信息傳播和傳媒形式的深刻變革。信息傳播空間迅速擴大,信息發(fā)布和接受的自由度極大提高,信息回饋的即時性也成為可能。這種“新媒體”改變了以往書籍、報刊媒體的單向傳播形式。作為連接文學創(chuàng)作與閱讀的橋梁,新媒體使創(chuàng)作者和讀者的即時交流成為可能,文學也開始以更主動的姿態(tài),介入普通讀者的生活;同時,“新媒體”載體也為讀者參與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事件提供了條件。而當下普通讀者對于文學作品與事件的反應,往往得不到研究者與批評家的有效關注。
德國文藝理論家、美學家姚斯認為“每一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獨有的,可從歷史學和社會學角度確定的讀者,每一位作家都依賴于他的讀者的社會背景,見解和思想”,以此觀點來界定新媒體時代詩歌的讀者,一方面新媒體詩歌的讀者失去了歷史學、社會學方面的“獨有性”,而成了當下的“全民化”;作家依賴的讀者的社會背景、見解和思想也在此基礎上更加的龐大和駁雜,詩歌創(chuàng)作者不得不謹慎應對讀者的“見解和思想”,以避免被支配的外部危機。
新媒體與詩歌的交遇與結合,不僅對詩歌本身,對其與讀者的關系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本文從普通讀者的角度展開考證,以文學生活化的視角來分析當下詩歌的“全民化”境況,以當下來對照歷史,透析新媒體與新詩結合而引起的深刻嬗變。
一、新詩困境的再解讀:歷史與當下的讀者參與
筆者在陜西西安高校及社會人群中發(fā)放調查問卷3000份,期以了解新詩與新媒體結合所產生的影響。下文將依靠問卷所反饋的數據,分析新媒體語境中,讀者對新詩創(chuàng)作、傳播與閱讀的影響。
回收問卷中,76%的人群表示閱讀過新詩。在接受現代詩歌的方式上:通過書本接受詩歌的人群占59.11%,通過電臺接受詩歌的人群占4.44%,通過新媒體接受詩歌的人群占68.89%,通過他人閱讀接受詩歌的人群占13.78%,通過其他方式接受詩歌的人群占12%。顯然,由于圖書市場的繁榮和民眾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書籍閱讀方式依然是大部分民眾的選擇。但通過新媒體接受新詩已成為當下接受新詩的另一主流方式,新媒體已改變新詩的傳播途徑。
新媒體是如何介入詩歌的?魯曙明與洪浚浩在其合著《傳播學》中指出,新媒體是指“以電腦、數字化技術為核心,具有互動性和多媒體功能的資訊與傳播科技。”[1]首先,在宏觀意義上,新媒體具有自由度高和門檻低的特點,這樣的網絡空間成為創(chuàng)作者們聚集和發(fā)表新詩作品的理想場所。微信公眾號、QQ、微博、創(chuàng)作軟件等個人化的、面向大眾的新媒體成為各個階層的詩歌創(chuàng)作者們新的發(fā)表地。隨著“民間寫作”的深度入駐和民間詩人的涌入,網絡詩歌開始泛濫于網絡空間,而基數龐大的網民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對網絡上傳播的詩歌有所接觸。其次,網絡詩歌閱讀在新媒體閱讀免費、鼓勵轉載的運營手段下,較于傳統(tǒng)的紙刊和書籍閱讀,具有操作便捷與成本低廉的優(yōu)勢。在當下網絡幾乎全民普及的情況下,借助手機和電腦等終端,進行線上閱讀,成為當下文化接受的主要手段之一,網絡詩歌重新介入讀者日常生活,可以說是順應時代趨勢的表現。從這方面看,通過新媒體傳播詩歌,帶來的似乎是“詩人”和“讀者”的一次雙贏,實則這次雙贏也給詩歌自身的發(fā)展帶來了挑戰(zhàn)。
在問卷中,對于新媒體傳播與詩歌發(fā)生關系的原因,54.22%的人群認為是市場需求,67.11%的人群認為是文化轉型,55.56%的人群認為是社會需要,24.44%的人群認為是政治促進,52%的人群認為是教育程度的提高,12.89%的人群認為是其他原因。數據中,除了政治促進和其他原因,選擇市場需求、文化轉型、社會需要、教育程度的人群均占50%以上,可見在民眾的認知中,經濟、社會及文化是促使新媒體與詩歌結合的主要原因。顯然,我國上世紀后期,社會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同時也引起了社會及文化的普遍變革。我們也不妨將這一過程稱之為“社會的經濟化”和“文化的經濟化”。在這一背景下,詩歌的卷入是后者。
據資料顯示,網絡文學的經濟化肇始于“榕樹下”網絡文學網站。網絡文學盈利模式基于2000年構建起的“榕樹下在線作品交易平臺”[2],通過線下出版線上作品為創(chuàng)作者和“榕樹下”盈利。2003年,起點中文網開始全面實行付費閱讀制度,現今實行的分級付酬和網絡版權簽約制度也在這一時間形成。此后,收購起點中文網的盛大文學公司CEO侯小強宣稱:“現在付費閱讀是我們最重要的模式,占了60%以上。我們在努力拓展新的商業(yè)模式,無線看書、線下出版、廣告、影視改版、游戲版權,等等”,“我們的作者中,通過版權運營,收入過百萬的作家已有10人,收入過10萬的有近百人”[3]。但是,這一時期,網絡文學經濟化的最大經濟獲益者只是最富有可讀性的網絡小說,而詩歌的境遇與小說不同,除了少數幾個大型的網絡詩歌網站外,都是私人博客、微博在為其發(fā)聲。晦澀、篇幅短小而意旨深遠的詩歌在文化的經濟化中浪潮中,具有明顯的滯后性。但是,詩歌并非一直甘于在“文學經濟”浪潮中居于末流,在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亦走上了大眾的“具有過渡性和淺白性的特征的‘生產者文本”[4]的道路。值得說明的是,詩歌的“生產文本”化并非全然是經濟和傳媒的作用結果,其間也有詩歌創(chuàng)作者和詩歌讀者的“努力”。
從上世紀90年代起,詩歌便呈現出后現代的反叛傾向。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徐江、韓東、伊沙、于堅等為代表詩人“民間寫作”一派形成,這一詩派以“堅持獨立精神和自由創(chuàng)造的品質”[5]為精神核心,立足于“民間”和“本土”,進行“原始”而“自然”的創(chuàng)作,進而解構自“五四”以來中國現代詩借助西方詩體和語料的“西化”寫作路線,恢復漢語尊嚴,發(fā)掘詩歌的口語化美學。在1999年的“盤峰爭論”和“99龍脈詩會”上,“知識分子寫作”一派退卻,“民間寫作”成為新世紀詩歌主流,“口語詩”也成為新世紀詩歌的象征。新世紀以來,詩歌隨著新媒體深入滲透民眾日常生活,不斷重塑民眾的思維脈沖與精神結構,詩歌受眾空前擴大。然而,新媒體在挽救了詩歌的“無人讀”的危局之后,又使詩歌走向了“大眾化”的困境。正如陳衛(wèi)所言:“文學一旦大眾化總是會使文學的本性變得可疑,歷次的文學大眾化都相應付出了犧牲文學本身價值的代價”[6],這種代價在新世紀詩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2000年,“下半身寫作”橫空出世,這種主張描寫“身體”和“性”的詩歌被評論家彭衛(wèi)鴻稱為是“網絡時代的畸形產兒”,是“中國當代詩歌中的一次惡性裂變”[7]。2006,隨著趙麗華的《張無忌》《一個人來到田納西》等詩依靠新媒體廣為流傳,“梨花體”一時成為詩歌風潮。2010年,隨著車延高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以明星徐帆、劉亦菲等為寫作對象的“羊羔體”詩歌甚囂塵上,成為當代詩歌事件之一。在這些詩歌事件中,我們既可以看見詩歌創(chuàng)作者對“口語化”語言的無節(jié)制使用,使代表著中國當代詩歌語言的“口語”流為“口水”,也可以看見中國的名譽思想、功利主義乃至人情評選對詩歌界的滲透污染。除上述兩點之外,在此類詩歌事件中,讀者的作為和態(tài)度也不可忽視。新世紀以來,每當較大的詩歌事件發(fā)生時,起因往往是一個或一群作者的詩歌被廣泛關注和議論,但過程和結局卻多是眾多讀者對此類詩歌的惡搞和戲擬,進而造成擴大化事件的產生。這種“擴大化”最明顯的表現是大眾出于嘲諷而對劣質的詩歌進行大量的模仿,使更多的劣質詩歌出現并泛濫與網絡。由此,我們可以發(fā)現“口水詩”的原創(chuàng)者是中國詩歌劣質化之源,而大眾是中國詩歌劣質化之流。顯然,出于嘲諷和惡搞的戲仿亦屬于讀者對當下詩歌的“見解和思想”,但這種“見解和思想”采取了直接介入的方式,一方面生產了大量的“犧牲了文學本身價值”的詩歌作品,一方面也使真正具有質量的詩歌淹沒于劣質詩歌之潮。此外,語言是時代情緒和精神的特殊載體,也是文化轉革的先聲,具有高度敏感的時代嗅覺,而這種嗅覺在詩歌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從口語詩的駁雜現狀中,可以看出網絡讀者現代質疑品質的缺失。在信息碎片化的時代,從眾主義再次抬頭,給詩歌的可讀性邊界界定提出了巨大的挑戰(zhàn)。
在問及讀者閱讀新媒體詩歌的原因時,48%的人群是因為他人推薦,43.56%的人群是因為詩人名氣,41.33%的人群是因為處于好奇,37.33%的人群是因為標題新穎,29.78%的人群是因為對現代詩有濃厚興趣,11.56%的人群是因為對中國現代詩發(fā)展情況十分關心,17.33%的人群是因為其他原因。在這一調查反饋中,新媒體詩歌在大眾間傳播主要依賴于“分享推薦”和詩人名氣。這種讀者間的分享傳播和創(chuàng)作者個人的聲名吸引,都基于新媒體詩歌語境中網絡式滲透傳播和民眾高度的參與意識。如鄭正西于2010年開通的個人博客“網絡詩選”,通過網絡分享和轉載,點擊率曾一度達到800萬人次,具有極大影響力。當代女詩人余秀華的詩歌開始時并未引起大眾的關注,但在2014年11 月10日,《詩刊》微信公眾平臺上的一篇題為“搖搖晃晃的人間——一位腦癱患者的詩”的推文將余秀華推至眾人眼前。文章發(fā)表的第二天,湖南文藝出版社副社長陳新文即聯(lián)系余秀華,表達了要幫她出詩集的意愿。此后,她的詩作被多家新媒體平臺收錄并發(fā)表,都獲得較大的閱讀量,一時風靡網絡世界。此外,眾多微信公眾號平臺,如“為你讀詩”“讀首詩再睡覺”等也推出一大批詩歌,它們或采用吸人眼球的題目,或采取新穎的形式,都力求吸引讀者閱讀并轉載,從而獲得閱讀量。
在這一系列行為和事件的背后,新媒體和大眾既對詩歌的產生積極影響,也給它帶來了新的危機。在消費邏輯強勢、總體民族想象破碎化的當下,詩歌作為人處理自身與世界的關系的一種重要載體,卻在一定程度上讓位于新媒體。人成為了無數新媒體傳導鏈條中的一環(huán),人本身淪為被消費者,而非能量放射與接收者。在這樣的現狀下,詩歌應以更堅實的生命內核和更強勁的宇宙脈搏進行回應。
二、對未來的思考:新美學與深內涵的發(fā)掘
詩歌與網絡遇合后,有人認為:“網絡詩歌將導致現代漢語詩全方位的改變,甚至由此產生新的美學革命和文體革命”[8],如果將視角投放于新媒體詩歌,“超文本詩歌”便是“美學革命”和“文體革命”一種表現。在問及對新詩文體的發(fā)展期待時,接受問卷的群眾普遍表示新詩在和新媒體傳播的結合中更需要與音樂、圖片乃至影視相配合,打造出符合當下傳播模式的“超文本詩歌”。所謂“超文本詩歌”是指“利用電腦的多媒體技術所創(chuàng)造的數字式文本,這種文本使用網絡語言,可以整合文字、圖像、聲音,兼具聲、光、色之美。”[9]詩人毛翰的《天籟如斯》成功將四十多幅圖畫和兩支曲聯(lián)結成為六輯唯美典雅的詩歌,被譽為是中國“超文本詩歌”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是新媒體技術與詩歌結合成功的典范,為詩歌的發(fā)展試驗出一條“美學”和“文體”的新道路。但在當下,“超文本詩歌”尚不成熟,一些微信公眾平臺與微博偶有詩配畫和詩配樂的新形式嘗試,大多數網頁詩歌和詩歌發(fā)表平臺則依然守持傳統(tǒng)的文字展示。退而言之,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使詩歌達到新的技術高度,引起新的形式體認,但詩歌問題終究需要歸于詩歌本位,無論如何經典化,都無法抹殺詩歌需要語言內核的硬性指標。對于這種“硬性”詩歌元素的體認中,大眾時代的“公眾意識”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小眾意識”撲朔迷離的關系值得我們思考。
在我國新世紀詩歌歷史上,詩歌并非始終如新媒體時代這般流派紛呈,論戰(zhàn)迭起,眾多詩歌創(chuàng)作者各行其道,看似大眾化,實則顯現出極端的個人化。2008年南方特大雪災、“5·12”汶川大地震和2010年青海玉樹大地震后,我國都曾出現過“救災詩”風潮,這是我國詩歌“個人化時代的集體表達”[10]的典型案例。“據不完全統(tǒng)計,‘5·12大地震之后,中國出版界就迅速行動起來,開始收集整理散落在報刊、雜志、網站、論壇、博客上的詩歌佳作,并在最短時間內將作品編輯出版,一時之間,形成了‘地震詩集井噴出版的現象。全國共有70多家出版社策劃、編輯、出版了100余種地震詩集。”[11]在這些詩歌作品中,如《孩子,快抓住媽媽的手》《柔弱的翅膀——5·12最美麗最感人的定格》《汶川我們與你同在》等作品都可以稱得上是現代漢語詩中的佳作,是詩人個體與大眾、與時代結合的優(yōu)質產物。不僅如此,許多專業(yè)詩人也在災難后迅速發(fā)聲,如成都詩人凹凸在5月13日,以個人名義在“芙蓉錦江·成都詩歌論壇”上發(fā)帖《提議:詩人們用詩記下“5·12”震災》;同時,在《芙蓉錦江》第4期開通“5·12:被大地震擊的詩”專欄,一時得到眾多詩人響應。[12]盡管在“救災詩”風潮后的反思階段,有許多人提出救災詩存在“自我感動”和“輕浮”等問題,對真正飽含血淚的災難并無益處,沒有真實地觸及“救災”本身,但單從詩歌方面來看,這一時期新媒體所造就的新詩的個人化縫隙呈現出彌合的趨向,詩歌的“民間”和“官方”的壁壘被打通。中國詩歌在新世紀所呈現出“整體”的性質,受益于并促動詩歌中的“公共意識”的再次覺醒。
在新世紀詩歌史中,“經典”一直是新詩創(chuàng)作者刻意回避的話題,談及這一話題時也往往將“經典”的桂冠贈予被歷史所承認的詩作,而對當下詩歌多給予保守的態(tài)度。這其中既有“經典”需要接受時間檢驗的必要性,也有出于對當下詩歌質量的考量,對當下詩歌非詩因素橫行的不滿。但新詩“再經典”已成為新世紀新詩的主要問題之一。對與這一問題,我們將從當下詩歌的“大眾化”與“小眾化”的矛盾切入,進行探討。
有人認為,詩歌之所以仍然存在的直接原因是:“一小部分人堅持在寫,一小部分人堅持在讀”[13]。顯然,這與當下的詩歌“大眾化”論調相悖,但卻深刻道出了當下新媒體詩歌應有的傳播狀態(tài)。新媒體時代,新詩在受眾方面,的確可以稱得上已“大眾化”;另一方面,極低的準入門檻使大量的詩歌創(chuàng)作者匯聚網絡,當下詩歌創(chuàng)作的底座是龐大而堅固的,但在創(chuàng)作上,他們更傾向于獨來獨往或小范圍的交流。如此看來,詩歌既不是“小部分”堅持在寫,也不是“小部分”堅持在讀。詩歌在“大眾化”時代“再經典”的道路上,如何大浪淘沙,如何發(fā)掘出詩歌“黃金時代”的潛質,依然是急需探討的問題。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底座之于高樓的作用。詩壇有準入門檻,而詩歌是通往無限的,應對任何時空開放。
三、結語
網絡是一個具有極大包容性的空間,在這一空間內,新媒體傳播和新詩的結合,產生出豐富的可能性。詩歌在新媒體傳播中既是受益者,亦是受害者。新媒體使詩歌走出了“小眾”和“無眾”的境遇,又給詩歌帶來了“大眾化”的困擾。詩歌雖有著“泛濫”的空心化憂慮,但整體而言,在極為龐大的柴基之上,詩歌之火必定越燃越旺。當下新媒體土壤雖積淀已久,但新媒體詩歌仍處于萌芽狀態(tài)。對于詩歌的未來,我們不僅要對詩歌本體進行“扶正”,也應從普通讀者的視角進行反思和探索,做出真正“大眾化”的努力。
注釋:
[1]魯曙明,洪浚浩:《傳播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頁。
[2]黃發(fā)有:《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55頁。
[3]黃發(fā)有:《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60頁。
[4]陳衛(wèi):《中國當代詩歌現場》,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頁。
[5]韓東:《論民間》,《芙蓉》2000年第1期。
[6]陳衛(wèi):《中國當代詩歌現場》,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頁。
[7]參見羅小鳳:《邊緣化?全民化? —新媒體時代新詩與公眾世界的關系》,《南方文壇》2016年第5期。
[8]王珂:《網絡詩將導致現代漢語詩的全方位改變》,《河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9]吳思敏:《新媒體與當代詩歌創(chuàng)作》,《河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10]蘇曉芳:《網絡與新世紀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頁。
[11]蘇曉芳:《網絡與新世紀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頁。
[12]參見蘇曉芳:《網絡與新世紀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頁。
[13]楊碧薇:《新媒體民謠旋風下的新詩》,《文藝報》2017年第7版。
參考文獻:
[1]蔣孔陽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美學名著選(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
[2]魯曙明,洪浚浩.傳播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3]黃發(fā)有.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4]陳衛(wèi).中國當代詩歌現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韓東.論民間[J].芙蓉,2000,(1).
[6]羅小鳳.邊緣化?全民化? 新媒體時代新詩與公眾世界的關系[J].南方文壇,2016,(5).
[7]王珂.網絡詩將導致現代漢語詩的全方位改變[J].河南社會科學,2004,(1).
[8]吳思敏.新媒體與當代詩歌創(chuàng)作[J].河南社會科學,2004,(1).
[9]蘇曉芳.網絡與新世紀文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10]楊碧薇.新媒體民謠旋風下的新詩[J].文藝報,2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