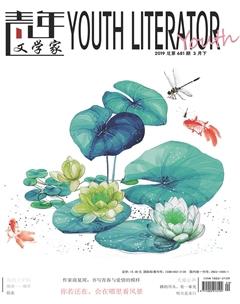《繁星?春水》中“愛”的智慧的表達譚
蘇賴馨
摘? 要:談到愛,我們往往會想起許多美好的事物,可以說“愛”就是美好的代名詞。愛不僅僅指愛情,也包含了母愛、父愛、友情、親情、博愛以及人對所有事物的根本情感。人們渴望得到愛,感受愛的呵護,并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的成長,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讓自己的心靈得到升華。愛是很多文學作品中永恒的主題,本文將通過對冰心《繁星·春水》中“愛”的智慧展開分析,感受作者對“愛”理解和體悟。
關鍵詞:冰心;愛;智慧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9-0-01
在現實社會中,愛一路陪伴我們成長,愛幫助我們克服困難和失敗,愛伴隨我們走出孤獨及不幸。冰心在她的詩集《繁星·春水》中一直貫穿著“愛”這一主題,不僅記錄了冰心對愛的理解和對愛的體會,還充分體現了“愛”的智慧。在冰心的內心世界中,愛的智慧集中地體現在她的人生態度上。在《繁星·春水》中,冰心大量通過少女的視角,將自身的經歷以及平時生活中的事物、包括自身的感想,通過簡潔而富有情感的文字表達出來,向讀者傳達自己理解的母愛及童心。
一、愛的智慧是對母愛的贊美謳歌
在《繁星·春水》這部作品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詩人冰心認為愛的智慧基礎便是母愛,從古至今,母愛都是無數文人學者不斷歌頌的主題。事實上母愛是世界上最無私以及偉大的情感。作者冰心所寫出的《繁星·春水》這部詩集中最為關鍵及占據比重最大的便是關于愛的闡述,她將愛的智慧當作詩集的中心思想,并將自己的見聞及感受通過擬人、比喻等修辭手法表現出來,闡述自身對母愛的理解和感受,讀者可以在精煉簡潔的文字中深刻的體會這種情感[1]。
在《繁星·春水》當中有著一句“小小的花,也想抬起頭來,感謝春光的愛——然而深厚的恩慈,反使她終于沉默。母親呵!你是那春光么?”在這里冰心采用了擬人的修辭,小小的花就像是晨光的孩子,那么究竟為什么小花要想感謝春光帶來的愛,最終反而令她沉默呢?這里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是:小花最后沉默就是因為春光給她的愛是非常無私且不求回報的,這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冰心運用了疑問句,是將自身對母愛的贊頌充分表達[2]。在這首小詩當中,冰心充分的暗示讀者春光就像是小花的母親,她為其付出了一切,卻不求回報,這就好像是我們的母親為了哺育我們成長無私的奉獻行為,這樣的母愛是無私與偉大的,無法用任何語言將其形容出來,作為子女,需要對母親偉大的母愛保持感恩。通過作者的表達,我們可以發現其經常采用平時生活當中常見平淡的事物,從而展現出母愛的偉大與無私,并進行贊頌,我們從中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對母愛的感恩以及敬意。
二、愛的智慧是對童心的歌頌
在《繁星·春水》這部作品中,我們還可以感受到一個重要主題,那就是童心。冰心在小時候因為家庭條件比較優越,擁有了一段單純美好的童年經歷,正是由于這樣的美好童年,她內心一直充滿了愛和幸福,一直保留著單純美好的童心,所以她所寫出的文字及作品也有著孩子般的天真和無邪。讀者在品讀的時候,總會身不由己的陷入這種簡單純凈的情感中無法自拔。比如說,作者在《可愛的》這首小詩當中就寫到過,“可愛的,除了宇宙,最可愛的只有孩子。和他說話不必思索,態度不必矜持。”這首詩其實并不復雜,其言語也非常的簡潔,冰心對于孩子的喜愛和贊美在她的文字中充分地表現出來。在成年人的內心中,童心就好像是故鄉般的存在,從小孩身上他們可以感受到人性的天真簡單。
三、愛的智慧是對自然的崇敬之情
《繁星·春水》的第三個主題就是作者自己對大自然的崇拜之情,對大自然的崇敬其實也是愛的一種展現,這是一種更為寬廣的愛。在冰心的文字帶領之下,我們可以深入女性的視角和心理感受這種廣博的愛,這充分體現在冰心對大自然中的花草樹木的喜愛。和男性比較女性有著更加細膩和豐富的情感體驗,如此才讓女性擁有著更強的自然感知能力,浩瀚的大自然有著廣闊無邊的包容與寬恕。冰心在《繁星·春水》中曾經寫道,“我們都是自然的嬰兒,臥在宇宙的搖籃里。”這句話雖然很短,卻把自然比擬為孕育人類的母親,而人類是大自然的兒女,這樣的方式不僅深刻的表達了自己對于母愛的贊頌,又表現出了自然對人類的呵護。所以說,作者寫出《繁星·春水》對于當下的人們還有著警醒及教育的作用,自然是社會和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重要物質源泉,我們對大自然應保持足夠的崇敬及敬畏之心。
總結:
綜上所述,《繁星》和《春水》是冰心在探索人生的過程中靈光閃動的匯合,里面包含著她對生命真諦的認識和理解,包含著“愛”的智慧。作者采用了多樣化的修辭手法以及豐富的表達方式,把自身生活的見聞和感想,通過富有感情的文字自然表達出來并寫成了小詩,自始至終表達的是“愛”的主題,而這也正代表了冰心對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和渴望。
參考文獻:
[1]張夢.淺析《繁星·春水》中“愛”的智慧[J].現代交際,2018(03):102-103.
[2]董榆萍.冰心《繁星·春水》中玫瑰刺與玫瑰紅的寓意[J].名作欣賞,2017(35):13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