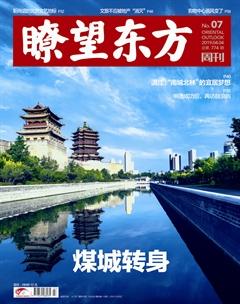法眼祖庭清涼寺

龔巨平
南唐李后主經常待在清涼寺內虔誠禮佛,留有“未嘗歸去宿龍宮”的詩句。
“塔廟當年甲一方,千層金碧萬緇郎。開山佛已成胡鬼,住院僧猶說李王。遺像有塵龕壞壁,斷碑無首立斜陽。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輿夜納涼。”徜徉在南京城西清涼山中,宋代詩人劉克莊的這首《清涼寺》油然浮現腦中。
清涼寺是南唐知名的寺院,也是都城內著名的標識之一。走進這座銘記一代繁華的皇家寺院,緬懷南唐“三千里地河山”“鳳閣龍樓連霄漢”的輝煌歲月,夕陽西下,斷碑在庭院中投下長長的陰影,清風拂過,劉克莊不能不由衷地生出一種時光無情、好夢不再的慨嘆。
清涼寺所在的清涼山,在宋代以前稱為石頭山。相傳諸葛亮曾用“鐘阜龍蟠,石頭虎踞”來概括南京山嶺之雄峻,龍蟠虎踞從此作為形容南京山水形勝的專屬詞匯。鐘山與石頭山一起,成為南京的自然地理標識,也是城市的文化標志。
最早看中這塊寶地、與石頭山緊密聯系起來的是楚威王。周顯王三十六年,越國進攻楚國,反被楚國制服。為了加強對這一區域的控制,楚威王在石頭山上營建金陵邑。金陵邑是史書明確記載的南京老城區政區建置之始,也是南京“金陵”雅稱的由來,為后世南京城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楚國的金陵邑在秦帝國鐵蹄的踐踏下,逐漸坯頹毀棄。金陵也在秦始皇埋金壓勝下貶稱秣陵。東漢建安十六年,孫權自京口移駐秣陵,十七年開始重整金陵邑城,改稱石頭城,用以貯藏糧草器械。
南朝繁華地,指日換旌旗。隋朝一紙“耕墾蕩平”的詔令,將四百載帝都毀于一旦。見識過金戈鐵馬、聽聞過動地鼙鼓的石頭山,在唐宋以迄明清的帝國版圖中,軍事地位、作用漸而消解;秀麗旖旎的自然風光,引得文人士大夫流連忘返,在唐詩宋詞的吟哦詠誦中,清涼山人文蔚起,逐漸形成獨特的清涼山文化,在喧囂的市井之外,為人們提供了緣自生理,發于內心的清涼世界。
在清涼山文化概念中,佛教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現有文獻表明,清涼寺的前身可追溯至楊吳順義四年徐知誥修建的興教寺。升元元年(937年)徐知誥復姓李,改名昪,在金陵稱帝,隨后將興教寺擴建為石城清涼禪寺,成為南唐的皇家寺院,開啟了清涼寺最為輝煌的歷史。
南唐李后主經常待在清涼寺內虔誠禮佛,甚至寄宿寺中,留有“未嘗歸去宿龍宮”的詩句。當時寺內所藏后主的八分書與李霄遠的草書、董羽的畫龍一起,被譽為寺院三絕。
世易時移,南唐時期清涼寺的規模布局今天已經難以詳考。然而天下山川形勝處,古今相承,往往隨人廢興,清涼寺之所以為歷代傳頌,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僧文益在清涼寺創立了中國禪宗五家之一——法眼宗,清涼寺因而成為法眼祖庭。
法眼宗博取眾家之長,“應時所需,宏開法眼;對病施藥,相身裁衣;理事不二,貴在圓融;若論佛法,一切現成;不著他求,盡由心造”等為其旨要。文益禪師在清涼寺法嗣六十余人,或為王侯敬重,或開化一方,“佛佛手授授斯旨,祖祖相傳傳此心”,使法眼宗在宋初趨于極盛,并遠傳至朝鮮半島。
明代建文四年,周王朱橚重建破敗的清涼寺,賜額清涼禪寺。在明代中晚期興起的士人雅游和勝景品鑒活動中,清涼寺作為登高攬勝的佳處,列名其中。在明清圖繪南京勝跡的畫作中,“清涼環翠”是題材之一,而“清涼問佛”更名列金陵四十八景之中,足見其形勝佳絕,引人入勝。
經過近年的考古發掘,明代、清代清涼寺的建筑布局基本清晰,發掘清理出的建筑基址將保護并展示。正在興復的清涼寺,作為石頭城遺址公園的一部分,將以生態文明為理念,充分考慮佛教傳統與現代相結合、寺院與園林相融、信眾與游人共分享等多種元素,將清涼寺厚重的歷史文化挖掘、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