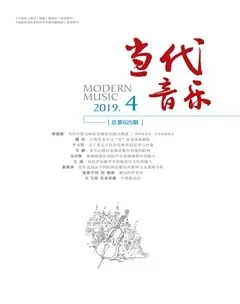古琴藝術中以“芳”論琴現象解析
[摘 要]“芳”在《太古遺音》中被列為“琴有九德”之一,用以品評古琴。“芳”在我國傳統文化語境中是對美好品德的贊美。而“德”也被賦予深刻的哲學內涵。而在對“芳”的內涵理解的探討過程中,缺乏對琴弦物理性能的關注,對“彈久聲乏”中“久”的理解也產生歧義。而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是研究以“芳”論琴現象的應有之意。
[關鍵詞]古琴;九德;芳;音色;味
[中圖分類號]J6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2233(2019)04-0004-02
一、研究緣起
就目前收集整理的資料而言,以“芳”論琴的現象最早出現在《太古遺音》中,該書將對琴器的品評概括為“九德”,“芳”為“九德”之一。原文中“芳”的表述為:“謂愈彈而聲愈出,而無彈久聲乏之病。”
查阜西先生在《古琴的常識與演奏》一文中對“芳”的理解為:“彈大曲時,發出的音響要前后統一,音量音色自始至終都不改變。”[1]鄭珉中先生在《旅順博物館藏“春雷”琴辨》一文中,將“芳”解釋為“愈聽愈美好”[2]。
顧永杰、裴建華在《古琴斫制技藝中的音色》一文中,將“芳”理解為音色的“聲學穩定性好”[3]。“琴體用木材經過適當處理,面板和底板用木材的比動彈性模量值越大,琴材材質、琴體制度、槽腹制度、灰胎的厚度和材質越均勻,則琴體的聲學穩定性和結構穩定性越好。”[4]
郭諗墨《斫琴家茅毅對琴人斫琴傳統的繼承研究》中談及“芳”時提出:“越彈音色越響亮、透潤、圓融,這與漆灰選擇有關。”[5]
據上述文獻分析,目前在以“芳”論琴的研究中,存在問題如下:1.沒有對產生以“芳”論琴現象的原因的探究,即表達芳香之意的“芳”,究竟是如何與古琴這件樂器本身產生聯系的問題。2.在斫琴制作工藝中,涉及古琴灰胎、琴體聲學結構等問題,但缺乏對琴弦聲學穩定性問題的研析。本文將就這兩個問題進一步闡述。
二、以“芳”論琴現象的產生
“芳”的本意是指芳香。但“芳香”就其字面意思而言,與古琴這件樂器似乎無任何聯系。因此,“芳”不應從其本意層面理解。在查閱相關資料后發現,“芳”在我國傳統文化語境中,與高尚的品德相關。《楚辭·離騷》中有云:“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意為:那些上古的君王治理國家以百姓疾苦為先,所以那些品德高尚的賢者都愿意擁護他。此處,“芳”與品德產生了某種聯系,而此種聯系在我國傳統文獻中并不是孤例。
東漢大儒蔡邕曾在《劉鎮南碑》中寫道:“昭示來世,垂芳后昆。”意為:美好的品德給后輩帶來福分。《晉書后妃傳上》中亦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的表述。其中“芳”應理解為“美好的品德”。
但上述例證,只表明“芳”與“德”之間的聯系,能用以解釋為何“芳”被列入“九德”之中。但“德”是對人品格的概括,而非對器物品質的概括。因此,還須繼續研析“德”與古琴這件樂器的關聯。
通過進一步收集整理資料發現,《尚書·皋陶謨》中就有關于“九德”的論述,原文為:“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其中,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強是“行”,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是“德”。原文并不僅僅是在說九德,還有九種與之對應的行為。所謂“九德”,是“德”亦是“行”。
有學者認為:九德“在本質上都是把‘德’和天、地、人的本質特性聯系在一起做出的疏解。天剛、地柔、人直,集此三者之特性于一身的‘德’,其作為形上的最高本體范疇的意義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6]
由此可見,“德”并不僅僅是指人的品格,是對天地萬物本質的一種闡釋,一切具備靈性之物皆可有“德”。琴在文人士大夫群體眼中,無疑是屬于靈性之物的范疇。因此,“德”與琴的聯系就在這一邏輯關系中產生。而“德”作為一個哲學范疇,其具體內涵,可以根據對象的不同而產生變化。
《太古遺音》中,“九德”的內容已經與《尚書·皋陶謨》中的內容從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大相徑庭。其實,若仔細分析,“九德”中的“奇”,涵括了“輕”“松”“脆”“滑”四部分內容,分別是指木材的密度、木材的老化程度等四種物理特性。但這四種特性均與木材的傳聲特性有關。四種特性可分別進行論述,亦可合并論述。但若以“輕”“松”“脆”“滑”取代“奇”,“九德”則要變成“十二德”。而之所以仍沿用“九德”,或是出于對傳統的尊重。“九”在我國傳統文化語境中被認為是“至數”,即圓滿之數。
由此可見,“九德”中“芳”并不能理解為“香氣”,而是對“德”的贊美之詞。“德”也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品德,而是哲學層面上對人與天地萬物本質的概括。正因如此,以“芳”喻琴,在我國傳統文化語境中就顯得恰到好處。
三、對“九德”中“芳”的理解
“芳”在“琴有九德”中的表述為:“謂愈彈而聲愈出,而無久彈聲乏之病。”對“芳”的理解的文獻資料中,查阜西與鄭珉中二位先生的闡釋具有代表性。
查阜西先生的理解為:“彈大曲時,發出的音響要前后統一,音量音色自始至終都不改變。”[7]而鄭珉中先生理解為“愈聽愈美好”[8]。顧永杰、裴建華從琴體的聲學穩定性角度闡釋,更接近于查阜西先生的理解。而郭諗墨從古琴的漆灰角度的解釋則與鄭珉中先生的理解有些相近。這其中各有各的道理,但相關研究中,缺乏對琴弦穩定性問題的討論。
琴弦音色的穩定性與古琴演奏音色關系密切。琴弦附著在琴體上,一頭固定在雁足處,另一頭與琴軫相連。琴弦在振動過程中,在龍齦與岳山兩處,通過弦振動引起琴體振動。
在古琴上弦工作完成后,琴弦、琴體均處于緊繃的狀態之中。琴體與琴弦相互作用,相互受力。琴體對琴弦的力,使其處于充分拉伸狀態。琴弦也必須產生足夠的張力,才能使琴體達到振動的臨界點。就琴弦而言,能否彈奏出最優質的音色,取決于琴弦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最佳狀態,取決于琴弦的穩定性。
琴弦的穩定性受琴弦延伸率與琴軫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延伸率是指琴弦達到定音高度后弦線出現的拉伸變形程度。”[9]琴弦的延伸“會使琴弦拉力、張力、音高逐漸降低……也會在樂器音強、音色等聲學特性上帶來變化”。[10]據實驗研究表明,絲弦的延伸率最高可達8%[11]。這會對古琴音色產生明顯影響。
影響琴弦穩定性的另一個因素是琴軫,琴軫是位于琴額下方用來調整琴弦張力、改變音高的一排旋轉軸。其工作原理,是依靠絞緊或放松連接琴弦的絨扣,使琴弦伸長或縮短,進而改變琴弦張力,使琴音音高發生變化。
受琴軫制作工藝的影響,古琴在彈奏過程中,容易出現跑弦的現象。具體表現為:蠅頭在岳山上的位置發生偏移。偏移現象的出現,通常意味著琴弦拉力、張力的改變,進而影響古琴音色、音準等方面。相比較而言,絲弦音色的穩定性,主要是受到絲弦延伸率的影響。
查阜西與鄭珉中二位先生對原文中“久”的概念的理解存在差異。查阜西將“久”理解為演奏一首大曲子的時長。而就目前收集到的音響資料而言,最長的琴曲為李明忠演奏的《秋鴻》,時長24分43秒。[12]對音色穩定性問題的探討,在以分鐘為計量單位的時間段內,可以從琴體聲學結構的穩定性角度去闡釋其原理,亦應從琴弦的穩定性層面進行闡釋。對鄭珉中的“愈聽愈美好”,可以從“漆灰”角度去闡釋,“漆灰”對音色產生的影響,屬于“九德”中“透”中的內容。但從嚴格意義上說,“透”也與“芳”有關。因為,“芳”是對古琴的整體的、動態的品評。
“九德”中,“奇”是對琴材的評價。“古”“透”“靜”是對古琴制作工藝的評價。“潤”“圓”“清”“均”是對琴音的評價。而經過一定時間范圍內的演奏后,在“奇”“古”“透”“靜”的前提下,琴音能愈發“潤”“圓”“清”“均”,才能稱為“芳”。“芳”是一種深刻而獨特的審美體驗。查阜西先生的理解,是“芳”應有之意。而鄭珉中先生的理解,或許與“芳”的本意更為接近。
結"語
綜上所述,“芳”是對古琴這件樂器的整體品評。“琴體的聲學穩定性”“漆灰”等,都屬于“芳”的應有之意,只是闡述的角度不同。“芳”不僅是我國傳統文化語境中以“味”論藝現象的具體體現,更是研究我國傳統文化語境中以“味”論藝現象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注釋:
[1]黃旭東,尹鴻書,程源敏,查克承.查阜西琴學文萃[M].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出版社,1995:551.
[2]鄭珉中.旅順博物館藏“春雷”琴辨[J].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03):22.
[3][4]顧永杰,裴建華.古琴斫制技藝中的音色[J].藝術科技,2017(03):180.
[5]郭諗墨.斫琴家茅毅對琴人斫琴傳統的繼承研究[D].山東工藝美院,2018:52.
[6]孫熙國,肖"雁.論《尚書》“德”范疇的形上意蘊——兼論中國哲學認識和把握世界的三個基本環節[J].哲學研究,2006(12):46.
[7]同[1].
[8]同[2].
[9][10]"[11]楊"帆.古琴振動體與共鳴體聲學特性研究[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5:72.
[12]李明忠.秋鴻 李明忠 百納絲弦琴(上集)[M].廣州:廣東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23.
(責任編輯:崔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