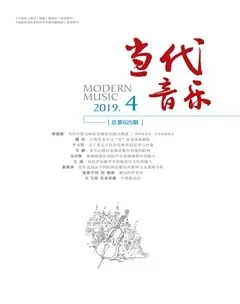淺談乾隆初期花雅同臺(tái)現(xiàn)象





[摘 要]《太古傳宗·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是湯彬和版《太古傳宗》的附刊,由徐興華、朱廷镠收錄,是當(dāng)時(shí)舞臺(tái)上常演的被稱為“弦索調(diào)”的流行劇目,反映出當(dāng)時(shí)“雅”“俗”諸腔兼收并蓄的歷史特點(diǎn)。本文對(duì)《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中部分看似七聲音階的樂譜進(jìn)行分析,實(shí)應(yīng)以五聲音階為主,記譜存在借調(diào)記譜和五聲綜合的特性。為此后用音樂形態(tài)學(xué)法實(shí)證乾隆初期,戲曲聲腔非如今流派涇渭分明,而呈現(xiàn)“風(fēng)攪雪”狀態(tài)的歷史特征,打下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關(guān)鍵詞]太古傳宗;音樂形態(tài)學(xué);聲腔并蓄;花雅同臺(tái)
[中圖分類號(hào)]J609"[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7-2233(2019)04-0134-03
《太古傳宗·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是首調(diào)唱名的工尺譜體系。工尺譜唱名標(biāo)記分為兩類:固定名標(biāo)音和首調(diào)唱名標(biāo)音。“固定名標(biāo)音,就是各個(gè)譜字代表固定(或相對(duì)固定)的音位、指位,有固定(或相對(duì)固定)的音高……首調(diào)唱名標(biāo)音,就是各譜字只標(biāo)示譜字之間的相對(duì)音程關(guān)系,其絕對(duì)音高根據(jù)所使用的調(diào)門來決定。”[1]《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的調(diào)性如何,前人并未做出過多說明,筆者在對(duì)《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中所有譜例解譯、分析后得出以下結(jié)論。
一、本調(diào)記譜的五聲音階為主
《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24套89個(gè)曲牌中,12套為五聲音階曲譜。且一套曲譜中,多數(shù)曲牌為一種調(diào)式。如《崔鶯鶯怨天恨啊呀地》中【和首】和【掛真兒】為五聲羽調(diào)式,而【山坡羊】中唱段為五聲徵調(diào)式。第一首《散曲》中【四朝元】及余下三首【前腔】為五聲徵調(diào)式等。現(xiàn)筆者將《太古傳宗·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中所有五聲音階曲譜按記錄的先后順序,按結(jié)音為調(diào)式主音方式判斷其調(diào)式。[2]
在《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中所載的12套本調(diào)五聲音階曲譜,多為商調(diào)式和羽調(diào)式,而《崔鶯鶯怨天恨啊呀地》《散曲》《僧尼會(huì)》中少數(shù)徵調(diào)式、宮調(diào)式的曲牌,《唐二別妻》中以角結(jié)尾唱段的出現(xiàn),是否與其所屬聲腔有關(guān)亦或是與其上演地區(qū)音韻相關(guān)仍有待筆者進(jìn)一步探尋。
二、含有五聲綜合的七聲音階樂譜
《花子拾金》為七聲音階曲譜,其中【四邊靜】【道和】均為結(jié)音落于“上”的清樂七聲宮調(diào)式。以【四邊靜】為例,解譯如下[3]:
首先“凡”字不突出,兩曲牌加一起“凡”僅出現(xiàn)一次,且為下行經(jīng)過“六凡工”形式,可忽略不計(jì)。其次“一”字為偏音。“一”字雖頻繁出現(xiàn),但旋律走向均為“上一四”形式的下行經(jīng)過音,不為骨干音。其三,將全部譜字由上排列,為上尺工凡六五乙的自然七聲音階,且“凡”只出現(xiàn)一次,也可定義為六聲宮調(diào)式。
【耍孩兒】及兩個(gè)【前腔】(按:【前腔】并非一個(gè)特定曲牌,而是此部分曲牌按照上一個(gè)曲牌唱),按【耍孩兒】傳統(tǒng)格式以“543”結(jié)尾,為七聲角調(diào)式。
【雜板令】這一曲牌,與前三個(gè)曲牌均有不同,是一個(gè)五聲但有綜合的樂譜。開頭“月暗星昏一舉成名天下聞”至“正是上山擒虎易”均為“上、尺、工、六、五”(按:六、五二字的低八度譜字合、四不列于此,僅講一個(gè)音列所用譜字列出。下同)五個(gè)音。
從“開口告人難”至“叫道都是賣花聲”轉(zhuǎn)為上方五度調(diào),首先宮音“上”字消失不見,而“一”字突出;其次“一”字常與“尺”字相連使用;其三,此五句所用譜字由六開始排列為“合、四、一、尺、工”五個(gè),由宮角大三度可知此五句為以“合”為宮。
[HJ2.4mm]
此五句之后至此曲牌結(jié)尾處,則轉(zhuǎn)回下方五度以“上”為宮,并結(jié)音落于“上”字,故而此曲牌為夾有上方五度綜合的五聲性宮調(diào)式。
《花子拾金》的最后一個(gè)曲牌【清江引】,則是五聲音階宮調(diào)式。
三、借調(diào)記譜的五聲性樂譜
《來遲》是一首典型的借調(diào)記譜形式的五聲音階樂譜,為下方五度借調(diào)記譜。首先,“一”字突出。《來遲》中五個(gè)曲牌【榴花好】【前腔】【好事近】【前腔】【尾聲】中,一字頻繁出現(xiàn),且與尺字相連。其次,“上”字處于弱音位置。在全曲中僅在【榴花好】及其后的【前腔】中的一個(gè)樂句出現(xiàn),【尾聲】中出現(xiàn)了一次。而【榴花好】中出現(xiàn)“上”字的樂句,明顯為本調(diào)向下方五度的綜合,故而不應(yīng)考慮在曲譜所用譜字之中。其三,由合將譜字排列,為合、四、一、尺、工,無上無凡,故而應(yīng)為以“合”為宮的五聲性調(diào)式。由【榴花好】起,所用曲牌的調(diào)式分別為商調(diào)式、宮調(diào)式、宮調(diào)式、商調(diào)式、徵調(diào)式。以【榴花好】前幾句為例:
四、存在轉(zhuǎn)調(diào)現(xiàn)象的樂譜
《醉?xiàng)铄肥且皇酌黠@為轉(zhuǎn)調(diào)的樂譜。首先,其第一個(gè)曲牌【新水令】,前三句為以“上”為宮的五聲音階,所用譜字無凡無一。由上排列所用譜字為,上尺工六五。其次,凡、一大量出現(xiàn)。從第四句“一霎時(shí)皓月騰空”始,樂譜開始出現(xiàn)大量凡、一,此時(shí)所用譜字為一個(gè)音列,上尺工凡六五乙。其三,工音沒落。在凡、一出現(xiàn)的三句“恰便似嫦娥離月宮,那嫦娥呵,你為我到此相陪奉”中,工音只出現(xiàn)了一次,且位于下行音階“凡工尺”中。其四,凡字成為骨干音。凡字自“恰便似嫦娥離月宮”中出現(xiàn)始,便頻繁出現(xiàn),且常與尺字、五字相連使用,旋律走向中常位于強(qiáng)拍強(qiáng)位,故而為轉(zhuǎn)調(diào),由原調(diào)向下方五度轉(zhuǎn)調(diào),但記譜仍按原譜記譜。其五,一字為偏音。一字雖頻繁出現(xiàn),但所處位置均為上一上,或上一四之間,不具有獨(dú)立性,且若按7唱,則為下方五度調(diào)中的變徵,唱起來顯得別扭,故而此處“一”應(yīng)按ь7,即下方五度調(diào)中清角處理。
而【新水令】中的旋律,并非僅為單純轉(zhuǎn)向下方五度至最后。在成功轉(zhuǎn)為下方五度調(diào)后,又夾有綜合的因素。如在由原來“一板一眼”記譜變?yōu)椤坝邪鍩o眼”時(shí),可以明顯看出樂譜有向譜面的下方大二度調(diào)轉(zhuǎn)調(diào)的傾向,但仍以譜面下方五度調(diào)為主,整個(gè)有板無眼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以上為宮的譜面記載的下方五度調(diào)與下方大二度調(diào)兩種調(diào)式的綜合。其一,一字與凡字交替突出。不同于一板一眼中的一字,此處一字間歇性與六字相連使用,而凡字亦不再通篇占據(jù)骨干音位置。在一字突出時(shí),凡字常與六字相連,削弱了大三度骨干音的性質(zhì)。而在凡字突出時(shí),常與尺字相連使用,一字與上字相連使用成為偏音。其二,工字未出現(xiàn)。在一字突出時(shí),亦未出現(xiàn)工字,故而有板無眼部分所使用譜字仍為上尺凡六五乙五個(gè),所以一字在凡字宮角大三度性質(zhì)削弱時(shí),調(diào)轉(zhuǎn)向譜面下方大二度。故而此部分為以譜面記載調(diào)式的下方五度調(diào)與下方大二度調(diào)式的綜合。這種情況持續(xù)至【新水令】尾音,最后一句譜面記載落于“上一”二字,實(shí)則應(yīng)為譜面下方大二度調(diào)的商宮,應(yīng)為譜面下方大二度調(diào)的宮調(diào)式。
《醉?xiàng)铄返牡诙€(gè)曲牌,也就是最后一個(gè)曲牌【清江引】,亦為本調(diào)向上方大二度的移調(diào)記譜,即實(shí)際以“一”為宮,結(jié)音落于“一”字,宮調(diào)式,亦是上一曲牌調(diào)性的延續(xù)。以【清江引】為例:
傅雪漪判斷《醉?xiàng)铄窞椤坝衫デ拘滤睢块_頭,中間插入大段弦索調(diào),最后又以昆曲【清江引】作為結(jié)尾的一個(gè)套曲”,并得出“可以清楚地看到京劇的《貴妃醉酒》,完全是從弦索調(diào)演變而成”“吹腔、昆曲、弦索調(diào)咋唱的形式,而后流傳于皮黃舞臺(tái)上的一個(gè)過程”的結(jié)論。[4]由此證實(shí)了在康熙初期,已形成花雅聲腔并蓄、同本同臺(tái)的現(xiàn)狀。至于【新水令】靈活的轉(zhuǎn)調(diào)情況,可能與花雅聲腔之間靈活運(yùn)用有關(guān),也暗藏著聲腔交融演變的現(xiàn)象。
五、含昆北主調(diào)的六聲音階樂譜
周來達(dá)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了昆北的兩個(gè)主調(diào)do si la和sol fa mi,即“如要出現(xiàn)Si音,就必須出現(xiàn)176三個(gè)音;凡要出現(xiàn)fa音,就必須出現(xiàn)sol fa mi三個(gè)音” [5],而在《太古傳宗·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中,也出現(xiàn)了昆北的主調(diào)——《小妹子夜夜守空房》的【山坡羊】,每次fa都是在sol fa mi同時(shí)出現(xiàn)的情況下出現(xiàn)的。
“凡”每次出現(xiàn),必伴隨著“工、六”,且多為拖腔,且其所在字的音調(diào)“沖、撞、上、不、倒”為去聲字腔音調(diào),“你、心”雖不為去聲字但所占比例不大,故而《小妹子夜夜守空房》的【山坡羊】應(yīng)為昆曲北曲。
由上述可知,《太古傳宗·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大部分為五聲音階,包括本調(diào)記譜、借調(diào)記譜、五聲綜合,且以羽調(diào)式為主,商調(diào)式、徵調(diào)式次之,轉(zhuǎn)調(diào)多發(fā)生在板眼變換處。少有七聲音階樂譜,如《花子拾金》的【四邊靜】【道和】,反映了乾隆初期聲腔融合、花雅同本同臺(tái)的文化現(xiàn)象。
注釋:
[1]王耀華.中國傳統(tǒng)樂譜學(xué)[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498.
[2]"其中第二首《散曲》《僧尼會(huì)》《北蘆林》《金盆撈月》《踢球》中有少量fa、si出現(xiàn),按經(jīng)過音處理,不列為曲譜所用固定音。據(jù)譜集【凡例】云:“譜中所收各套有本無牌名者,則仿照《借靴》套首用【歌頭】二字之例,每套冠以【和音】二字,蓋此譜專以音節(jié)為工,不便另加牌名勉強(qiáng)牽合。”故而對(duì)于僅有【和音】【歌頭】者,將其每個(gè)唱段的結(jié)音標(biāo)出,以便觀察其規(guī)律。
[3]"本文所有譜例均為筆者根據(jù)劉崇德主編的《中國古代曲譜大全(一)》中《太古傳宗·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工尺譜解譯而來。劉崇德.中國古代曲譜大全[M].沈陽:遼海出版社,2009:677—744.
[4]"傅雪漪.明清戲曲腔調(diào)尋蹤——試談《太古傳宗》附刊之《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J].戲曲研究,1985(15):12—15.
[5]"周來達(dá).昆曲音樂研究——周來達(dá)戲曲音樂學(xué)術(shù)論文選[M].北京:中央音樂學(xué)院出版社,2017:05.
(責(zé)任編輯:崔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