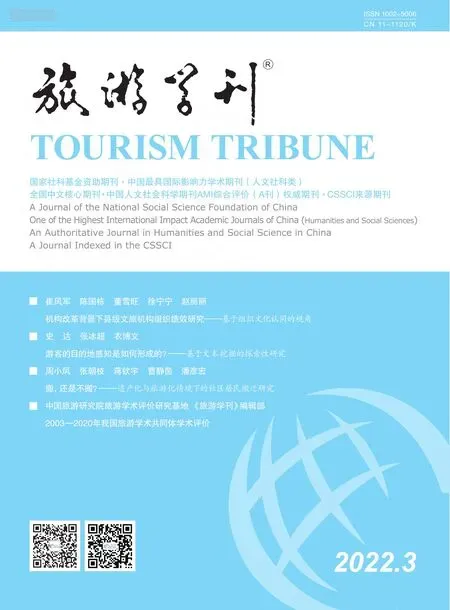新制度的來源、要素和形成
秦宇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3.001
制度是有組織的、得到確立的做事程序,是社會的構成規則,是理解社會運轉的鑰匙。制度不僅約束著組織和個體的行動,而且也被擁有能動性和變革能力的個體和組織創造和改變。換言之,制度創新不能僅用個體主義的理性選擇理論解釋——即個體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選擇合適的制度類型,也不能僅用宏觀結構主義理論解釋——即個體只能是制度的接受者。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旅游企業一直是服務業中制度創新的先鋒。對于那些做出了制度創新的企業而言,它們是在哪些情境下、如何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以新的方式行事的?為什么成功了?有何影響?對于那些未能實現制度創新的企業來說,為何無法脫離其慣有的方式行事?這些在現實中引入入勝的問題也是制度創新的核心理論問題。
一、新制度的來源
任何一個現代社會,都不可能只有一套制度體系,而是有多套并行的、相對宏觀的制度體系。美國社會學家Friedland和Alford(1991)將這些制度體系稱為制度秩序,并指出西方國家主要的制度秩序包括家庭、宗教、國家、市場等。每一個制度秩序都有獨特的組織原則、實踐和符號體系。處于多重制度秩序之中的組織和個人能夠意識到不同制度秩序中文化性規范、實踐和符號的差異,并將這些多樣性融入它們的信念、思維和決策行動之中。從而,制度創新所需要的能動性和使得能動性可行的知識,都來自不同的制度秩序,這影響著個體和組織的制度創新行為。簡言之,新制度來源于個體和組織——有意識地或潛移默化地——對宏觀制度秩序的解讀、類比、借用和組合。
Thomton、Ocasio和Lounsbury(2012)在《制度邏輯觀點》一書中將前述宏觀制度秩序擴展為7種,包括家庭、社區、宗教、國家、市場、職業和公司,還綜合、比較了不同制度秩序在合法性來源、權威來源、身份來源、規范的基礎、注意力的基礎以及戰略制定出發點等維度上的主要差異。這一擴展工作的理論含義極其豐富,包含了大量的思想。其核心認識是,不同制度秩序在各個制度維度上的差異存在潛在的矛盾和沖突,但這也使得組織和個體在解決組織問題時擁有了多重邏輯潛力。新制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來源于這7種制度秩序中不同的組織原則、實踐和符號體系。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飯店業開始摒棄計劃經濟體制下原有的運營模式,大量借鑒、學習并采用科學管理模式。到了世紀之交,如家、漢庭等企業又開創了連鎖經營的新模式。我們發現,上述3個階段的模式,分別與宏觀制度秩序中的國家秩序、職業秩序和市場秩序大致對應。招待所、星級飯店和標準化的經濟型酒店,是這3種制度秩序下的典型業態,而對這3類模式中制度變化的分析,都可以回到制度秩序之中尋找線索。例如,3種制度秩序下身份來源的差異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改革開放之前的招待所為何高高在上?高星級飯店行業中的各類媒體為何會定期公開披露總經理任命信息?還可以解釋某些經濟型飯店公司為何放棄了星級飯店管理公司對職業經理人在飯店業中工作經驗和資歷的要求,大量錄用從未有過飯店從業經歷的管理者。
二、新制度的要素
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在研究制度創新時有不同的分析重點。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研究重點是規制的制度(regulative),主要指各種明確、正式化的法律、規則及伴隨違反規則面臨的強制制裁;古典社會學家的研究重點是規范的制度(normative),主要指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往往與職業或人在社會中的角色相關聯;新制度主義理論家的研究重點是文化與認知的制度(cultural-cognitive),主要是指由外在文化框架塑造的內化認知框架。
Scott在其《制度與組織——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一書中將這3種制度要素綜合到同一個框架之中(表1),清晰表明了不同制度要素的基礎、運行機制及實現過程等方面的差異。
例如,規制制度的合法性源自對遵從法律要求;規范制度的合法性則來自與道德準則規范保持一致;而文化一認知制度的合法性是指行動符合社會文化中常見的意義框架。更重要的是,Scott還指出這3種制度要素并非相互替代,而是相互配合共同發揮作用——盡管有時某一種會處于支配地位。
我國旅行社業過去40年來的發展變化就體現出這3種制度要素的共同作用。國務院分別于1996年10月和2009年5月頒布的《旅行社管理條例》和《旅行社條例》,是規制的制度;大型國有旅行社企業(如國旅總社和中青旅)的制度創新則主要受到規范性制度要素(例如對國企的社會期望和國有企業運行的規則)的影響;文化一認知的制度要素,則可作為主要工具分析攜程、六人游、世界邦等在線旅行社企業如何改造傳統旅行社的行業實踐。
三、新制度的形成過程
某個新制度被制度創業者創立之后,要成為典型、普遍的原則和做事實踐,需要被制度化。Tolbert和Zucker(1996)將制度化劃分為“前制度化一半制度化一完全制度化”3個階段。前制度化的核心是制度的慣常化,也就是新的制度安排開始正式地出現在組織的政策和程序中。但是,這一階段采納新制度安排的組織不多,而且在具體實施上有很大的差異。半制度化階段的核心是客觀化,即組織中關于某一制度安排的價值已經形成了某種程度的社會共識。社會共識的形成取決于所謂的理論化工作的效果。即首先需要確定某種普遍存在且持續發生的組織問題,其次要為解決該組織問題的正式制度安排正名。理論化為新制度安排提供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合法性。一旦實現了客觀化,制度安排就開始了廣泛的擴散。完全制度化階段的核心是制度的沉淀,即新的制度安排得到了全面的采納并且長期維持下來。3個階段的主要特征見表2。
飯店接入OTA平臺是完整經歷上述3個制度化階段的典型制度安排。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前制度化階段,攜程地推團隊進入飯店洽談接入合作的時候,被斥為“騙子”的遭遇不在少數。在OTA們不同輪次的理論化工作——例如向飯店說明接入OTA可以帶來更新更多的客源并解決傳統客源渠道單一的問題——并且這些說辭在現實經營中獲得證據支持之后,這一制度安排快速擴散。目前,這一新制度已經得到全面采納并長期維持下來。新飯店開業,列入開業清單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接入OTA。到2017年年底,全國接入OTA銷售平臺的住宿設施已經超過40萬家。
四、結語和展望
研究制度創新,是理解中國社會和旅游經濟不斷轉型發展的核心(馬波,2007)。組織的制度創新是其中一個重要領域。組織不僅受到技術要求及資源依賴的影響,而且還深深嵌植于社會與政治環境之中并受到這些環境的影響,組織的結構與實踐映射出比組織更宏大的社會中存在的規則、信念和慣例。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經歷快速而重大的制度變遷,這些制度變遷源自各種制度秩序——國家、市場、職業、公司之間的競爭、矛盾和沖突。中國的制度變遷為我們認識組織和企業中新制度的來源、要素和形成提供了難得的研究機會。
本文介紹的幾個框架的應用顯然可以超越旅游企業研究領域。事實上,如果我們把旅游企業看作一種組織,我們就可以考慮將上述邏輯和框架作為主要的分析工具,應用到其他類型的旅游組織——大到世界旅游組織和各個國家的各類旅游監管部門,小到旅游目的地一個幾十人的小村莊或高校中僅有十幾人的一個旅游系。若我們將本文介紹的這幾個組織制度主義理論框架當作一種分析視角——例如用來分析飯店與OTA之間的沖突、或分析家庭一工作之間的沖突——則可以看到更大的應用拓展。我們期待制度研究領域能夠產生一批原創性成果,不僅促進對中國實踐的更好解釋,更重要的是通過提出并回答新問題增進國際學術研究知識體的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