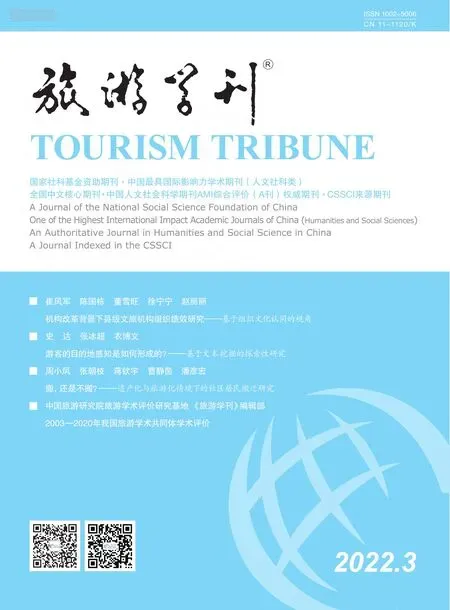城市旅游轉型與旅游制度創(chuàng)新的思維轉向
章錦河
Doi:lO.19765/j.cnki.1002-5006.2019.03.004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旅游發(fā)展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正由旅游大國向旅游強國闊步邁進,但也面臨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文化和旅游部門深度融合、轉向高質量發(fā)展等現(xiàn)實問題,而旅游制度創(chuàng)新則是解決中國旅游發(fā)展存在問題的關鍵與鑰匙。馬波教授在“2018《旅游學刊》中國旅游研究年會”上做了題為《開創(chuàng)旅游制度學派:契機、訴求與方法》的主旨報告,既是對現(xiàn)實困惑的回應,更是對理論創(chuàng)新的渴求,將有力推進中國旅游制度建設與研究的深入。
一、城市旅游轉型的發(fā)展態(tài)勢
城市旅游轉型既緣于城市轉型,又促進城市轉型。城市轉型包括但不限于資源枯竭型城市,是人口超齡、資源短缺、能源緊缺、生態(tài)脆弱、環(huán)境污染、交通擁擠、住房緊張等城市問題加劇背景下的必然選擇,是對過往城市發(fā)展理念與模式的反思。“低碳、智慧、開放、友好、共享”是城市轉型的新理念,“產業(yè)重組、空間重構、資源再生、服務提升、生態(tài)管控、政府治理”等是城市轉型的新主張,“生產型城市”向“消費型城市”轉變是城市職能轉型的新態(tài)勢。城市轉型的新理念、新主張與新態(tài)勢,契合了城市旅游轉型的方向與基本路徑。當前城市旅游轉型的態(tài)勢主要體現(xiàn)在10個方面:(1)從以往通過大項目、大投資招商的龍頭項目牽引式旅游發(fā)展模式轉變?yōu)榘l(fā)現(xiàn)與滿足市場需求,提供新型爆款小業(yè)態(tài)為主;(2)從內向性的旅游產品打造轉向外向性的旅游產業(yè)培育,旅游產品通過產業(yè)化的價值鏈延伸與整合,實現(xiàn)旅游價值的規(guī)模增長與溢出;(3)更加注重品牌,旅游品質是旅游品牌的基礎,旅游品牌既是旅游品質的象征,更是旅游品質的市場拓展、制約與保障;(4)旅游投資由政府主導轉向企業(yè)主體,從政府資金引導轉為企業(yè)、社會資本運作為主;(5)旅游績效考核由旅游人次轉向旅游收入,優(yōu)質客源市場的培育與吸引成為城市旅游提質增效的關鍵;(6)行為規(guī)范從各類旅游法律、法規(guī)、條例等制度剛性制約轉向旅游彈性規(guī)劃、指南、導則等制度柔性引領;(7)旅游市場監(jiān)管由文旅部門主導轉向多部門協(xié)同;(8)存量盤活代替增量發(fā)展成為實現(xiàn)城市旅游精明增長的重要路徑;(9)更加注重細節(jié),“成功在于細節(jié),特色在于積累”“特色蘊于細節(jié),匠心鑄就精品”的理念開始深入人心;(10)尋求靈活的發(fā)展機制,機制改革與創(chuàng)新是城市旅游轉型發(fā)展的重要保障。
二、旅游制度創(chuàng)新的思維轉向
制度關乎人的行為準則與規(guī)范,制度創(chuàng)新重在解決社會現(xiàn)實問題。城市旅游轉型發(fā)展所面臨的十大趨向實際上是城市旅游制度創(chuàng)新所面臨的制度環(huán)境,在此背景或環(huán)境下,城市旅游制度創(chuàng)新的思維轉向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6個方面:
第一,旅游制度視角從“供給端”到“需求端”。供給端導向的旅游制度建設遵循的是“我有什么?我能提供什么?我能更好服務什么?”的“我者”邏輯,強調旅游資源品質、產品質量、價格約束、服務規(guī)范、管理效能等制度建設,而需求端導向則是“他人需要什么?如何更好滿足他人需求?”的“他者”尊重,更注重旅游體驗、文化訴求、地方感、場所精神、主客互動、滿意度等制度設計。當前,城市社會資源旅游化、旅游資源社會化的雙向互動特征明顯,諸如商業(yè)休閑化(商業(yè)街區(qū)、商場等空間與設施的休閑利用)、服務社會化等現(xiàn)實變革,使得需求端導向的旅游制度設計與創(chuàng)新具有必要性與緊迫性。
第二,旅游制度創(chuàng)新主體從“政府”到“非政府”組織。“以人為本”是城市建設與發(fā)展的最高標準。政府部門往往是“供給端”的角色,對市場需求并不敏感,相比之下,各類旅游企業(yè)、行業(yè)協(xié)會、學會以及旅游公益性組織更能感知市場需求,勢必在旅游制度,尤其是非正式旅游制度建設上發(fā)揮主體作用。構建政府、NGO、企業(yè)、居民、游客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多方協(xié)商、互相促進的旅游制度建設主體體系,是城市旅游制度創(chuàng)新的重要保障。
第三,旅游制度類型從“規(guī)制/規(guī)范”到“認知”。美國社會學家Richard Scott認為“制度由規(guī)制性、規(guī)范性、認知性三大基礎要素構成”,也即,旅游制度可以相應劃分為規(guī)制性旅游制度、規(guī)范性旅游制度與認知性旅游制度。規(guī)制性旅游制度是剛性的,通過獎懲機制為受制成員提供積極或消極的激勵,如旅游法律、法規(guī)、條例等,遵循制度是工具理性的邏輯。規(guī)范性旅游制度強調制度對受眾的情感、價值與道德約束性,提出規(guī)范性期待,具有彈性,如各類旅游標準、導則、各種形式的旅游創(chuàng)建活動規(guī)范、旅游服務規(guī)范等。認知性旅游制度強調制度的受眾的內在建構,形成共同的價值觀與行動準則,如各類旅游指南、旅游信用等,遵循制度是價值理性的邏輯。
第四,旅游制度建設重點從“線下”轉到“線上”。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物流網(wǎng)、智能科技的飛速發(fā)展,線上旅游交易規(guī)模持續(xù)增長,旅游智能機器人服務指日可待,有關旅游餐飲、住宿、交通、景區(qū)點、旅游商品、旅游娛樂等傳統(tǒng)線下旅游產品與服務的法律、法規(guī)、規(guī)范面臨革新,而旅游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投資、運營、安全、銷售、物流、大數(shù)據(jù)、投訴處理等以及旅游智能機器人服務規(guī)范亟待構建。科技引領未來,旅游業(yè)是高科技應用的重要試驗田與高科技普及化的重要橋梁,“線上”旅游制度創(chuàng)新具有前瞻性與溢出價值,將成為智能時代人們生活的藍本。
第五,旅游制度形式從“單一”到“多樣”。跨界整合、產業(yè)融合、部門聯(lián)合、產品組合、中外結合等是全域旅游時代“旅游+”的核心要義。我國旅游制度形式相對單一,一般都是由各級政府,尤其是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制定與發(fā)布,且都是單獨成文,譬如《城市旅游服務中心規(guī)范》(LB/T 060-2017),優(yōu)點是針對性強,但由于缺乏部門溝通與協(xié)同,制度的落地性不強。“旅游+”是旅游部門勇于擔當?shù)墓ぷ鲬B(tài)度,而“+旅游”是旅游部門積極作為的工作方式,例如在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長江經(jīng)濟帶發(fā)展、特色小鎮(zhèn)、鄉(xiāng)村振興、大運河文化帶、交通驛站等建設過程中,拓展旅游發(fā)展空間,突出旅游功能與作用,必然要求多方溝通、協(xié)調與協(xié)同。旅游的“嵌入性”特質,使旅游制度形式多樣化將成為常態(tài)。多部門聯(lián)動與旅游制度嵌入其他制度文本之中,是旅游制度多樣化的兩種主要形式,這也是解決城市旅游用地、旅游服務中心、旅游驛站、旅游交通管制、旅游廁所、旅游公共設施、旅游公共服務等諸多現(xiàn)實問題的關鍵。
第六,旅游制度評價從“效率”到“公平”。制度的效率與公平是對立統(tǒng)一的關系,統(tǒng)一是因為兩者追求的目標具有一致性,對立在于兩者秉持價值觀的相異性。效率注重生產力,有量的屬性;公平則關注生產關系,有質的屬性。不同發(fā)展階段,公平與效率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具有差異性。在“全球政治覺醒(the massive global political awakening)”思潮的影響下,公平成為衡量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制度設計與創(chuàng)新的重要指示器,也是彰顯人文價值和人文關懷的出發(fā)點與落腳點。在當前城市有機更新、歷史街區(qū)振興、文化遺產活化、公共空間共享、公共設施均等化過程中,堅持居民需求導向(而非游客導向)、注重文化補償、強化地方性建構等涉及“公平性”的制度設計,無疑是尤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