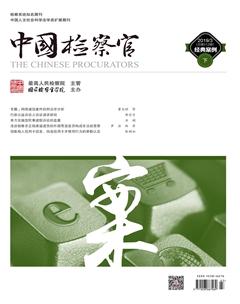“校園貸”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張艷
摘 要:隨著網貸消費逐漸深入大學校園,利用“校園貸”網絡分期平臺非法獲取財物的犯罪案件逐漸增多。行為人誘騙在校大學生在網絡分期平臺上辦理分期手機貸,在收取分期公司寄出的手機后套現的,是典型的利益型詐騙犯罪。被害人是學生,行為對象是學生對分期公司的貨物給付請求權,且行為人的欺詐行為與被害人對財產性利益的占有、轉移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秘密竊取他人身份信息后在分期平臺上辦理分期貸業務的,要區分被盜信息者是否已經在分期平臺注冊賬號。行為人竊取他人身份信息在分期平臺注冊賬號后辦理分期貸款的,構成詐騙,分期公司是被害人,行為對象是分期公司的財物;行為人竊取他人分期平臺賬號密碼辦理分期業務非法占有財物的,成立盜竊罪而非三角詐騙,被害人是學生個人,行為對象是他人的財產性利益。
關鍵詞:校園貸 財產性利益 占有
[誘騙學生辦理手機分期貸后將手機套現非法占有財物]
案例一:2015年7月被告人彭成通過微信聯系到其小學同學——山西工商學院在校學生許琪,稱在校大學生在分期平臺購買手機價格很低,并謊稱想借用許琪的身份信息為自己買部手機,分期貸款由其負責償還。后被害人許琪用自己的身份證辦理一個新手機號并將自己的學生證、身份證一并交給彭成。彭成用許琪的上述信息在人人分期平臺上注冊賬戶,并下單購買一部蘋果6plus手機。被告人彭成收到分期公司的手機后在大南門二手市場以4500元的價格將手機變賣套現。此后,被告人彭成以審核失敗未辦理成功為由,以同樣的方式先后誘騙許琪在趣分期、優分期、分期貸網站辦理四部蘋果6plus手機分期貸款,共計套現27500元人民幣,所得贓物用于個人揮霍。被害人許琪收到分期公司的催款賬單后發現被騙隨即報案[1]。
爭議焦點:該案在審理過程中,被告人彭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不存在爭議,爭議較大的是本案被害人是分期公司還是學生。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彭成隱瞞自己非在校學生的事實,冒用他人身份,在分期網站辦理手機分期業務,騙取分期公司手機,被害人是分期公司。另一種觀點認為本案被害人為學生許琪。筆者認為,本案是典型的利益型詐騙犯罪,被害人是學生,行為對象是財產性利益,理由如下:
(一)分期公司主觀上沒有錯誤認識,其交付財物的行為不屬于詐騙罪中的處分行為
在本案中,分期公司主觀上不存在錯誤認識。分期公司通過網站的初步形式審核,對注冊者(學生)的身份信息、學籍進行審核后授予信用額度;之后又通過面簽的方式,將合同內容告知學生,并對合同中分期購買的手機品牌、價格、分期數及最低還款額度予以明示,學生在分期合同上簽字,對合同內容認可并同意受合同的約束,基于以上形式和書面的審核,分期公司已經盡到審慎的審核義務,對處分財物的行為不存在錯誤認識。持分期公司主觀上有錯誤認識的觀點,認為行為人隱瞞自己冒用他人身份信息,使分期公司陷入了錯誤認識。筆者認為該觀點不能成立,理由是:一方面,買賣合同中,在名義購買人與實際購買人不一致的情況下,名義購買人不管出于何種動機,其與合同以外第三人就購買賣標的的約定,從債的相對性來講,效力只存在于名義購買人與第三人之間,且此種效力不得對抗分期公司;另一方面,從維護市場正常的交易秩序的角度來講,在合同雙方盡到審慎的注意義務和告知義務之后,合同一方出于信賴原則履行合同的行為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故分期公司依照合同約定發貨屬于交付行為,其主觀上不存在錯誤認識,其行為不屬于詐騙罪中的處分行為,分期公司不屬于本案的被害人。
(二)行為人以債權債務的概括轉移為由,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繼而處分了自己對分期公司的貨物給付請求權,行為人的欺詐行為與被害人的錯誤認識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
首先,本案行為對象是學生對分期公司的貨物給付請求權,系財產性利益,且被害人對財產性利益的占有取得與行為人的欺詐行為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本案中行為人在實施欺詐行為開始,被害人僅屬于具有一定信息或者身份的人,其“占有的僅僅是自己的信息”,且這種信息在刑法上不具有任何價值。學生從單純的信息“占有”到對財產性利益的占有是在行為人的逐步誘導之下實現的,這一過程可以認為是分期貸詐騙犯罪中的犯罪預備階段,具體體現為:第一步,行為人以借用身份信息購買手機為由騙取學生的手機號、學生證以后用學生手機號在分期網站注冊賬號、密碼;第二步,登陸分期公司網站,將獲取學生的身份證、學生證、手機號等身份信息錄入分期公司系統,分期公司后臺經過信息審核后給與學生與其征信對應的信用額度,即授信;被授信的用戶在分期公司享有可期待預借債權的利益,但這種利益是抽象的、觀念意義上的利益;第三步下單,行為人在分期網站商品頁面選擇手機的型號生成訂單,此時,學生享有的可期待利益進一步數量化、具體化,但這種利益是單方面的、不具有對抗性;第四步面簽,分期公司派學生所在的校園代表上門與學生簽訂書面合同,由學生確認合同內容并簽字、摁印,在這一環節行為人會事先聯系被害人,將面簽需要做的事項告知被害人。學生在書面合同上簽字即以合同的形式將財產性利益具體化、確定化,且這種財產性利益體現為學生與分期公司之間具有約束力且能夠主張的向分期公司發貨的請求權。最后,分期公司依據訂單進行發貨。上述過程,被害人所享有的利益逐步的從抽象的、觀念上的利益轉化為具體的、量化的、可轉移的財產性利益。
其次,學生主觀上陷入了錯誤認識,且其錯誤認識與行為人的欺詐行為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本案中,行為人以好處費進行利誘,借用學生身份、信息在分期平臺注冊賬號、購買手機并承諾分期還款,最終使學生陷入了錯誤認識。從實質上來講,被害人主觀上是因行為人承諾償還分期貸款而形成的對債權債務概括讓與的錯誤認識,屬于對待給付的認識錯誤;行為人客觀上隱瞞了自己不履行償還貸款義務并利用分期貸進行套現,且在騙取學生對分期公司的分期債權后,會使學生處于歸還分期債權的事實,行為人給予一定的好處費又進一步強化了被害人的這種錯誤認識。
再次,學生客觀上實施了處分自己財產性利益的行為。主張被害人為分期公司的一個重要的理由在于,分期公司客觀上有交付手機的行為,而學生并沒有任何交付財物的行為。筆者認為,該種觀點的錯誤在于將處分行為簡單的等同于交付行為,且對處分行為的認定沒有區分詐騙行為對象是財物還是財產性利益。區別于一般的對有體物的詐騙案件,被害人的處分行為體現為客觀有體物的轉移交付,在行為對象為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由于財產性利益一般表現為使債權的增加或負擔某種債務,而債即屬于雙方的意思表示,對于債權的轉移占有除交付債權憑證的客觀行為外,往往多表現為對債權轉讓的意思表示[2]。在分期手機貸案件中,如果說學生將信息資料、聯系電話交給行為人,并默認行為人使用上述信息在分期網站注冊賬號、密碼并下單,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其財產性利益憑證的處分,行為人占有了該財產性利益憑證還不能稱之為對財產性利益的排他性占有,因為按照分期平臺的規定,分期購買手機之時,還必須由業務代表上門與學生簽訂書面合同,在學生未簽訂書面合同之前,行為人僅僅是占有了沒有任何實質利益的權利憑證而已。
最后,本案行為人的行為何時既遂在審理過程中也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分期公司發貨之時為行為的既遂,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收到貨之時為行為的既遂。上述兩種觀點分別是失控說、控制說的體現。筆者認為,在行為對象為財產性利益的詐騙案件中,采失控說較妥,具體表現為債權的不可追及。在一般情況下,分期公司發貨之后,由于行為人掌握了收貨人的電話,分期公司在正常情況下,均會將手機交付與行為人,且此時被害人所負擔的債務已經形成,法益損害已經產生。而在學生簽訂合同之后、分期公司發貨之前,存在一個時間差的問題,期間,會由于學生的征信問題、分期公司庫存不足等問題出現砍單的情形,此時分期公司會取消訂單,這種情形下,構成詐騙未遂,詐騙金額以手機分期價格為準。
綜上,以好處費進行利誘,并承諾歸還分期貸款,騙取學生在分期網站辦理手機分期并套現的,構成詐騙罪,且是典型的財產利益型詐騙。
[秘密竊取他人身份信息辦理分期貸款非法占有財物]
案例二:2016年12月15日,被告人張瑄(山西工商學院在校學生)通過盜取舍友馮浩宇的移動手機SIM卡(18334790810),在馮浩宇不知情的情況下,以馮浩宇的身份在分期樂網站注冊賬戶并辦理2788元的現金分期貸款,后將涉案贓物用于網絡游戲。
案例三:2016年10月份至2016年12月份,被告人張瑄乘舍友閆宇星睡覺之際,盜竊閆星宇放于枕頭下的手機,登陸閆星宇手機上的“分期樂”網絡貸款軟件,辦理3000元分期現金貸款,并將所貸款項通過支付寶秘密轉移到自己的銀行賬戶。
法院最終認定被告人張瑄構成盜竊罪[3],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案例二、案例三中行為人均是通過竊取他人身份信息的方式在分期平臺辦理現金分期貸款繼而非法占有財物。筆者認為,被告人張瑄的行為不能一概認定構成盜竊罪,應當區分學生是否在分期網站注冊賬戶,而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構成盜竊還是詐騙,具體理由如下:
(一)行為人竊取他人信息后在分期網站注冊賬號辦理分期貸款的,構成詐騙罪,被害人為分期公司,行為對象是分期公司的財物
1.案例二中,學生馮宇浩不存在符合刑法上盜竊罪構成要件中的占有,也就不存在占有被打破,故被告人張瑄的行為不構成盜竊罪 。盜竊罪乃違背他人意志轉移占有的行為,系奪取占有型犯罪,故成立盜竊罪的前提必須是存在占有。日本通說認為,刑法上的占有是指對財物以支配的意思而進行的事實上的支配[4]。就事實上的支配而言,不僅單純的物理的、有形的支配,占有的存在與否應當根據性質、時間、地點和社會習慣等因素按照社會上的一般觀念來判斷。
首先,從學生的角度來講,行為人的行為打破的是學生對身份信息的占有;其次,行為人秘密竊取他人身份信息,后注冊賬號密碼,雖然學生是這種利益的名義占有者,但其沒有掌握分期貸平臺的賬號、密碼,其名義上的占有并不具有排他性,而行為人在事實上掌握了注冊信息、分期賬號、密碼,故行為人的占有具有客觀的排他性;再次,學生主觀上也不具有占有的意思,行為人竊取他人身份信息后注冊賬號的,整個過程學生主觀上并不知情,其并沒有認識到自己占有了對分期公司的貸款請求權。因此,學生主觀上既缺乏占有意思,在客觀上又不存在排他性的控制支配力,故學生不存在占有,那么在占有不存在的前提下,更不存在占有被打破的情形。
2.行為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騙取征信并辦理貸款的行為與法益侵害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案例二中張瑄的行為分為盜竊行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并在分期平臺上注冊、在分期平臺辦理分期貸款業務的行為。首先,盜竊他人身份信息的行為并不必然導致他人財產的減損,并且分期平臺賬號、密碼的價值無法具體認定。其次,行為人冒用他人身份騙取分期公司授信,分期公司存在錯誤認識。分期公司授信的基礎在于個人的征信,而征信即償還分期還款的能力,分期平臺在決定是否授信、授信額度有多大的前提均是建立在申請者的身份、收入等事實的判斷之上的。行為人的冒用行為,實際上是隱瞞自己不具有相應的分期預借現金的能力,以他人的信用騙取分期公司將預借現金處分給不具有還款能力的人。最后,行為人冒用他人分期平臺身份,向分期公司提交分期訂單,并通過掌握的注冊手機號,輸入驗證碼,使分期公司的審核人員陷入錯誤的認識處分了自己的財物。區別于行為人盜竊他人分期平臺的注冊賬號、密碼,分期平臺僅是對密碼進行核實,在他人未注冊賬號、密碼的情況下,分期公司的處分行為是建立在對注冊者信用資質審核及密碼驗證基礎之上進行的。故行為人的冒用行為與分期公司處分財物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被告人張瑄的行為構成詐騙罪,被害人為分期公司。
(二)在被害人已有分期網站賬號的前提下,行為人秘密竊取他人分期網站賬號、密碼辦理分期貸款的,構成盜竊罪,被害人為學生,行為對象為學生對分期公司的貨物請求權
案例三中,對被告人張瑄行為的認定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構成三角詐騙。分期網站用戶開通分期業務時,分期平臺對被害人身份信息的審核后與被害人簽訂分期合同,事實上以合同的形式取得了對被害人分期債權的處分權,因此,分期平臺客觀上具有處分權。賬號和密碼是分期平臺對被害人身份的驗證,行為人隱瞞自己盜竊他人網站賬號、密碼的事實,冒充真正的持卡者,在分期網站輸入賬號、密碼,使分期平臺陷入錯誤認識,處分了學生的分期債權,故構成三角詐騙。而另一種觀點認為,分期公司不能被騙,其主觀上不存在錯誤認識,張瑄的行為構成盜竊罪。
筆者認為,分期網站(分期公司)不存在錯誤認識,行為人張瑄的行為構成盜竊罪,理由如下:
1.分期平臺雖具有處分權限,但缺乏處分意識,被告人張瑄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詐騙罪中的處分意識,是指被害人認識到財物的占有或者利益的轉移及其引起的結果,是被害人基于自由意志支配下對利弊權衡后作出的選擇。主張構成詐騙罪的理由之一是,行為人隱瞞自己非真實的買家而冒用他人賬號辦理分期貸款,這種觀點隱含的邏輯前提是行為人實施了冒用他人身份和在分期平臺輸入賬號、密碼兩個客觀行為,而分期平臺的識別流程中,僅僅是對賬號密碼的識別而不包括對使用賬號、密碼人的身份的識別,行為人輸入驗證碼后,分期網站平臺僅僅能做出正確與錯誤的非此即彼的判斷,其不能基于利益權衡而做出不同選擇的行為,只是簡單的執行指令的行為,故輸入賬號密碼的行為與分期公司處分財物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而冒用行為與錯誤認識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故分期公司的交付行為不屬于詐騙罪中的處分行為。
2.被告人張瑄的行為構成盜竊罪。被告人張瑄未經他人同意,竊取他人的財產性利益憑證——分期平臺賬號、密碼,后在分期平臺辦理分期貸款業務,將他人占有的對分期平臺的財產性利益轉移至自己的占有之下,其行為構成盜竊罪。
注釋:
[1]太原市小店區人民法院(2017)晉0105刑初769號刑事判決書。
[2]參見張明楷:《論詐騙罪中的財產處分行為》,載《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8期。
[3]太原市小店區人民法院(2017)晉0105刑初814號刑事判決書。
[4]參見周光權:《刑法上的財產占有概念》,載《法律科學》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