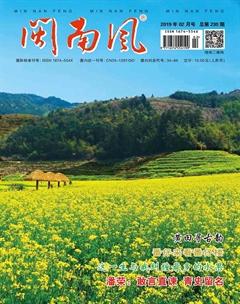村莊,無法抹去的回憶
黃勇英
最近在閱讀劉亮程先生的《一個人的村莊》,深受觸動,他引發了我對村莊的記憶和關注。
劉亮程是一個大西北土生土居土長的人。作為一個農民,他“常常扛著一把鐵锨”,“與蟲共眠”,飼養牲畜;作為一個作家,他是整個村莊“唯一的旁觀者”,“和那些偶爾路過村莊,看到幾個生活場景便激動不已,大肆抒懷的人相比”,他“看到的是一大段歲月”,而這歲月在他的眼中又是那樣的與眾不同。這歲月有他關于童年的所有快樂和悲傷,也有巨大的恐懼和孤獨。村莊有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仿佛田野里到處瘋長的蒲公英,帶著淡淡的苦澀和四處飄飛的夢想。
小時候我跟母親去外婆家,交通工具是一輛自行車。外婆家在一個很山里的地方,地名叫“月家窟”(只是諧音,三個字準確寫法不明),那只能算是一個很小村莊,有十來戶人家。我至今不明白為什么人要住到那么偏遠的地方去,這種生活更像是一種自我隔絕。村前有一棵大樟樹,樟樹上掛了一個大鐘,村里要召集人就會敲響大鐘。大鐘的聲音在空曠的山里回蕩,有時有“嗡嗡”的回音。外婆家養了幾只大鵝,有時我們幾個小孩在屋旁玩,大鵝就追著我們跑。有一次一只大鵝叼住我的褲腳,我放聲大哭,悲切的聲音招來了正在喂豬的外婆,她趕走了大鵝,還塞給我幾個野生的紅艷艷的“萢”。看在那幾個野果的份上,我總算轉悲為喜,但是自此以后,我就對鵝產生了嚴重的恐懼。至今看到鵝我還是心有余悸,它們昂著頭的姿勢有著不顧一切的勇猛。
“月家窟”,那是我看過的最小最遠的村莊,我的童年和它息息相關。它給了我奔跑和自由的記憶,滿山的映山紅和野果,蘊藏著一個孩子膚淺的快樂。這種膚淺的快樂是城里的孩子無法感受到的。而我的外婆和舅舅們,他們則帶著村莊給予的淳樸和善良,最終離開它,走向繁華的小縣城。在我看來,一個人即便身體離開了他曾經生活過的土地,他的靈魂依舊會偶爾回去。因為那里藏著來時的路,藏著最純粹的親情和友情,藏著生活最初的愿望,關于生存和繁衍的愿望。那是一個人活于塵世的根本追求,也是歲月終究無法抹去的記憶。
劉亮程在《一個人的村莊》中寫道:“所有的人在朝一個叫未來的地方奔跑,跑在最前面的是繁華都市,緊隨其后的是大小城鎮,再后面是稀稀拉拉的村莊,黃沙梁太小了,邁不動步子,它落在了最后面。”我不知道那個藏在“月家窟”的村莊是不是還在,長大后我就再也沒有去過。外婆和舅舅們都搬到了縣城,他們也沒有再回去過。那個帶給他們溫飽和愛恨的地方估計沒有什么人再留守在那里,因為那里實在是太偏僻了。一個偏僻的村莊終究會被淘汰而荒蕪,因為創造村莊的人總要往未來奔跑,不管你是否愿意。有些時候,我們總是身不由己,我們被卷進城市的漩渦,而忘記安靜和簡單的生活。
這兩年到一些鄉鎮走訪,也看到一些村莊。這些村莊和我記憶中的村莊很不一樣。在這些村莊里,我看到新建的安居樓和公園,可是我再也看不到炊煙升起,聽不到嗡嗡作響的鐘聲。這里幾乎看不到什么年輕人,只有一些老人和孩子。在我記憶中的那個充滿野性的村莊已然死去,這些看似新鮮的村莊讓你看不到蓬勃的活力,它們就像村子外還沒有盛開就已經死去的桃樹。很多的新房到了晚上沒有亮起燈盞,只有黑洞洞的窗戶散發出無法言說的寂寞。村莊越發沒有聲音,仿佛一個漸漸患上失語癥的老人。
高建群先生在他的小說《大平原》中這樣說到:十年以后,哪里還有炊煙升起的村莊?其實已經不用十年了,因為我們正在失去村莊,村莊的記憶也正在逐漸模糊,那渺渺炊煙逐漸將成為我們夢里的魂牽。是的,我們正在失去村莊,我們走進了更現代化的生活。我們逐漸離開熟悉的土地,就像四處飛舞的蒲公英,最終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落腳。那些鋼筋水泥建造的高樓大夏,將我們困在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