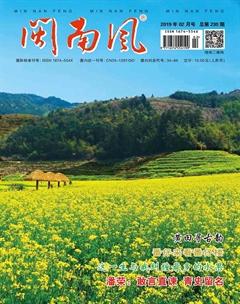我家的變遷
楊躍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家如沐春風,家和業興,先后幾次搬遷,家也就一次更比一次寬敞舒適,一次更比一次幸福溫馨。而家的變遷,猶如歷史長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又像歷史進程中一個小小的里程碑,它見證了改革開放風起云涌的40年,可以說我家住房的變遷,是中國農村群眾生活巨變的縮影。
聽母親說,半個世紀前,她嫁給父親時,家是既簡陋狹小,又陰暗潮濕的低矮房。地板是泥土的,房門是自制的,床板是磚頭墊的。當時,父親與大伯剛分家,爺爺奶奶跟著父親,一家六七個人口,擠在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祖屋里。母親回憶說,當時家里最值錢的家當,便是一張殘腿斷臂的飯桌和一個缺口歪脖的米缸。
后來父母辛勤勞作,省吃儉用,家里便有一點小積蓄,加上向鄰居借來幾塊銀元,對祖屋進行修繕,還添置了一張新娘床,一只床頭柜和梳妝臺。父親說,等日子好了,還要給母親建新房。這是父親,作為一個男人給自己心愛的女人最莊重的承諾,也是父親心中的夢想。為了踐行一句真摯樸實的承諾,實現心中的夢想,父親的一生在追夢的道路上沐風櫛雨,篳路藍縷。
20世紀60年代初,家鄉一場突如其來的特大洪水災害,把家里的土屋沖垮,本不牢靠的土屋夷為平地。在寄人籬下半年后,父親決定舉債自建新房,以遮風擋雨。父母風雨同舟,印制土塊,用于砌筑墻體,四處撿來不成規則的磚頭石塊作為地基石,向鄰居購買、賒欠舊杉木,做屋梁和椽子。沒有花磚墁地,而是鋪設次品的土磚。當時沒有專業建筑隊,父親請來木工、瓦匠幫忙,土洋結合,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建設,兩間有模有樣的新房終于落成。
在人們看來,兩間并不起眼的土屋再普通不過了,但在我們心中,是那樣的唯美壯觀,是那樣的溫暖珍貴,因為土屋一磚一瓦,一草一木無不傾注了父母心血。
母親清楚地記得,搬家時,沒有鮮花、沒有請客、沒有新家具。床鋪和床頭柜是從洪水淹沒的泥土中挖出來的,雖已然面目全非,搖搖晃晃,經鐵線纏繞、鐵釘加固,還是可以安睡的。所幸的是一張掉了半截的舊飯桌,還有奶奶的嫁妝——那副古樸老舊的睡眠床,沒有被大水沖走,靠在墻角里還能使用。一家三代肩挑手提,帶著并不值錢的生活必需品,第一次悄然搬家。
新家為兩間占地約50平方米、單層加閣樓的土木結構的瓦房。屋頂呈人字形,在屋脊和屋瓦上壓磚頭,以防狂風驟雨吹落稀薄的瓦片。左右兩門進出,隔墻打開通道,兩間相通,邊墻和后墻設有方形木質窗戶。在走廊邊上利用兩面墻體用磚頭壘砌大灶臺,用大黑鍋燒柴火做飯菜、煮豬食。天長日久的煙熏火燎,黑乎乎的墻體宛若烽火狼煙。
屋子雖有兩間,依然十分擁擠。奶奶的房間,既是臥室、餐廳,又是儲藏室。地瓜、木薯、稻谷、小麥、米缸、蔬菜……都要往里面裝。為了充分利用空間,奶奶常常把殘羹剩飯等食品裝在竹籃里,掛在屋梁上,那晃蕩的籃子勾魂似的誘惑著我們的肚皮。父母的房間擺放兩張床鋪,一只床頭桌,兩只破舊的木柜,只剩一條不足1米寬的通道。沒有衛生間,就在門后的墻角放著陶瓷尿缸,尿缸抵近床頭,臭氣彌漫在窄小的空間里。有時家里來了客人,母親就用洗腳桶蓋在上面,以防臭氣散發。窗外的黃牛很不善解人意,常常在天剛拂曉時,嗒嗒嗒……機關槍掃射似的拉出一地糞尿。人畜排泄物氣味混雜,令人難以入眠。后來,兄弟姐妹多了,就輪流跟奶奶睡,再大一點就寄宿鄰居。
雖是瓦房,卻擋不住狂風驟雨的肆虐。晴天閃金光,雨天響叮咚,這是我家的真實寫照。風雨飄搖的老屋,最讓家人擔驚受怕。每逢風雨交加,就得全家上陣,端上鍋碗瓢盆接天水。而父親頭戴斗笠,身披蓑衣,冒險架梯爬上屋頂,匍匐著身子修理瓦片——“補天洞”,珠子般的雨點敲打在他的臉上,一不小心就會被狂風刮倒或滾下地面,那后果不堪設想,家人總是為他捏了一把汗。每次下來,父親總是渾身濕透,不知是雨水、汗水、還是淚水。
當時,沒有自來水,家家戶戶到井邊打水。我家離水井有200米遠,小時候,我跟哥哥常到井邊挑水,回來倒進水缸里飲用,用水很節約,洗澡時木質臉盆只盛六七分滿就遍身擦洗。
時光流逝,歲月如梭。我們全家在簡陋、窄狹的老屋里過著蝸居生活整整20年。老屋猶如一張變得發黃的圖紙,記錄了我童年幸福的生活,寫滿了父母的艱辛,描繪了時代的變遷。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猶如一夜春風,吹遍祖國大地。我的家鄉和廣大中國農村一樣,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發展多種經營。父親農閑時,打短工、做生意、搞運輸,增加家庭收入。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全家人口增至11個。為改善居住條件,父親又開始謀劃建新房。由于我們兄弟多,父親深謀遠慮,以地換地,整合地塊,向上申請可建4間房子的宅基地,量力而行,分期建設。1981年8月,我師范畢業,家里第一間新樓房破土動工。
當時農村建房為防水災,往往要建兩層高。地基用沙石干砌灌水夯實,一層用方形或條狀的花崗巖壘砌成石墻,二層用土窯燒制的紅色土塊筑成磚墻,層層疊疊的瓦片覆蓋屋頂。石材是請惠安一帶的專業打石師傅打制,用人力獨輪車從山上運回來的。鋼筋、水泥、杉木都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緊缺物資,民房很難申請得到。家里建房時,用柯木代替杉木,用石灰代替水泥,歷時半年的建設,一座石木結構的二層嶄新樓房拔地而起。
新樓房兩層面積共有100多平方米,坐南朝北,通風透氣,門口寬闊平坦。搬遷新房時,家里安裝電燈,架設廣播,燃放鞭炮,殺雞宰鴨,還添置部分新家俱,過節似的歡歡喜喜,熱熱鬧鬧。“從此,我們再也不怕刮風下雨”,父親愧疚地說。
不久,我家又在門口建一間約20平方米的廚房,挖一口10多米深的水井,安裝抽水泵。當第一次用上自來水時,母親久久凝視著白花花的井水,緩緩腰彎如弓,雙手捧水,深深地喝上滿滿的一口,清冽甘甜的井水,順著喉嚨流進肚里,頓時,在她臉上綻放出如清新淡雅,不飾雕琢的花兒。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家的生活日漸紅火。七兄弟、兩妹妹一個個長大成人,成家立業,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全家人口增至一二十個,在當地是個大家庭。先后建成一排5間的二層樓房,配套建成5間廚房,有土木結構、石木結構,也有鋼混結構。“從今天開始,你們各自獨立門戶。給你們的財產有限,今后要靠自己奮斗。”父親選擇良辰吉日,把我們叫到跟前,語重心長地說,“兄弟分家后,要和睦相處,勤儉持家。”父親語氣低沉,眼眶濕潤。那年,父親剛滿60歲,他的話成了我家守望和傳承的好家風。
光陰荏苒,白駒過隙。轉眼我們在父親建造的樓房里幸福地生活了20多年,走過了人生中最寶貴、最美好的歲月。然而,滄海桑田,時過境遷,當年風光一時的“豪宅”,已然成了老屋。屋里設施不配套,水井不夠三四十個人口飲用,進出不便,屋頂漏雨,墻體裂縫,墻壁斑駁……在周遭鱗次櫛比的高樓映襯下,顯得那么破舊蒼老。
2015年,老大和老五、老六先后在政府規劃的新村點,購買商品宅基地建新房。耄耋之年,且體弱多病的父親,執意要看看兒子的新家,在我和弟弟的攙扶下,親眼目睹正在施工建設的樓房,臉上露出了絲絲笑意。在他那被歲月刻滿刀痕的古銅色臉上,我讀懂了老人家的心愿:兒孫滿堂日子紅,家家再上一層樓。兩年前父親走了,遺憾的是他沒能分享兒子們搬新家的喜悅,沒能與兒孫們同屋共夢!
兄弟的新家是框架鋼混結構,四層半共有數百平方米,別墅套房設計,室內寬敞明亮,外觀整齊精美,道路寬闊筆直,環境清新優美,是個宜居宜業之家。
我和老四、老七在外工作多年,也在城里買房安家。每每回鄉走進老屋倍感親切,那里留下我童年的夢想和青春的憧憬,那里曾是我心靈的歸宿和溫馨的港灣,那里蘊藏著醇厚的鄉愁。清晨里,聽樹上小鳥啁啾而入神,望窗外細雨飄飄而發呆;月光下,與同伙追逐嬉鬧,聽老人談古論今,那情那景,浮現眼前,縈繞耳際。
日出日落,歲月更迭。在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大潮中,家鄉嬗變,家屋變遷。初秋的周末,我走進弟弟的新家,登高望遠,藍天白云下,綠草如茵,竹木蔥蘢,遠山聳翠,流水琮琤。龍眼樹、橄欖樹、香蕉林一串串果實掛滿枝頭。一排排、一幢幢別墅小洋樓沐浴在柔和的晨光里,裝修一新的紅瓦灰墻閃耀著光芒。匆匆出工的村民,迎著朝霞,快步走在寬闊的大道上,他們用矯健的步伐,邁向新時代,踏上新征程,追逐新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