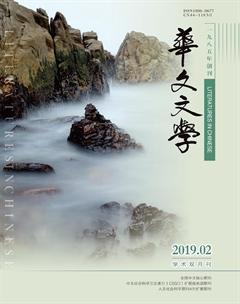臺灣資本主義化之下的倫理追尋
吳心越
摘要:本文將社會學評論與文學評論相結合,探討了陳映真小說中“故鄉(xiāng)”之意涵的變化,并分析了陳映真在其中寄予的個人情感、文化想象和社會歷史思考。文章指出,只有將其文學書寫放回臺灣資本主義化的社會脈絡中,才能夠更深刻地理解陳映真的社會關懷和替代性的倫理追尋。
關鍵詞:陳映真;故鄉(xiāng);資本主義化;臺灣;社會批判
中圖分類號:I20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9)2-0068-09
故鄉(xiāng)往往縈繞作家一生的創(chuàng)作,比如莫言書寫高密東北鄉(xiāng)始終抱著“極端的愛憎”和“混亂的激情”,賈平凹的商州也被他稱為“身體和靈魂的地脈”。對某些作家而言,故鄉(xiāng)甚至在源頭上型塑了他的創(chuàng)作風格和文化視野。陳映真在《后街》一文中談論他的創(chuàng)作歷程,也是從故鄉(xiāng)的童年記憶寫起,那里有臺灣光復后街頭落魄的臺灣人日本兵,在火車站前被打倒的外省客商,小學里為了班上一個佃農(nóng)的兒子甩過他一記耳光的吳老師,以及與吳老師在同一年被帶走的外省人兄妹。1993年,陳映真發(fā)表了《后街》,彼時的他回望故鄉(xiāng),埋下的似乎都是他思考的伏筆和小說人物的原型。這些故鄉(xiāng)的人物、場景,究竟是56歲的陳映真對過去的選擇性重構,抑或它們的的確確是陳映真童年記憶中的深刻烙印,在冥冥中召喚著他后來對白色恐怖、兩岸分斷和臺灣人殖民經(jīng)驗的關注,我們不得而知,或許兩者都有。但我們大概可以從中體會,陳映真對他的故鄉(xiāng)鶯鎮(zhèn),大抵并非保持著現(xiàn)代性體驗下的所謂文化懷鄉(xiāng),鶯鎮(zhèn)也沒有奠基他個人某種濃厚不可解的鄉(xiāng)土情懷。然而在陳映真的小說中,“故鄉(xiāng)”卻是一個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話題,從早期的《故鄉(xiāng)》《死者》《祖父與傘》到后來的“華盛頓大樓系列”、《山路》三部曲以及《忠孝公園》三部曲,“故鄉(xiāng)”在其中始終都是頗為關鍵的敘事元素,自然也承載了重要的意涵。
“故鄉(xiāng)”是空間上的故里,同時也是時間上的過去;“故鄉(xiāng)”也可以是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精神故土、文化淵源。“故鄉(xiāng)”意味著已經(jīng)發(fā)生了的告別,和終究要面臨的繼續(xù)流離或回歸的未來,它也總是在當下、未來與過去之間產(chǎn)生一種對照甚至緊張關系。陳映真的小說敘事鑲嵌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歷史脈絡之中,時間和空間上的斷裂與折返是不可回避的主題。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梳理陳映真小說中“故鄉(xiāng)”之意涵的變化,以及它背后所呈現(xiàn)的社會歷史變遷,并探究陳映真在其中寄予的個人情感、文化想象和社會歷史的思考。
一、左翼青年的彷徨:
“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
“故鄉(xiāng)”第一次作為陳映真的小說主題出現(xiàn),是1960年9月發(fā)表于《筆匯》的小說《故鄉(xiāng)》。然而這個故鄉(xiāng)不僅異常缺水,而且常年籠罩在陶瓷工廠的煤煙底下,樹木熏得枯萎,麻雀也一身煙灰,沾著一身煤屑的人們竟分不清是男是女。故鄉(xiāng)既不美麗迷人、令人思戀,我與故鄉(xiāng)的親人也早已隔膜至深。《故鄉(xiāng)》中的哥哥曾是受我崇拜的理想者,最初懷著虔誠的基督信仰和社會主義理想投身于焦炭廠做一名保健醫(yī)生,然而隨著父親咯血而死,家道中落,昔日的理想者也隕落為放縱邪淫的魔鬼,娶了一個娼門的賭婦,故鄉(xiāng)的家早已成為賭窟。于是,故鄉(xiāng)成了夢魘,成了我要逃離的地方——
我不回家,我要走,要流浪。我要坐著一列長長的、豪華的列車,駛出這么狹小、這么悶人的小島,在下雪的荒脊的曠野上飛馳,駛向遙遠的地方……
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①
陳映真在署名許南村發(fā)表的《試論陳映真》一文中,對自己早期小說中對故鄉(xiāng)的避拒以及自我放逐進行了闡釋,認為這是“悶局中市鎮(zhèn)小知識分子的濃重的感傷的情緒”,由于養(yǎng)父去世,家道遽爾中落,“這個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時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這種由淪落而來的灰黯的記憶,以及因之而來的挫折、敗北和困辱的情緒,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種蒼白慘綠的色調(diào)的一個主要根源”②。因而,在陳映真的闡釋中,這是類似于契訶夫所表現(xiàn)的社會轉(zhuǎn)型期自由知識分子的普遍性狀況:雖然敏感于時代的頹壞與更迭,卻無力于投身自身所認同的新世界的建設,因而便只有絕望、憂悒、自我厭棄與自我放逐——這便是《故鄉(xiāng)》中的我,最后“投進了繁華的、惡魔的都市”,揮霍著父親留下的人壽保險金,追逐著女子,過上了墮落浪蕩的生活。
趙剛認為,閱讀陳映真早期小說如果能夠超越這種“現(xiàn)代主義”式的理解,更可以挖掘其中多層次的存在狀態(tài)和豐富的思想意義③。《故鄉(xiāng)》顯然是指向自我的懺悔錄式的小說,但除了“我”之外,故事中我的哥哥,未嘗不是陳映真的另一個投射。懷抱理想的左翼青年必然要面對主體內(nèi)部的緊張狀態(tài),既有著高蹈的改造社會、投身民眾的熱情,又面臨著世俗中的現(xiàn)實自我,后者是充滿缺陷的,被種種下沉的力量拉扯(諸如青年男子的性欲)。于是理想者的淪落與崩潰是陳映真早期小說的常見情節(jié),《故鄉(xiāng)》中我的哥哥,《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鄉(xiāng)村的教師》中的吳錦翔,太陽神流轉(zhuǎn)隕落,天使淪為魔鬼,最終或瘋或死,可謂同一敘事的三種版本。陳映真在《后街》中寫道:“他從夢想中的遍地紅旗和現(xiàn)實中的恐懼和絕望間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總是懷抱著曖昧的理想,卻終至紛紛挫傷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避開了他自己最深的內(nèi)在嚴重的絕望和自毀”。④再進一步具體到左翼青年在1960年代臺灣的狀態(tài),他們通過隱秘地閱讀馬克思,閱讀中國30年代的左翼文學懷抱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對對岸的紅色中國充滿向往,如同心中熊熊燃燒著熾熱火焰,但這理想無從示人,既不可能結合同志,也無組織可依靠,更談不上任何實踐的可能性;他們心系一個理想國度,但身之所處卻是國民黨統(tǒng)治之下反共的、肅殺的臺灣社會,未來不來,又拒斥當下,可謂在那“白色的、荒茫的歲月中”無地彷徨,又從哪里去尋找安頓身心的故鄉(xiāng)呢?
我認為陳映真早期小說對“故鄉(xiāng)”的描寫,呈現(xiàn)了鄉(xiāng)土臺灣的“人間景象”,其中包含陳映真對社會現(xiàn)實的思考和復雜的情感。比如吳錦翔從婆羅洲的戰(zhàn)場返回故鄉(xiāng),懷著一腔改革的希望和愛人的熱情,然而村莊里的人懶散又呆板,過著日復一日“宿命的、無趣味的生活”,甚至孩子們也是局促且無生氣的;故鄉(xiāng)的人們也熱衷于作為“看客”,嚼著別人的舌根;《死者》中林鐘雄的故鄉(xiāng)蒙著一層森森的陰氣,一家人圍繞著將死未死的生發(fā)伯。而讓老人臨終之際仍放不下的,是這“敗德的莊頭”里自己媳婦私通的事情。但作者本人也現(xiàn)身評論,“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們是一群好淫的族類。因為他們也勞苦,也苦楚,也是赤貧如他們的先祖”。陳映真筆下的鄉(xiāng)土臺灣在某種程度上有對魯迅的繼承,他分明看到了那里的貧窮、破敗,人們的愚而不安,他也批判,也渴望改造,但對底層人民艱困的生存狀態(tài)依然有著深切的同情共感,而不是帶著知識精英的啟蒙姿態(tài)與之切割。就如陳光興所言,“對吳錦翔/陳映真而言,作為中國人,必須概括承受祖國所表現(xiàn)出的愚昧與不安,中國不是一個理念,是一個要誠實直面的歷史復合體,充斥著多面性的矛盾”⑤。
二、失落的土地:“田水汩汩地往外流去”
時間到了1960年代,用一句最常見的形容,臺灣的經(jīng)濟開始起飛。農(nóng)業(yè)社會逐漸轉(zhuǎn)向工商業(yè)社會,勞動密集型的工業(yè)生產(chǎn)遍布臺灣。國民黨采取“工業(yè)取代農(nóng)業(yè)”“低廉工資代工”等經(jīng)濟措施,大力發(fā)展出口導向型經(jīng)濟。不僅在經(jīng)濟層面,整個臺灣在文化層面也欣然擁抱資本主義全球化,美國式的現(xiàn)代化想象和都市文明占據(jù)了價值的高地。而1966年之后,陳映真的小說視野從內(nèi)向的自我省視逐漸轉(zhuǎn)向?qū)ν獾纳鐣泻蜌v史書寫,臺灣的社會變遷,以及其中知識分子、外企白領、底層勞工、農(nóng)民的生活經(jīng)歷和思想狀況,皆成為陳映真敘述的主題。從1966年的《最后的夏日》開始,直到陳映真的最后一篇小說《忠孝公園》,其實都涉及這樣的情節(jié),所以我在這里就不再做出社會批判和歷史書寫的階段分期,而是按照陳映真的敘事內(nèi)容來組織論述。
我認為1966年之后,陳映真小說中對故鄉(xiāng)的描寫,首先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社會學式的考察,尤其呈現(xiàn)出臺灣社會轉(zhuǎn)型過程中城市與鄉(xiāng)村的沖突,農(nóng)業(yè)文明與工商業(yè)文明的價值背離,延續(xù)了馬克思一脈的資本主義批判。例如在《忠孝公園》中,陳映真對1960年代末的臺灣農(nóng)村社會有一段這樣的描寫:
欣木二十四歲上下的那些年,種稻子的收入已經(jīng)遠遠追不上肥料、農(nóng)藥和日用品的開銷,村鎮(zhèn)上的年輕人逐漸到城市里去打工。但欣木不一樣。“阿爸,我想到外頭去,跟著人開個鐵工廠。”欣木說。他的朋友坤源在臺北三重一家不銹鋼加工廠當了幾年工人。“貿(mào)易公司來訂貨外銷。賺錢快。”欣木說。林標沉著臉,不肯答應。直到光是種稻實在已經(jīng)打不開生活開銷時,有人來牽線,林標把地賣給了臺北來的一個“李董”去蓋房子。欣木拿了地價的三分一,帶著女人和三歲大的小月枝遠走臺北三重……⑥
學界一般將1960年代中期視作臺灣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分水嶺。1968年后農(nóng)村土地利用程度開始下降,從事農(nóng)業(yè)越來越不足以糊口,農(nóng)村貧窮化迫使大量人口逃離農(nóng)村,光是1966年到1976年之間,農(nóng)業(yè)就業(yè)人口占總?cè)丝诒壤蛷?5.01%下降到26.71%。大規(guī)模的離農(nóng)、貧窮化與兼業(yè)化可以說是1960年代以來臺灣農(nóng)村結構變遷的基礎軸線⑦。陳玉璽也在《臺灣的依附型發(fā)展》中談到,1960、1970年代,政府通過對農(nóng)民的高賦稅,壟斷肥料價格,以行政手段干預農(nóng)產(chǎn)品市場價格等手段榨取農(nóng)業(yè)剩余。例如書中援引1972年《聯(lián)合報》的新聞報導:“臺灣省政府最近要求‘中央政府稍微提高米價,強調(diào)提高米價將會使幾十萬戶小農(nóng)家庭直接受益。但是,‘中央政府不予同意,主要理由是這么做可能會影響物價。”⑧
林欣木最終還是離開了他的故鄉(xiāng),投身于“猬聚著小型地下工廠的、空氣污濁、卻沸騰著對于成功發(fā)家的強烈欲望的三重市”,然而遭逢石油危機工廠倒閉,林欣木寧可流浪露宿街頭,再也沒有回去過。在這里,“故鄉(xiāng)”意味著臺灣現(xiàn)代化過程中沒落的農(nóng)村,意味著那個一去不復返的以自耕農(nóng)為基礎的鄉(xiāng)土世界。無論原因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局限性,抑或國家與資本的聯(lián)手壓榨,總之1960年代末開始,臺灣的農(nóng)業(yè)凋敝、農(nóng)民貧困流離是令陳映真深感痛惜的社會事實。另一方面,陳映真還指出了城市化過程中的土地開發(fā)對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造成的另一重影響,表現(xiàn)在《歸鄉(xiāng)》這篇小說中——楊斌老人朝思暮想的故里和親人也在歷史的洪流中變了樣。
1970年代,都市不斷擴張,“土地凡沾上城市發(fā)展的范圍,點石成金一般,地價就節(jié)節(jié)哄抬,造就了一批生活穿著土氣,卻家財數(shù)億的農(nóng)民暴發(fā)戶”。楊斌老人的二弟賣了地發(fā)了家,從此卻“全變了樣”。蜂擁的人群上門來拉投資,當說客,原本老實樸素的這位二伯父,不久就買了新車,賭博喝酒養(yǎng)女人,花天酒地。他的大兒子也靠著土地金開酒家、炒地皮,還選上了議員。這二伯父一家被金錢和利欲蒙了眼,不僅謀奪楊斌老人的地產(chǎn),連他這個親人都不認。
二伯父一家不就是臺灣土地開發(fā)中典型的“田僑仔”嗎?他們不是受資本或國家剝削的農(nóng)民,反而像是抓住了歷史的機遇一下子“翻身”成為有錢人。然而貨幣經(jīng)濟和市場化邏輯的入侵,對傳統(tǒng)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沖擊,一筆巨大的意外之財使得農(nóng)村人原有的價值體系和生活規(guī)范被打亂,金錢甚至瓦解了最親密的社會關系,使得夫妻成仇,手足反目。
作家楊渡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對“田僑仔”也有過相似的描述。他寫到,臺灣大部分的地主都是因為50年代的土地改革才有了一片耕作的土地,大多“惜地如惜生命之根”,不會有人愿意變賣祖產(chǎn)。但如果長輩不在,兄弟經(jīng)濟情況不一,就很容易賣了土地分家。原本淳樸的農(nóng)民一夕暴富,但在他們原有的生命經(jīng)驗中,只有稻米成熟、存放糧店,有需要再賣出換現(xiàn)金以應生活所需,所以他們對現(xiàn)代資本的運用毫無概念,一旦坐擁大筆資金就揮霍無度起來:買金條,買進口車都還算好,有的農(nóng)民拿到錢,不知如何花,硬是在酒家玩了一年多,拋妻棄子,包養(yǎng)女人;在大酒家把錢敗光了,再去小酒家,靠向兄弟借錢度日,最后才拖著一身病回家⑨。
城市的金錢涌入農(nóng)村,也改變了人與土地的關系。《忠孝公園》中,林標老人在分到土地,成為小自耕農(nóng)的那一年,“心喜得不知所措,就在屋后種下兩棵龍眼樹苗”,早早晚晚悉心澆水。等到龍眼樹蔥翠如蓋的夏天,便給了這全家一片蔭涼。“當其中的一棵龍眼樹忽然開出黃色的碎花的那個夏天”,兒子欣木娶了親,“第二年,吃過第二次收獲的龍眼,生下了孫女月枝”。這一小段敘述非常優(yōu)美,龍眼樹仿佛充滿慈愛地守護、陪伴這一家人,自然的節(jié)律與人的生命時間有一種呼應,人與土地相近相親,人在土地上自由地勞動,也自由地享受。但土地一旦被商品化進入市場交換,“人與土地的溫情脈脈的關系”便不復存在,“所有者和他的財產(chǎn)之間的一切人格關系必然終止,而這個財產(chǎn)必然成為純實物的、物質(zhì)的財富;與土地的榮譽聯(lián)姻必然被基于利害關系的聯(lián)姻代替,而土地也像人一樣必然降到買賣價值的水平”。⑩
在這兩篇小說中,林欣木離開了故鄉(xiāng),漂泊無蹤;二伯父一家也在經(jīng)濟的巨變中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操守——但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被“拋出”原有世界的人,因為社會經(jīng)濟巨變已經(jīng)使得他們的“故鄉(xiāng)”面目全非,社會的結構性轉(zhuǎn)變施加于常民生活造成了如此的價值失序和經(jīng)驗斷裂。
三、資本主義與精神危機:
“花草若離了土,就要枯黃”
在更為抽象的價值層面,在陳映真的小說中,“故鄉(xiāng)”也常常代表了一種希望,一種救贖的可能性,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例如在《永恒的大地》的結尾處,飽受凌虐的“伊”突然說:“那天,我竟遇見了打故鄉(xiāng)來的小伙子……他說,鄉(xiāng)下的故鄉(xiāng)鳥特別會叫,花開得尤其的香!”,“一個來自鳥語和花香的嬰兒……我的囝仔將在滿地的陽光里長大”。而在《夜行貨車》中,詹奕宏毅然帶著劉小玲逃離那傲慢、虛偽的“華盛頓大樓”,也決定要一起回到他的南部的故鄉(xiāng)。小說的最后,詹奕宏忽而想起那一列“黑色的、強大的、長長的夜行貨車。轟隆隆地開向南方的他的故鄉(xiāng)的貨車”。“故鄉(xiāng)”在這兩篇小說中都以最后的庇護所出現(xiàn),它給飽受傷害的人們以安慰、以希望、以拯救。在下文中,我將通過對《萬商帝君》和《云》的具體分析,闡述陳映真對“故鄉(xiāng)”寄予的價值內(nèi)涵,以及在資本主義化的現(xiàn)代世界中,故鄉(xiāng)如何對個體的生命經(jīng)歷產(chǎn)生影響,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如何反過來“吞噬”人們的故鄉(xiāng)。
《萬商帝君》可謂“華盛頓大樓系列”中前景最為黑暗的一篇,資本主義全球化如同天羅地網(wǎng),令人無處逃遁;曾經(jīng)對立的陳家奇和劉福金相視一笑,在徹底貶抑和拋棄民族主義上達成共識,全身心擁抱world shopping center的迷夢,而華盛頓大樓的底層和邊緣人林德旺則精神崩潰,徹底瘋了。
林德旺的瘋狂固然是由于被這個資本主義體系拋棄——在公司中受人嘲諷冷落;長久地被噩夢中老金和Lolita偷情的場景所壓迫;又逢莫飛穆公司承辦國際會議,人人都沐浴在前所未有的欣快中,人人都能參與其中,可是分給他林德旺的連一張紙片都沒有。對林德旺來說,華盛頓大樓不僅僅是個拼事業(yè)、出人頭地的工作場域,而且?guī)缀跏切悦难鲑嚕叭绻x開臺灣莫飛穆,他寧愿一頭從七樓栽下這宮殿一般巍峨的華盛頓大樓”。然而在另一方面,林德旺又要與生養(yǎng)他的土地一刀兩斷。比起華盛頓大樓中衣著光鮮的“上等人”,在他眼里,故鄉(xiāng)顯得“那么愚昧、混亂、骯臟、落后”,“我當然不屬于鄉(xiāng)下那個落后,不識字的地方”。
在林德旺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來自第三世界農(nóng)村的底層人民,如何與資本主義世界劈面相逢。對于林德旺們來說,后者不僅僅是一種經(jīng)濟形態(tài)、一種社會制度,也是一種重新魅化的世界宗教,閃耀著攝人的奇異光芒。它讓林德旺們充滿欲求,去把自己包裝成舉手投足的都市人,去投身于“出人頭地”的職場攀爬之路。然而正是資本主義的這種意識形態(tài)效應如同“下蠱”一般,讓林德旺們深陷巨大的夾縫,上不上,下不下;既無法被這個體系全然接納,自在游走于其中,也在價值上永遠失落了他們的故鄉(xiāng)。在資本主義與現(xiàn)代文明的“映照”之下,整個鄉(xiāng)土世界顯得愚昧、破落,好不容易從鄉(xiāng)村進入都會的林德旺們急切地想要斬斷與這一切的關聯(lián),徹底拋卻那些民間社會的生活傳統(tǒng),恨不能抹去自己身上故土遺留的一切痕跡。
現(xiàn)在,我們似乎就可以理解林德旺另一個固定的噩夢:
他忿怒地——也不知為了什么,總之,他便是那樣地、異常生氣地在故鄉(xiāng)銅鑼的、干涸的河床上奔跑。河床上的石頭堅硬、棘腳,被太陽曬得火燙。……他還是那么生氣而執(zhí)念地跑著,一心要跑出這荒蕪的、看似無邊的故鄉(xiāng)的河床。然而,整個河床卻只像輪盤一般,慢慢地轉(zhuǎn)動,使他耗盡力氣,就是怎么也無法逃脫整個惡意而燠熱的、慌亂,而又令他羞恥的河床。{11}
在小說中,林德旺的姐姐說到,“花草若離了土,就要枯黃”。既無法投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又在價值和情感上拋卻了故鄉(xiāng),最后亦沒有得到宗教的救贖,林德旺除了瘋癲,別無出路。
而《云》中的小文和她的故鄉(xiāng)則可以說是與《萬商帝君》形成對比的“正面描寫”。在到麥迪遜的工廠做工之前,小文同樣出身于臺灣南部的農(nóng)村家庭,父親是退役的空軍,母親則是本省的農(nóng)婦,一家人勤勉地勞作,有一個相依、相愛的家。所以小文進入跨國公司的工廠后,依然惦念著故鄉(xiāng)和親人,她的日記、散文中充滿深深思戀的文字。小說中寫到,一個加完班的周末,小文就趕著坐夜班車回鄉(xiāng);第二天的早上她與大嫂沿著圳溝散步,家中的小狗興高采烈、前奔后跑,“五月初的天,明亮、透明,照著兩邊的蔗田里隨著風舞動著的蔗葉”,“每次回到家,看著這些,就不想要回到工廠去。或者,至少也希望能多幾天假,待在家里”。
小文也從鄉(xiāng)村進入了城市,卻始終牽掛著她的故鄉(xiāng)、她的家。心有所系便不容易在流俗中茫然浮蕩,因此她對自己在城市中可能沾染的消費欲和虛榮心始終誡慎警懼,在日記中常常提醒自己;她也沒有像好朋友秀麗那樣全身心地墜入與陌生男子的戀愛之中。另一方面,互相扶持、互相關心的家庭也給予了小文愛的經(jīng)驗和愛人的能力,她也才能在工廠中被何大姐她們感染,義無反顧地投入工會這一“大家庭”的建設。“堅決相信人應該互相友好、誠實地生活”,這不僅是何大姐們給予她的信念,同樣是她在故鄉(xiāng)家庭的生活經(jīng)驗給予她的初心。
在這篇小說中,陳映真還難得花了不少筆墨,對“故鄉(xiāng)”進行了一番頗為審美化的描寫。
我還想到屋后的一片竹林,在秋風的吹拂中,發(fā)出好像幾百件衣裙相摩擦的聲音。在夏天的清晨,嘰嘰喳喳的饒舌聲把我叫醒的上百只麻雀,就是棲息在這叢竹林里。我的房間,開著一個窗口,流進來幾乎帶著綠色的晨光,也是太陽透過這叢竹子,照進來的。照著我的寬大的、因歲月而發(fā)亮的木榻。{12}
小時候,在竹叢下的古井邊乘涼,每次看見流星總要對一邊燃燒著、一邊流逝著的星星,不知為了什么地合十,惹得母親愛笑。……多么叫人懷念的故鄉(xiāng)。多么叫人懷念的童年的那一顆流星……{13}
這一段描寫仿佛古舊的夢境,充滿傳統(tǒng)的詩趣,也可以說是一種非常文人式的對鄉(xiāng)村生活的再現(xiàn)。正如趙剛指出,這里的“古井”和“竹叢”具有高度的象征意義,它們表征了一種在自然中的人文、一種歷史中的生命足跡、一種無意識的傳承,以及一種來日的另類文化的深層源頭{14}。小文的故鄉(xiāng)仿佛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田園烏托邦,但它在時間上不是孤立的,而是坐落于一個充滿中國古典意味的傳統(tǒng)脈絡中,自然與人的關系不僅親近,而且提供一種心靈的滋養(yǎng),讓人打開眼,打開心,于是,這篇小說中也只有小文能望著天上的云朵,發(fā)出這樣的感慨:
我方才一直在看著那些白云。看著他們那么快樂、那么和平、那么友愛地,一起在天上慢慢地漂流、互相輕輕地挽著、抱著。想著如果他們俯視著地上的我們,多么難為情。{15}
四、結論:從“故鄉(xiāng)”重建一種價值倫理
23歲的陳映真在小說《故鄉(xiāng)》中化身流浪的青年,流著淚踏上北上的列車——“我不回家。我沒有家呀”。后來的陳映真,面對臺灣社會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卻深感失根的焦慮,在個人的情感和價值追求上也經(jīng)歷了一個逐漸“歸鄉(xiāng)”的過程。但這種歸鄉(xiāng)不是文人作家在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下的文化鄉(xiāng)愁,追憶一種逝去的情致意趣。我們必須回到陳映真的左翼立場,尤其是身為第三世界的左翼,面對如無邊巨網(wǎng)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面對兩岸分斷體制以及分離主義的崛起,陳映真始終堅持著他的批判與介入。
陳映真的“歸鄉(xiāng)”一方面是試圖挽留或召喚某種可能已經(jīng)失落的生活經(jīng)驗和文化性格:人與人之間親近友愛而不是冷漠疏離,人對自然敞開心靈、懷抱虔敬,而不是為了利益肆意污染,人對故土、對過去有一份溫情與傳承,而不是在異化的資本主義叢林中失魂落魄,心無所依。
另一方面,陳映真的“歸鄉(xiāng)”也表明了他愈加清晰而強烈的歷史的、文化的民族主義立場。陳映真固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但他并不是只是“向前”看,如同中國大陸過去的很多左翼作家那樣,以一種背對歷史、建設未來的“進步”態(tài)度,致力于鄉(xiāng)土的改造與重建,促成從舊世界到新世界的革命的發(fā)生。相反,陳映真帶著一種自覺,反身回顧中國民族文化的傳統(tǒng)資源,這既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抵抗,同時也是孜孜以求一種讓人更真實、更合理地活著的倫理價值。在電影《甘地傳》的觀后感《自尊心與人道愛》中,陳映真寫到,“從自己民族的傳統(tǒng)和文化中尋找像甘地那樣單純而又萬古常新、簡單而又深刻的信念,重新為自己建造對人、對生活和對世界的信念”。{16}對陳映真而言,第三世界不應以西方的左翼“解放”理念為唯一參照點,而是應該分析和把握自己的歷史脈絡和生活邏輯,從中找到繼續(xù)轉(zhuǎn)化的可能性;而對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和思想資源的領悟和重新采用,也是在第三世界中形成有效的在地實踐的重要前提。
① 陳映真,《故鄉(xiāng)》,見《陳映真小說集》(1),臺北:洪范書店2001年版,第56頁;第57頁。
② 陳映真,《試論陳映真》,見《陳映真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3-11頁。
③{14} 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2011年版。
④ 陳映真,《后街》,見《陳映真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
⑤ 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11年第84期。
⑥ 陳映真,《忠孝公園》,見《陳映真小說集》(6),臺北:洪范書店2001年版,第161頁。
⑦ 葉守禮,《小農(nóng)經(jīng)濟現(xiàn)代變遷:東勢果農(nóng)的商品化之路》,臺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15年碩士論文。
⑧ 陳玉璽,《臺灣的依附型發(fā)展》,臺北:人間出版社1995年版。
⑨ 楊渡,《回望臺灣股瘋》,財新網(wǎng)文化專欄,2015年7月13日,http://m.culture.caixin.com/m/2015-07-13/100828338.html。
⑩ 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頁。
{11} 陳映真,《萬商帝君》,見《陳映真小說集》(4),臺北:洪范書店2001年版,第194頁。
{12}{13}{15} 陳映真,《云》,見《陳映真小說集》(4),臺北:洪范書店2001年版,第18頁;第65頁;第117頁。
{16} 陳映真,《自尊心與人道愛》,見《陳映真作品集》(9),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版。
(責任編輯:黃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