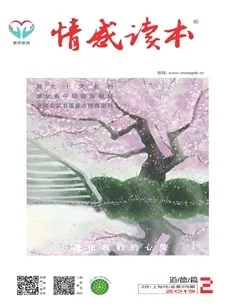抱抱我
陳鳳華
走出首都醫院,冷風習習中似乎有暖風吹來。我抹去淚水,羞澀地對先生說:“抱抱我!”
深秋看銀杏樹時,不經意扭身,頸部有痛感,本能摸摸,卻有雞蛋大的包塊。以為扭傷,以為炎癥,并未在意。然而,疼痛在蔓延,只好去看醫生。醫生漫不經心地說:“血管瘤,切去即可。”
瘤,聽起來如魔鬼。又換醫院查看,檢查結果腫物。瞬間,眼前模糊,不知所措。
住院,手術,經過一場血與肉的PK,割下一粒藥丸大小的瘤子。瘤子好與壞,都需要病理檢查。可是,病理之后,醫生卻電話通知先生面談,并告知要再做免疫組化檢查。先生含糊其辭解釋這個電話,但我明白了隱衷。這時,想到老師留給學生的家庭作業,如果沒有錯誤,老師是不會找家長的。有錯誤,或抄襲,老師才需家長到校。這時,我便對切下去的腫物,多出了恐慌和畏懼。
次日,我拒絕先生參與此事,盡管虛弱,還是自己去了病理檢查科,捏著一把鈔票,并不心甘情愿地交付醫院。檢查結果,纖維瘤。怯怯問醫生如何治療,醫生面無表情機械一般地說:“中性瘤,復發率偏高,沒有好的治療方法,再長再切。”
“切!”經醫生的唇齒碰撞后,似乎切蘿卜一樣簡單。而我聽后,通體哆嗦,不自覺盜出冷汗,內心卻也結了寒冰。
刀口的痛在蔓延,病理又如一顆炸彈,心情被各種壞消息折磨著,我有些坐立不安。并非我膽小,而是親眼經歷好友的生命被病魔折磨得茍延殘喘。蜜蜜們似乎從第二次病理中明白了什么?紛紛送來鮮花,買來禮物和食品。似乎我不是從手術臺敗下來的病人,好像從前線凱旋而歸的將軍。每一個人都在勸我要有好心態,病要慢慢養……一份份雞湯“端”給我。以往我也以“智者”之身給他人灌雞湯,而自己的雞湯,不但無法稀釋煩惱,反而如一劑毒藥,侵襲著折磨我,又如一把利劍,剜我心頭的肉。
無奈時,喜歡借助網絡尋求解決內心糾結的良方。
如果我是無知的村婦,不懂網絡和書本,自然不會慌張,我會活得很自在,很逍遙。可是,我有文化,還愛求根溯源。通過網絡看到幾個病例,令我毛骨悚然。默默祈禱自己是另類,與他們不一樣。自我在安慰,可內心的惶恐一點也沒有削減。
女人是水做的,果不其然,一邊傷感落淚,一邊懷想曾經,感覺天要塌下來,生命也到了臨界點。想著年邁多病的父母,想著尚未成家的孩子,想著下崗打工的先生……總之,內心滿滿的不舍。恐懼病魔的原因是因為還有一份責任在。以淚洗面的日子,讓我對生命充滿著期許和向往。覺得當下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奢侈,都是恩賜。
先生也因這份報告單焦頭爛額。
怎么辦?怎么辦?怎么辦?
都說有病亂投醫,同事建議去北京看看,況且北京有神奇,也有神話。
刀口漸漸愈合,而內心的恐慌驅之不散。以往的笑容不知逃遁何處。強裝笑顏,卻讓蜜蜜們心酸和心疼。學姐為我買了紅圍巾,她想用紅色平復我內心的悲傷。而我也極力用亮色衣裙為自己增加喜色。我不想以病態示人,更不想把內心的絕望昭示天下。
北京就醫充滿著向往和神圣。醫生對病理結果輕描淡寫,卻如創可貼,止血止痛,還化解了憂傷,內心的恐慌瞬間瓦解。同時,血液腫瘤化驗單上也沒有腫瘤細胞的成分。頓時,如重生,我想雀躍,我想狂奔,我想高喊,我的生命線并沒有戛然而止。這時,撲面而來的淚水是喜悅的,是溫暖的,內心的壓抑,釋放了,稀釋了。
醫生確認“腫物”的那一刻,時隔幾十個日夜,茶飯不思,寢食難安。就這樣,分分秒秒的時光,被無端的頹廢剝奪;大把大把的鈔票,為了治療而消耗。不經歷了苦難,就無法得到救贖。經過這一場生病的插曲,更加珍惜生命的重要,更加懂得人生的價值,同時清晰該舍棄什么,該珍惜什么。記得一篇文章說過:“人不生一次病,往往意識不到自己的身體有多脆弱。生一場病就活得通絡了。”道理雖如此,但還是不生病為妙,能不生病就活通透該是智者。而我的通透卻是在生病的虛驚之后。
走出首都醫院,冷風習習中似乎有暖風吹來。我抹去淚水,羞澀地對先生說:“抱抱我!”
疾病面前考驗的不僅是生命,更是感情。生病時日,先生比我還要煎熬,他既要承受我疾病的現實,還要精心護理我。其實,病者是一種福氣,大難過后的從容和通透都是賞賜。通過這次生病,讓自己活得更加明白,讓自己懂得愛的珍貴。
之后,我拉著先生的手說:“我們去前門吃烤鴨吧。”
孫慶紅摘自《吉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