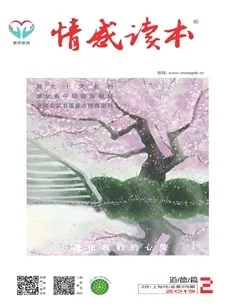給世界留下溫柔的關門聲
董改正
愿他在山下的世界里平安順遂,愿他健康,愿他的臉上綻開笑容,愿他所過之處的鄰室,都會為他輕輕合上屋門,給世界留下溫柔的“吧嗒”聲。
二十年前,我租住在露采的一座小山上。那時候剛畢業不久,輾轉分配在一個郊區的化工企業中,從事著一種叫“保全工”的工種,負責原料供給和機器維修,苦累不說,三班制嚴重摧毀了我的睡眠。即使睡著了,也像棲息在草尖上的蜻蜓,一點風吹草動,也會猝然醒來,夢魂逡巡盤旋,再也不肯著陸。為了免入抑郁的恐慌,我就亮燈讀書,靠疲倦帶來睡眠。
房東姓徐,矮小精干,在銅礦上班。他的妻子姓周,大個子,是江北嫁過來的,沒有職業,這片違建的房子便是她的田地。房子依山而建,大約有二十間,我住在最上面的兩間中的一間里。房子不大,約十平方米,高約兩米,無廚無衛,水也是要靠水桶拎的。菜也須在山下做好,然后端著上山來。
小山并不高,約一百米吧,上山的水泥階梯是房東做的。他話不多,笑瞇瞇的,卻會做很多事。我房前便是山頂,也被他辟出一大塊菜地,至今我依然記得仲夏的豇豆架上,滿架豆藤如墻,承著滿架花開,便如一墻斂翅的蝴蝶,風便來吹它們,月光便來照它們。除了種菜,他還給我種下了四季蟲鳴,尤其是月夜,尤其是盛夏,嘈嘈切切,蟲鳴如雨。若真是下雨了,無論是憂傷的春雨,還是酣暢的夏雨,無論是陰郁的秋雨,還是蕭索的冬雨,都會以清寂的雨聲提醒自我的所在,讓小屋與整個世界剝離出來,讓我清晰地置身己身之外,看到一燈如豆,看到蜷臥的自己。
我也會在月明之夜,站在午夜的小山上,俯瞰城市燈火和鱗次櫛比的俗世生活。我來自江北鄉村一個貧寒農家,沒有遠大理想,也沒有人生規劃,我不知“幸福”的具象,我甚至從未進入過一個真正意義上城市居民的家中,這個城市也沒有一個與我痛癢相關的人。我雖不知道幸福的模樣,卻知道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只是因為與生俱來的保守和怯懦,不敢放棄現在的工作,去深圳、上海或北京闖蕩。
仲秋的一個夜晚,我上夜班回來,洗漱完畢,臥床夜讀,忽然聽見隔壁傳來了開門聲。我租住此間已經兩年了,一直是一個人獨占著一座小山。因為不便和空寂,鄰室一直空著,租不出去,這是我第一次聽見人聲。我下意識地關掉了燈,便清晰地“看”到了他,站在菜地的邊緣,看著山下的萬家燈火。我陪他一起看著。夜色如海。直到聽到他“吱呀”掩門,“吧嗒”拉合后,心神才在月色蟲鳴里,蝴蝶一般回到身體,斂翅待眠。世界黑起來,夜色溫柔。
我幾乎每一個晚上,都是在他的關門聲后睡去,睡得很香。
“小董,你和他說過話嗎?”女房東小周問我。
“沒,怎么了?”
“我后悔了,不想租給他,又怕他報復。我怕他是個壞人。他不跟任何人說話,天天晚上站在菜園里,半天不動。”
“不與人說話就是壞人?我也經常站在那里的。”
“你不一樣,你是正常人。他長臉,臉上鐵澆筑的一樣,鷹鉤鼻子,眼睛就像電焊槍一樣。而且,他從不做飯。我怎么看他都像一個逃犯。”
“他不是。”
“你怎么知道?”
“他關門是輕輕拉到門鎖咬合處時,再輕輕一拽,聲音很小,就像樹葉落下來一樣。”
小周狐疑地看著我,似乎我跟他差不多了。她離開后,我聽見鄰室的門開了,向我的窗走動幾步,又回身,門又被關上了。他居然在家。
轉眼就是冬天了。那夜居然下起了冬日少見的瓢潑大雨,我回來時,已是夜里一點半了,鄰室的燈依然亮著,在滿世界的雨聲和雨影里,尤顯力不從心,似乎隨時都會被風刮走,被雨澆滅。我進門,輕輕掩上屋門,再輕輕拽合,開燈,洗漱。鄰室的門開了,又關了。我們的兩盞燈,就像一雙眼睛,凝視著風雨之夜。
槐花盛開的這個夏天,似乎比以前明朗一些。一日回來,下意識看見鄰室屋門大開,不由過去看看,卻見是小周在打掃。她抬頭見是我,說道:“搬走了,我也省心了。即使像你說的那樣,我也不想租給他。”我笑笑回屋。
夜就越發空寂起來,在夜的深處,再也沒有一扇關門聲,為我擋住洶涌的夜寒,合上夜的眼皮,帶來深深的睡眠。我只好繼續以疲倦來消解疲倦。
不幾日,我下班走上臺階時,小周在身后叫我,說有封信給我。
我便回身等她。她半天才從正屋里出來,手里拿著一個信封,懊喪地說:“唉!這孩子真淘氣,把信折飛機玩了,找不到了,只剩下信封了。”
我接過信封,收信人那一行中,鐵畫銀鉤著:“山頂鄰室收”。
我沒有怪她的兒子。雖然沒看見內容,但我想我是大致知道的。愿他在山下的世界里平安順遂,愿他健康,愿他的臉上綻開笑容,愿他所過之處的鄰室,都會為他輕輕合上屋門,給世界留下溫柔的“吧嗒”聲。
金磊摘自《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