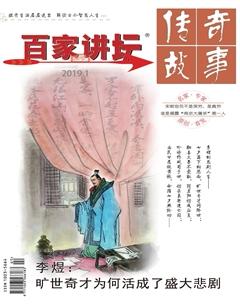明代畫家:唯以丹青迥世塵
荷衣蕙帶
被稱為“明四家”之一的繪畫大家仇英是個異數,相對于沈周、文徵明、唐寅,他既不擅長詩、又不能文,也不工于書法,唯以丹青妙筆拔群出萃。
仇英出生于江蘇太倉(今屬江蘇蘇州)一個貧民家庭,幼年時,他和其他孩子唯一的不同之處就是酷愛繪畫。身邊沒有老師的指點,他就對著實物自行描摹,因為天賦出眾,這些無師自通的畫作看上去倒也有模有樣。
等到他十一二歲的時候,家人便開始為他將來的生計做謀劃,知道他喜愛繪畫,就讓他跟著一位漆工師傅做學徒。學習漆工就要學習識色、調色和圖案設計,這些對他而言,正合心意。他學得很快,不久就成了當地小有名氣的漆工,請他做彩繪棟宇的人很多,通過幾年的省吃儉用,他也有了一些積蓄。
只是在內心深處,仇英更喜歡的依然是繪畫,對于在宣紙上走筆暈彩有著一種近乎虔誠的執著。為了圓自己做畫家的夢想,十幾歲的他就離開太倉來到蘇州,希望在這里為自己尋一位老師。
初到蘇州,仇英依然是以漆工為業,憑著精湛的技藝,他很快就在一家漆作坊找到了工作。盡管做漆工非常辛苦,可是他依然堅持著自己的夢想。每有閑暇,他必會跑到書畫裝裱店和字畫古董店觀看店中的字畫,順便聽聽別人對這些書畫名家作品的點評,再仔細地觀看這些畫,暗暗記在腦中,晚上回去憑記憶畫下來。
去的次數多了,那些店里的老板也就留意起這個衣著寒酸、只看不買的小伙子,其中不免有些人會對他白眼相加,也有人對他這種勤學精神很是贊賞。也就是在這些書畫店中,仇英偶遇了文徵明,經過簡單的交談,文徵明對他關于書畫中用色的見解極為欣賞,與他結為忘年交。
有了文徵明的賞識和提攜,仇英很快結識了吳門畫派中幾位重要的畫家,正式開始以繪畫為業。等到文徵明進京時,還特意將仇英引薦給了大畫家周臣,請周臣多加關照。看到仇英為人踏實勤奮,周臣正式將他收為弟子。
周臣的畫風承襲了南宋院體的風格,構圖洗練緊湊、墨色清潤,這段學習經歷為仇英的繪畫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周臣還有一位特別出名的弟子就是唐寅,作為早已名聞天下的才子兼畫家,唐寅對這位匠人出身的小師弟照顧有加,時常指點一二。等文徵明再見到仇英時,仇英的畫已經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有了文徵明、周臣、唐寅等人的提點和幫助,年紀輕輕的仇英很快就聲名遠播,成了青年畫家里的翹楚。
文徵明畫《湘夫人圖))時曾邀仇英為之設色,仇英反復畫了兩次都沒有達到文徵明想要的效果,最后還是文徵明親自設色才達到理想的效果。
通過這件事情,仇英意識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后發奮在設色上深研微探,使自己的作品設色鮮妍又不流俗,達到了后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因為是工匠出身,對于詩書一途毫無功力,仇英就只能在繪畫上付出全部的心力,尤其是在臨摹上更是下足了功夫,他臨摹的作品完全可以以假亂真。有實力又有許多名家提攜,他的臨摹作品深受當時的收藏名家欣賞,請他臨摹前人佳作的應接不暇,不過對他而言,這也是絕佳的學習機會,可以開闊眼界又有大把銀子可賺。
不久,昆山一位姓周的著名收藏家就成了仇英的第一位贊助人,將他接入府中專職創作。在周府的六年時間里,仇英進步神速,與這位收藏家也相處得極為融洽。之后,另一位著名收藏家、鑒賞家又將他聘入府內,專司臨摹。在與這位收藏家相處的幾年里,仇英有機會看到了更多的前人畫作,他一面細心臨摹一面認真學習,畫藝得到進一步提高。
臨摹的作品多了,仇英也有了更多的想法和創作意識,雖然后來他的作品中也常常會有臨摹的作品,卻不是一味地抄襲前人的作品,而是在保留題材的基礎上,加上個人的藝術創作,這其實就和文人畫的取其意、遺其形的理論不謀而合。
《清明上河圖》是宋人張擇端的作品,所繪的是汴京(今河南開封)的生活實景,而仇英筆下的《清明上河圖》則是明代江南地區的生活情景,雖然構圖布局參照了張擇端的形式,但是其中的城墻、運河、茶肆酒樓、洗染坊等無不透露著蘇州地區的明顯標志。尤其他還采用了自己最擅長的青綠山水的技法染色,使得畫面充滿了“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潔而明凈”的春天氣息。
如果說張擇端將宋人的生活場景截取片段留給了后世參詳,那么仇英無疑是將明人的風俗和生活鮮活地記錄了下來。文徵明看到這幅畫后不僅撰寫《清明上河圖記》,還贊這幅畫:“后之覽者,當即以真本視之可也。”雖然他的摹本不如張擇端原本的藝術價值和研究價值,卻也有著自身獨特的價值,這就是再創作后賦予作品的新生命。
一次,某收藏家得到了一卷趙孟頫的書《以般若經換茶詩》,可惜保存得不好,已經破爛不堪,經文也不知所蹤。于是,他請文徵明補寫了一篇《摩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又請仇英畫了趙孟頫以經換茶的情景,文徵明的長子寫了跋文將此事記錄下來,次子也在此卷上留下題跋。
文徵明的長子和次子在當時也都是非常有影響力的文人,可以說文氏一族都在力挺仇英。有了這么多的助力,仇英的名氣越來越大,甚至遠遠超過了老師周臣。當時資助仇英的還有昆山和蘇州的兩位大富豪,因此他的畫在收藏界非常搶手,許多請不到他的人就學他的風格,或者假冒他的作品,以至于后世他的畫作假款非常多,甚至有人用周臣的畫挖去簽名換上他的名字。
可就是畫作如此搶手的仇英,卻有著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辛酸,他是明四家中最末的一位,也是名氣最小的一位,這倒不是因為他的年紀最小,而是因為他的出身。
自蘇軾提出了“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的主張后,許多文人開始加盟畫壇,文人畫在之后的數百年一直是畫壇主流。明四家其他三人都是詩、書、畫全能的文人畫家,仇英畫畫卻只敢在角落里落下一個小小款識,不用別人開口,他自己就知道矮人一頭,即便是參加文人的雅集,不會吟詩的他也很難真正融入其中。
明代著名書畫家董其昌提出畫壇的南北宗論(南宗是文人畫,北宗是行家畫)時,仇英就是很令他頭痛的一個人物。仇英的畫恰好介于畫師與文人畫家之間,他得到過文徵明和唐寅的指點,設色典雅,畫中有士氣,卻又不能算真正的文人畫家。雖然最終董其昌將他貶抑地劃人了北宗,卻又在看他的畫時忍不住稱贊:“近代高手第一”“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仇英的字)”。
觀看仇英的畫作,就會發現他的畫中每一個皴擦、每一點虱都法度森然,一絲不茍。沒有了詩、書的輔助,他只能將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安放在畫中的每一筆上,他的畫有一種近似虔誠的工整,那是他對作畫的赤誠與摯愛,這樣的畫者怎能不是畫中高手,怎能不被后世銘記。
編輯/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