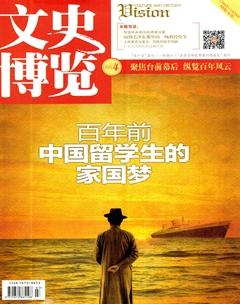蘇聯文學留給我們那代人的青春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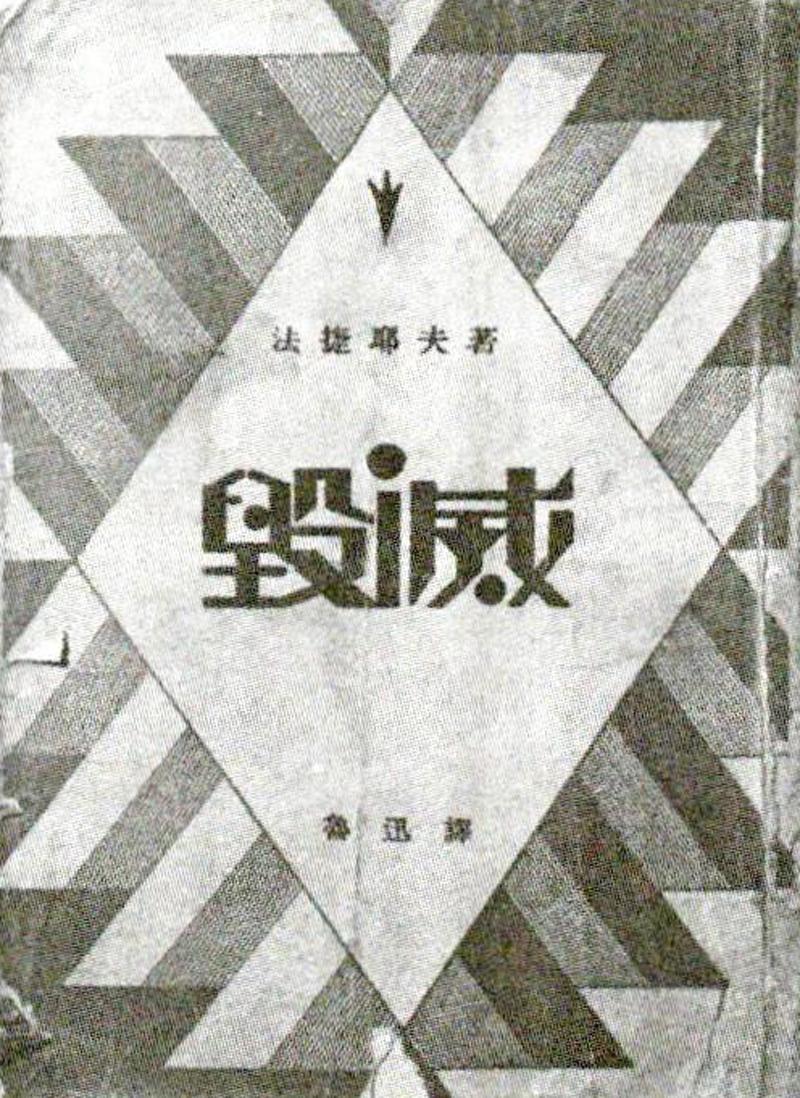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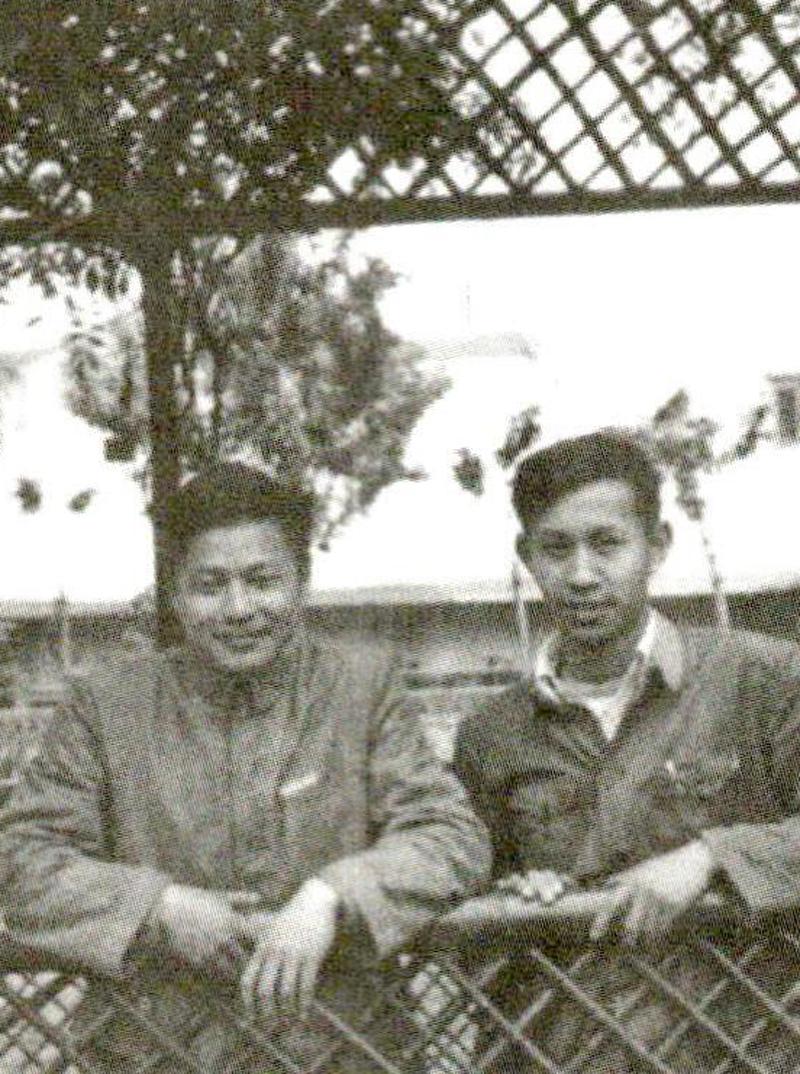

吳興唐,中聯部調研咨詢小組成員、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1960年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后,先后在中聯部一處、蘇聯東歐研究所和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館工作。曾任中聯部研究室主任、中聯部新聞發言人等職。本文所講述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蘇聯文化對青年一代人的影響,摘編自《蘇聯的烙印——那些與青春有關的故事》,標題有改動。——編者
1950年到1956年,我在上海市市東中學念書。那時剛解放不久,蘇聯又是我們的“老大哥”,舉國上下都在倡導向蘇聯學習。我們學校的氛圍向來非常開放,除讀革命書籍、唱革命歌曲外,也非常重視蘇聯、東歐文化的傳播。這6年里,我所受的革命教育和蘇聯文化相互結合,深深地影響了我后來的人生道路。
蘇聯文藝作品讓我初步認識了社會主義
我從小就很喜歡讀書,中學那幾年把學校圖書館里所有的書都讀了一遍,尤其是蘇聯的文學作品,更是特別的喜愛。我最早接觸的是法捷耶夫的《毀滅》和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毀滅》是魯迅翻譯的,講蘇聯國內戰爭時期遠東地區一支游擊隊艱苦奮斗的故事,我讀后感到非常震撼。法捷耶夫還有本很有名的小說叫《青年近衛軍》,講地下青年組織怎么反抗德國法西斯占領軍的統治。其他作家的作品譬如《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鷹之歌》等,我都非常喜歡。值得一提的是,高爾基的作品中,我對《底層》特別感興趣。因為我家是工人階級,我自小就生活在上海的貧民區,住的是一棟石庫門房子。原本那是供一家人住的,可當時竟住了十幾家,如同電影《七十二家房客》一樣。
解放前夕,警察每夜都來“查戶口”,因住得雜亂,我家經常被漏掉。弄堂對面有條河,河對岸就是申新紗廠。我家樓上住著一位20來歲從外地逃婚出來的瘦弱女孩子,住在曬臺上(原來是曬衣服的地方,后改裝成住房),每天天未亮就拿個飯盒去紗廠上工,晚上出廠還要被搜身。這里還住著店員、小學教員、小職員,以及跑單幫的、走卒小販、國民黨逃兵等。我日常接觸的多數都是這樣的小市民,看這部作品時便產生了極大的共鳴。
蘇聯文藝作品為我帶來了對社會主義、對信仰的初步認識。當時剛解放不久,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很多人都不清楚。加上當時上海經濟比較混亂,國民黨的飛機還總來轟炸,上海當時最大的發電廠——楊樹浦發電廠就曾被炸掉一半。除了炸彈,飛機還撒傳單,說蔣介石八月十五要到上海吃月餅,等等。因此,一部分人對于上海的未來是很迷茫的。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我們學校專門開展了主題為“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活動,請來從蘇聯回來的上海市青年代表團到學校作報告,講蘇聯人民怎么生活。為配合這一活動,學校還組織大家看《幸福的生活》《拖拉機手》等蘇聯電影。隨著看電影的學生越來越多,校長決定建一個新禮堂,但條件非常簡陋,屋頂是用草蓋的,坐的都是一條條長凳。即便如此,同學們看電影的熱情仍然很高漲。我當時任學校團委副書記、宣傳委員,看完電影我就寫觀后感,當時幾乎每期黑板報上都會登一篇我的文章。另外,我們每個班都有團支部宣傳委員,我召集他們開會,要求每個禮拜都有一次讀報活動。但是有時候讀報很枯燥,我就讓他們讀蘇聯電影影評,盡管篇幅很短,但很受歡迎。而我自己參加黨課學習,看到了蘇聯、社會主義的美好未來,深受鼓舞,從而更加堅定了信念,并在17歲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普通勞動者的化裝舞會
蘇聯文藝作品對我的人生觀、人生道路的選擇也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那段著名的話:“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一個人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這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它幫我樹立了一個正確的人生觀:不要碌碌無為過一生。
蘇聯文學中很多講的都是普通人,比如女拖拉機手瑪麗來娜、鄉村女老師瓦爾娃拉等,他們為社會主義奮斗,都是到最艱苦的地方、到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去搞建設。受他們的影響,我覺得做一個拖拉機手就很好了,當一名老師就很光榮了。后來我跟校長提出來:我們學校要培養什么人呢?是普通勞動者。校長很贊成。因為學校在榆林區(后并入楊浦區),我的同學們好多都是工人子弟,家境比較貧寒,校長就說:“我們學校不是培養學生們去做經理、做老板或者當官,而是做一名普通的勞動者。”后來把“堂堂正正做人,實實在在做事”作為校訓。
我在學校里搞了兩次化裝舞會,參加的同學不是像西方那樣穿著奇裝異服來“群魔亂舞”,而是志愿從事什么職業,就化裝成什么。同學們扮成工程師、醫生、教師、記者、造船工作者、煉鋼工作者等,最多的則是扮成解放軍士兵和軍官。我因為一直都非常喜歡文科,想考文學類專業、做一個記者,所以像教書先生那樣穿了一件長褂子,又用樹枝做了一支筆拿在手里。舞會非常受同學們的歡迎,沒想到后來竟沿襲下去,成了我們學校一個很好的傳統。
我還在學校搞了個校辦工廠,校長要我來當廠長。這在當時很少見。我們把工人老師傅從學校旁邊的工廠請來,教我們最簡單的勞動,譬如用銼刀等做一些簡單的活,目的是培養一種工匠精神。當然,這也跟上海的傳統有關系。我們這些同學家庭比較貧寒,當時生活也比較艱苦,很多人希望初中畢業就去工廠里工作,這也算是滿足了大家的心愿。我們還曾組織學生去滬東造船廠參觀學習、座談,我的不少同學后來都成了優秀的船舶工程師。
而我本想考北京大學文學系或者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但是當時有保送上大學的規定,學校選擇優秀學生上指定的大學。我是“三好學生”(“三好”即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又是團干部,因而被保送到外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西校區)。我看了那么多的蘇聯小說和電影,覺得俄語很好聽,中學里也學過一點,所以很想學俄語。但當時俄語學院跟外語學院是分開的,中間隔了一條馬路,東邊的是俄語學院,西邊的是外語學院。我去的是后者。我對老師說:“俄語不能學,我就學法語吧,法國文學也很好。”老師告訴我:“學德語的人太少了,你是黨員,根據組織需要,你就學德語吧。”當時大家因為希特勒的緣故,普遍對德國印象不好,為此老師還特意勸我:“不要以為你學的是希特勒的語言,它可是馬克思的語言!”我被說服了,于是學了德語。
跟“保爾”學勞動
可能我們這一代很多人都曾像我一樣,從蘇聯小說、電影中汲取能量,以此來克服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困難。有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我最早接觸真正的艱苦勞動是修建十三陵水庫。那時我剛上大學,天熱得不得了,還要拉沙子,女同學在后面推,男同學在前面拉,一天勞動很緊張,晚上大家都疲勞不堪。當時一共要干兩個禮拜,可沒干幾天很多人就受不了了,特別是城市里長大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甚至還有逃跑的。
這時,我建議大隊部給大家放電影《保爾·柯察金》。其中有一段劇情是講保爾去修鐵路,條件特別艱苦,任務很繁重,饑餓和寒冷時刻威脅著他和其他同志的生命。經過長時間的勞動,他虛弱極了,一天早上實在爬不起來,為了完成黨交付的任務,他連連對自己說:“起來!不是休息過來了嗎,起來呀!你的意志哪去了?”最后,保爾憑著頑強的意志,掙扎著起來繼續參加修筑鐵路的工作。同學們看到這里非常感動,深受鼓舞,接下來的勞動也變得有干勁了。
當然,蘇聯文藝作品不光是講革命、講奮斗,還具有很強的藝術性和美感,能夠很好地陶冶我們的情操。上海剛解放時,我們在學校唱《咱們工人有力量》《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燈塔》,但《夜上海》等“靡靡之音”也仍然很流行,好多同學都還在聽和唱。
其實,上海并不是像《上海灘》拍的那樣,要么是黑幫,要么是舞女。上海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地方,也是工人運動風起云涌的地方,上海是屬于勞動者、屬于工人階級的。所以在學校每天下午搞文化活動的時候,我教同學們唱《紅莓花兒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蘇聯歌曲,因其旋律十分優美,同學們都很喜歡,大家也變得更有年輕人的朝氣和情懷。
跟人打交道有“人情昧”
20世紀60年代中蘇論戰開始后,由于工作需要,中聯部提前從學校把我調到部里工作。批判蘇聯修正主義是件很嚴肅的事,我認真做好這項工作,但同時對蘇聯文化仍有一種特殊感情。例如,中聯部曾在釣魚臺國賓館放過內部電影《第四十一》,講的是蘇聯國內戰爭時期。一個蘇聯紅軍女戰士擊斃了40個白匪,但卻跟一個白匪男軍官在一個小島上戀愛了。接下來有一艘白匪的船來救他們,男軍官迎向船去,女戰士只好開槍殺了他。當時這部電影被批判為“修正主義”。無獨有偶,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里女兵沐浴的鏡頭也遭到了批判。然而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很富有藝術性、很有人情味的。
人情味還曾給我帶來一些“麻煩”。學校組織小分隊去進行禁毒活動,我是隊長,同吸毒人員談話時我老是笑著的,結果就被批評了:“你跟這些人笑什么?”我說:“他們也不是壞人,應該尊重他們,這樣才能贏得他們的尊重,才有可能讓他們聽我們的勸告,戒掉毒品。”還有,我上大學一年級時,趕上了“大鳴大放”。我是班里的黨支部書記,有人要我貼黨委的“大字報”,我想:“剛上學一年貼什么大字報呀,黨委的同志都挺辛苦的。”有人講“電燈不好,殘害青年”,我很不解:“電燈不好,怎么殘害青年了?跟黨委又有什么關系?”我不寫,就被批評。
盡管如此,我仍然堅守著這份人情味。后來我做政黨外交和民間外交工作,尤其要做人的工作,依舊保持著這樣的行事風格。我在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館待了差不多5年,上到聯邦德國總理、議會議員、黨派領導人,下到普通學生,都成了我的朋友。
我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中國國際交流協會任總干事,也有一些日本朋友經常跟我們討論問題,有時爭論很激烈。我除了堅定表明原則以外,還經常講我童年的故事。我說:“我小時候在東海漁村差一點就被日本飛機炸死了,我家里好幾個親屬就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我還對他們說,我老家寧波有天童寺和玉皇寺,唐朝時接待過許多日本僧人來學習。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罪行累累,罄竹難書,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他們聽后很受震撼。我們經常帶日本青少年到抗日戰爭紀念館去參觀,他們看了都流下了眼淚。他們說,在日本不知道這段歷史,看了紀念館之后才知道,必須要讓日本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了解歷史的真實模樣。
親熱的蘇聯人民
中蘇論戰開始時,中蘇的民間組織在國際會議上互相攻擊。時任中聯部部長王稼祥曾說:“不要失言失算,不能授人以柄。你講的話過分了,人家反過來也會還擊給你。”對此我是很贊成的。當時傳達毛主席內部講話說赫魯曉夫是“半修正主義”,那首著名的詩《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有一句是“僧是愚氓猶可訓”,就是講當時的“蘇修”還可以挽救。后來赫魯曉夫多次攻擊中國和中國領導人,兩國關系慢慢也惡化了。
盡管我對蘇聯文藝作品的感情確實起源于中蘇蜜月期,然而這份感情卻并沒有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而產生質的變化,原因是我認為蘇聯人民對我們還是好的。后來胡耀邦在會見外賓前對中聯部領導(因我是新聞發言人也在場)說,中蘇兩國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
我在駐聯邦德國大使館工作的時候發現,德國人對中國人很尊敬、很有禮貌,但是感覺不親近;蘇聯人則特別熱情,對中國人非常親熱。一次恰逢德國葡萄酒節,所有駐德國使館都有代表被請去參加這次活動,我則代表中國使館去參加。德國外交部的禮賓官把我介紹給蘇聯的文化處人員,說:“你們自己用德語談吧。”德國外交部的人告訴我:在駐德使館中,德語說得最好的是中國人和蘇聯人;美國人和一些亞洲國家的人只用英語交流;日本人講德語,別人根本聽不懂。
剛巧那個蘇聯人了解一點中國文學,所以我和他用德語談中蘇兩國文學作品,聊得很熱鬧。后來一位美國外交官也走過來想一起聊,無奈德語不太好,我還幫他翻譯。過了一會兒,德國禮賓官來開玩笑說:“哎喲,你們三個大國在一起聊吶,那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很有意思。
后來我去過蘇聯幾次。一次到一個中學去,看到蘇聯孩子們在學中文。一個女孩子的媽媽見到我們,特別高興地說:“好多年都不見中國人來了,連中文都沒辦法好好學。”我聽了便讓那個女孩常用中文給我寫信,女孩的母親非常高興。
1991年5月,我作為中聯部新聞發言人,同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吳建民一起隨江澤民同志訪問蘇聯,專門有一場活動,大概有400多位中蘇友好人士參加。江澤民同志提議說:“我們一起唱歌吧!”大伙就一起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蘇聯歌曲。曾慶紅同志又建議說:“再唱一首中國歌吧!”于是江澤民同志很高興地說:“我來指揮,唱《歌唱祖國》!”大家又一起唱這首歌,氣氛非常熱烈,令人難忘。
雖然蘇聯早已成為過往,但我想這些小說、電影和歌曲會一直留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心中,正如我們的青春,永不磨滅。
(責任編輯: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