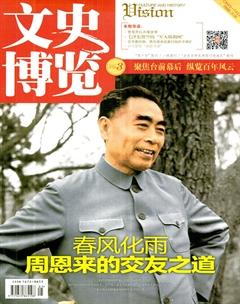“割壽材”跟建房一樣隆重
余春明
我們家鄉江西習慣稱棺材為“壽材”,這大概因為棺材讓人忌諱,人人都想長壽,稱“壽材”可討個好彩頭。然而人終歸有一死,死了總不能隨意“填溝壑”,古人所謂“馬革裹尸”終究只是極少數人舍身報國的豪邁。
對于小民而言,總想百年之后也有安身之所;而達官貴人、王侯將相,乃至至高無上的皇帝,更是要為身后營造豪華的地宮,以延續陽世的榮華富貴。所謂“梓宮”,就是皇帝的靈柩。“梓”者,梓木也。古人認為最高檔的棺材就是由梓木做成。可見壽材的重要。既然如此,由此而產生的壽材匠也就不可或缺。
記憶中,家鄉的壽材匠并不多,我們一個公社(鄉)也就一位。師傅姓楊,是青竹大隊楊浪吾村人。當年40歲不到,中等身材,結實健壯,整天笑容滿面,很和善。壽材匠不多的原因,當然是這個行業生意不興隆,那時候社會還遠沒達到老齡化的地步,就是現在,一個村一年也“老”(死)不了幾個人。況且,一般家庭老人不到六七十歲也不準備這個玩意兒,畢竟不是什么喜慶的東西。
記得父親60歲那年,突發膽囊結石,而且被醫生誤診為胰腺癌。那時候,醫學不發達,膽囊切除需開刀,也算是大手術。第二年,又由于上一年泥沙型結石清除不干凈,阻塞膽總管,重開一刀,使得父親元氣大傷,身體狀況欠佳。我和弟弟商量為他老人家準備壽材。當時父親老大的不高興,我知道父親除了考慮我們兄弟經濟拮據之外,更重要的是認為自己還不老,不愿這么早就準備后事。但他身體狀況如此,為了避免臨時“打急腳棍”(措手不及),再加上其他親屬也贊成,權當沖沖喜,我和弟弟還是決定去縣城買河杉,為父母各做一副壽材。壽材做好后,父母的身體果然很好.都活到了80多歲,這是后話。
前面講了,帝王的靈柩用梓木做,老百姓也會盡最大的能力為父母選好材料,不能讓人瞧不起。家鄉壽材用料沒有一定之規,家庭困難的會用松木,松木容易惹白蟻,不是好材料;更有人因為不是上壽亡故,家人就用一般的樓板臨時做個“盒子”安葬;就是條件較好的村民,因為當年植樹造林取得了成效,就用本地的山杉做。山杉,是指直接從山上砍下沒經河水浸泡的本地杉樹,一般木質疏松,不如河杉結實,且容易蟲蛀。河杉則是從鄱陽湖上游的修水、武寧的原始森林里砍下并扎排順著湖水流下的杉樹。因長時間經河水浸泡,拒白蟻,堅實,可經漫長歲月都不會腐爛,是家鄉壽材的首選。這也是我們兄弟到縣城買的原因,算是對父母的一點孝心吧。
經過一番挑選、付款、找車運送,整整兩天,我和弟弟才把河杉運到了家。緊接著又請細叔去楊浪吾村請楊師傅。壽材匠本來就不忙,楊師傅帶著徒弟第二天就挑著工具上了門。其實,家鄉做壽材稱“割壽材”,跟建房一樣隆重。迷信說法,房子是生人住,稱陽宅;棺材是預備亡人住,稱陰宅;得同樣慎重,不允許有半點馬虎和隨意。要選吉日吉時開工,稱之為“架馬”,須請師傅喝“架馬酒”,開工那天師傅也就用鋸象征性地鋸兩段木頭,主要是接受東家的款待。“架馬”要放鞭炮,表示喜慶。
喝了“架馬酒”,楊師傅就開始了緊張的工作。前期的斫料是辛苦活,手持斧頭,撐起五尺長的杉木段.是需要很大勁力的,非一般人力所能及。別看楊師傅個子不高,斜撐著木段斫得有板有眼,有條不紊。越是粗大的木段越難做,而越是粗大木段做的壽材越顯眼,越氣派,本錢也越大。
家鄉的壽材有十割、十二割、十四割的區別。這是根據杉木段的粗細而分的。十割的壽材四面只用十棵木段,以此類推,割數越多,杉木段的腰圍越小。十割的壽材很少見,十二割的也不多。我們為父母做的就是十二割的,這在當時村里也是數一數二的。
割壽材屬大木,雖然不像小木做家具那樣精雕細琢,但楊師傅也做得非常過細。壽材的蓋、兩壁和前后的門面部位都用特殊的圓刨刨得很光滑。每刨一處他都要用手摸摸,以手感來檢查質量。楊師傅還特別在壽材頭上費了工夫,兩邊的轅門柱略呈八字形,壽材蓋頭的紗帽高高挺起,顯示出門楣高大雄偉的派頭,父母看到都非常滿意。
割壽材同建房一樣講究竣工,稱之為“圓材”,也有吉時。這一天清早,楊師傅就開了工。他讓我用紅紙寫了兩個大“壽”字,分別貼在兩副壽材的門面上,再寫上“長命百歲”和“吉祥如意”的條幅貼到壽材的左右兩壁。他還剪了兩個紅“壽”字圖案貼在壽材尾上。一切準備就緒,親戚和鄉鄰們拿著鞭炮都來了。吉時一到,鞭炮齊鳴,好不熱鬧;加上圓材的酒宴一鬧,整個山村都充滿了喜慶氣氛。這時的楊師傅坐在主席位上,接受大家的敬酒,滿面紅光,十分開心。
(責任編輯:亞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