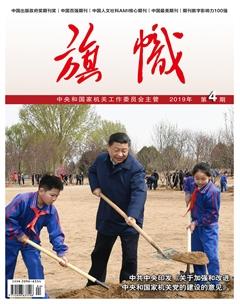關于違規兼職取酬行為的辨析
趙艷群
典型案例
王某,中共黨員,某農委副主任(副處級)。經查,王某在職期間未經組織部門批準,于2012年1月至2015年10月,私自受聘擔任某高校科研中心“特聘教授”,其間領取酬勞10萬余元。2017年1月王某退休后,自行受聘到某農產品流通協會擔任會長(未領取薪酬),并在外省某上市股份公司擔任獨立董事。截至2017年12月組織調查時,共計領取董事津貼15萬余元。
處理意見
對王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根據規定,黨政領導干部不得在營利性組織中兼職取酬。王某退休前擔任某高校科研中心“特聘教授”,該中心并非營利性組織,王某在此兼職應不受有關禁止性規定的限制,不構成違紀;至于王某退休后的兩次兼職,一次未領取薪酬,一次是到原任職務管轄地區之外的企業擔任董事,本人并沒有借助原有職權的影響力謀取私利,因此均不宜按照違反廉潔紀律定性處理。
第二種意見:王某身為黨員領導干部,未經批準兼職或兼職取酬,違反了有關廉潔自律制度,損害了國家機關的清廉形象和公職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所謂違規兼職取酬,是指黨員干部違反規定,未經批準在各類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等兼職,或者雖經批準兼職但違規取酬的行為。公職人員是具有特殊身份的群體,違規兼職或兼職取酬,容易滋生權錢交易,帶來利益輸送等腐敗問題,影響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必須嚴格禁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陸續出臺規范違規兼職取酬的政策文件,《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幾次修訂,也均將違規兼職取酬明確規定為違反廉潔紀律的行為。但在利益誘惑面前,總有人罔顧紀律底線,對此心存僥幸,妄圖逃避監管,結果必將受到紀律的懲處。具體辨析如下:
第一,違規兼職取酬的行為主體不限于在職黨員干部。根據有關規定,對列入兼職取酬禁止性范圍的人員,按照是否在職,可以分為在職黨員干部、退出現職尚未辦理退休手續(即退居二線)的黨政領導干部及已經辦理退休手續的領導干部等三類;按照行業領域,可以分為黨和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的黨員干部,事業單位中相當于處級及以上黨員領導干部,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及其分支機構的領導班子成員,鄉鎮黨員領導干部和基層站所的黨員負責人等。案例中,王某作為行政機關中的副處級黨員領導干部,不論在職還是退休,均應受到有關規范違規兼職取酬行為條款的約束。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將退居二線和退休人員也納入規范范疇,就是為了防止其搞權力投資,利用在職時基于公職和身份產生的影響力,幫助所兼職企業謀取不當利益或不當獲取競爭優勢。這有利于形成對公職人員的閉環監督,防止出現監管真空。

第二,違規兼職取酬的兼職單位不限于營利性組織。《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規定,兼職取酬的禁止性人員違反規定在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等單位中兼職或者經批準兼職但獲取薪酬、獎金、津貼等額外利益的,構成違規從事營利活動行為。可見,違規兼職取酬的兼職單位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經濟組織,如各類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個體經濟組織及民辦非企業單位等,另一類是社會組織,如協會、基金會、學會等。此外,還包括除前述兩類主體之外的其他單位。案例中,王某先后受聘擔任某高校科研中心特聘教授、某協會會長和某公司獨立董事,既有領導職務,也有非領導職務,但其未經批準兼職或兼職取酬均可能危及公權力行使,帶來被圍獵風險并影響黨和國家機關的社會形象,應當態度鮮明地給予紀律上的否定評價。
第三,兼職不取酬行為也可能構成違紀。違規兼職取酬行為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未按規定履行批準或備案手續即兼職;一種是雖經批準、備案程序進行兼職,但在兼職期間違規獲取經濟或其他額外利益(包括領取薪酬、獎金、津貼等報酬以及獲取股權等利益,或者領取超過規定標準和實際支出的通訊補貼、交通補貼等費用)。根據規定,對于前一種情形,認定行為人違紀并不以其實際獲得報酬為必要條件。《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也規定,“黨政領導干部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后三年內,擬到本人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外的企業兼職(任職)的,必須由本人事先向其原所在單位黨委(黨組)報告,由擬兼職(任職)企業出具兼職(任職)理由說明材料,所在單位黨委(黨組)按規定審核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征得相應的組織(人事)部門同意后,方可兼職(任職)”。案例中,王某先后三次兼職,均未經過必要的審批程序,即使其沒有借助職務或原任職務的便利幫助他人謀取利益,從程序上看,也均違反了有關規定。鑒于其違規兼職時間長、次數多、取酬數額較大,且在黨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斂不收手,屬于違紀情節較重,應當給予紀律處分。
此外,在處理違規兼職取酬類型案件時,還應特別注意違紀所得的收繳問題,避免行為人因其違紀行為在經濟上不當獲利。本案中,王某三次兼職中有兩次違規領取了報酬,應對此部分違紀所得及時收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