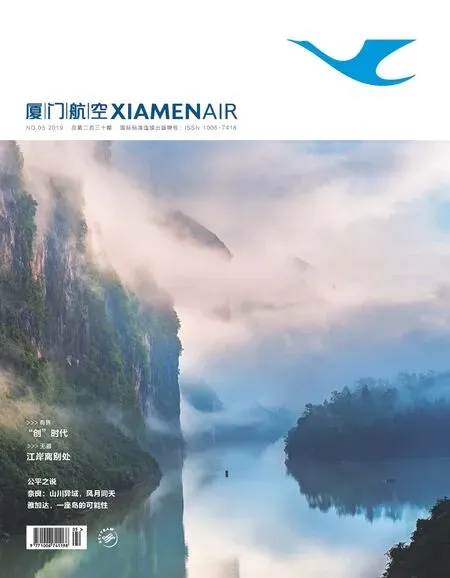買到了文創,買不到靈魂?
撰文/編輯_來
沒有哪一類產品像文創產品一樣對靈魂如此渴望,因為好的文創品往往會在實用性上落人一步,但卻借由文化的帶領,依靠具有“工匠精神”的匠人之手的打造,讓使用者了解和擁有更有品位與精神追求的生活方式,這才是文創的使命所在。在物化的外在下創造者與使用者之間完成靈魂層面的交流,最后這一環節是成就一件好文創品的關鍵,無論大小、高低、貴賤。
創造,買、賣你腦中的東西還有你的熱愛
想象力需要盡可能地打開你的感官去生活中體驗,在不斷體驗中獲得感知從而迸發想象。創造力則首先需要一個內外的動力去驅使你做一些事情。比如發明,可能就是一個事情刺激你,你要去解決問題,這是內在驅動力。上班能不能996,感到快樂、獲得成就感就成了外在驅動力。因為熱愛未必一定就能創造出好的作品,但沒有喜歡這個內在驅動力一定無法創作出打動人的產品。
對現實超越感情的冷靜判斷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則是更稀貴的素質。這三種稟賦和氣質,才構成了一種全面的創造能力。
跟上與跟不上之獨立思考
需要一個更適合更好的生活方式,獨立思考是必不可少甚至決定成敗的關鍵。但這又有些自以為是“子非魚”的設想。許多并不擅長或者喜歡思考的人仍舊可以過著看起來幸福不錯的生活,那么獨立思考是否真的在生活中那么重要?生活中有時“裝傻”比較好,無論從對痛苦與逆境的感受還是自我安慰上,都有正向作用。但唯獨在創造中,獨立思考是創造本身靈魂的靈魂。
“最大的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李開復教導很多創業者說,最大的成功就是成為最好的自己。問題是很多人不知道最好的自己是什么,所以會盲從,隨大流。大部分人“跟”,無非是“跟得上”和“跟不上”的區別。但是最優秀的人就像孟子所說的“雖千萬人,吾往矣”,他認準的目標一般人是不在意的,但是他能夠看到這個目標代表了未來。
寬容失敗
一件好的文創作品往往是用寬容堆積而成的。創造從來都是失敗多于成功,投資者缺乏對失敗品的寬容就沒有繼續下去做出成功品的基石。對于創作者本身而言,寬容同樣是一門需要掌握的技能,人們并不是平白無故便做到“寬容”,往往基于了解才能做到,對自己失敗的寬容接受與理解也正是失敗最可愛的價值所在。
敬畏成功
這個時代人們對成功的渴望已經遠遠超出了以往。但人們真的是渴望成功嗎?還是僅僅只是對財富本身的追逐?創造者本身應該對文化敬畏,對他的職業敬畏,更應該對他獲得的認可與成功敬畏。他成功的標準不是外在的、市場的、世俗的標準,不單以財富多少、公司規模為唯命是從。一個行業自身的行業內在價值被淡化,那么創造精神也就衰落了。
善意
幾年前山東的藍翔高級技工學校暴得大名,因為他們的校長對學生說:“你們要有出息,如果你們不好好學本事,我們就和北大清華沒什么區別了。” 雖然藍翔培養的開挖掘機的畢業生收入未必比清華北大的畢業生低,但依然贏來社會一片嘲笑。文憑社會,這是一個非常無奈的現實,固有的成見讓人們對于創造者本身的出身與所做產品的領域很難完全出于善意。“行行出狀元”,對我們的周邊保有善意,一件好的作品同樣可以傳遞善意。
不一定是“審美匱乏”,也可能是一種“審美懶惰”
擁有審美力的人,往往能品嘗到人生中最甜的那部分滋味。 沒有人不熱愛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本質其實就是“美生活”。
工匠精神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有品位,你要做出優質的產品,首先你要知道何為卓越,何為平庸,要有專業的品位。審美上不一定是“審美匱乏”,也可能是一種“審美懶惰”。創造者也常常會為自己的懶惰尋找借口,有時候將這種“審美懶惰”推給消費者,美其名曰:國民審美匱乏,他們不懂。這只是一場沒有終點的皮球賽。
細節決定成敗
中國的“傻子”太稀罕,“聰明人”太多了。
品位最重要的是細節,細節決定成敗。好的文創者除了有良好的創造力還需要有“傻子”般的工匠精神。愿意在精益求精和在細節上下功夫。
中國媒體有一句神評論,說中國人“老是想著job,所以永遠出不了Jobs”。一個產品要做到完美,到了后期階段,每提高1%,它的投入成本可能是以幾何級數增長的。一味追求利潤最大化,最終“劣幣驅逐良幣”必將成為不可抗的現實。沒有人可以幸免,因為創造者、投資者及使用者都曾是始作俑者。我們應從工業中學習標準和流水作業的規范,而不是因其丟失對創造品位品質的追求。
當文創為我們生活品質升級,我們也看到市場以狂歡的方式,有不斷壓榨“文創”的趨勢。我想所謂一件好的文創品的靈魂,正如我們關注自身的靈魂一樣。紀伯倫曾寫過一首著名的《我曾七次鄙視自己的靈魂》,可做一個完美結篇。
第一次,當它本可進取時,卻故作謙卑;
第二次,當它在空虛時,用愛欲來填充;
第三次,在困難和容易之間,它選擇了容易;
第四次,它犯了錯,卻借由別人也會犯錯來寬慰自己;
第五次,它自由軟弱,卻把它認為是生命的堅韌;
第六次,當它鄙夷一張丑惡的嘴臉時,卻不知那正是自己面具中的一副;
第七次,它側身于生活的污泥中,雖不甘心,卻又畏首畏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