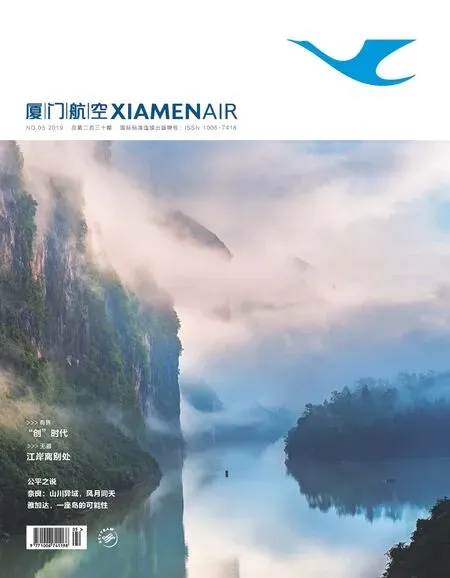“不務正業” 也是一種態度
撰文_呈子
在長袖善舞和死心眼這二者之間,有一個非常大的閾值,可以讓我們自由行走。
在國外逛書店的時候,人多到我總把“Excuse me”掛嘴上,當時還想這外國人就是愛讀書。其實很大一個原因,是國外書店觸手可及,在最繁華的街角、最偏僻的商業中心總有一家。國外很多商業社區是幾百年來早就形成的,比如倫敦的Charing Cross,17 世紀就是商業中心,人流量巨大,開幾家書店自然不愁沒人來。而在國內,商業社區起步較晚,對于這些新起的商場來說,引流是首要KPI。書店不僅是裝點門面,也得完成吸引消費者的任務。高知如北大高才生許知遠,也知道要讓單向街賣臺歷、搞活動,讓人進來,讓書店變得不那么書店,才有活路。
變化,總是引起擔憂。但市場的宏觀變化是我們要承受的,微觀才是我們有所作為的地方。當越來越多朋友約我去單向街參加一場活動,去言幾又瞅瞅藝術品,去鐘書閣打卡拍照,讀書才真正變得有趣親民,書店成了年輕人的廣場舞。這些新興的書店聚集了大量黏性很強的用戶,比如著名的西西弗。這家號稱開店第一年就能盈利的網紅書店,其實已經二十多歲了,是擁有Park 書店、矢量咖啡、“不二生活”創意空間、“7&12 閱聽課”兒童閱讀體驗空間、推石文化和《唏噓》雜志六個子品牌的綜合文化集團。
當年西西弗差點兒活不下去,創始人薛野為了拯救書店,拉來了自己在商界打拼失敗、準備出家的姐夫金偉竹。金偉竹印證了“失敗的經驗比成功的經驗更寶貴”這句話,迅速判斷出實體書店的落魄從表面看是受互聯網、電子書等的影響,實際上是因為實體書店本身的體驗服務不夠好,以及運營管理模式過于落后。金偉竹很自信地表示“懂書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懂市場才是王道”!他像打造產品一樣打造西西弗書店,確立品牌定位是“推動大眾精品閱讀”,明確用戶畫像“不是文藝青年或城市閱讀精英”,書不僅是賣給愛讀書的人,書店要讓更多客人愿意走進來,并且帶走一兩本書。
書店里開咖啡館的做法,最早就是由薛野搞起來的。慢慢地,西西弗搭建起了更多流量入口,即使你沒有買書的想法,也能因為其他因素留下來,來咖啡館小坐、買點兒文創,或者參加一場親子活動。以“書”為核心的多元化體驗,豐富了受眾層級,自然就帶來穩定的流量。這是一個良性循環,商場一方面看中這些書店可以豐富自己的商業形態、提升自己的格調,另一方面,這些書店高黏度的受眾能有效引流。
所有成功的連鎖書店,走的都是以書籍為核心,做文化類、生活類業態的衍生,比如言幾又。老牌如誠品,也早就從“誠品書店”變為“誠品生活”,打造文化生活品牌。作為當地文化地標,誠品除了賣咖啡、賣文創,還開起了酒店,而有誠品品牌的積淀,這家酒店成為閱讀文化的另一個載體,和其他酒店輕松形成區分,這個新的流量入口又能為“賣書”的核心業務助力、供血,讓書店文化具有長期穩定發展的能力和空間。
我有一個搞文化公司的朋友,跟我談文創的意義:一是讓原本無法被消費的內容成為可被消費的產品,比如博物館的藏品,原本無法被帶走,現在卻可以帶入生活,實現了普通消費者對文物及高端藝術品的消費。二是讓已經失去現實消費價值的產品符號化,煥發新的消費價值,比如回力運動鞋,現在年輕人消費它,已經脫離了產品本身,消費的是其背后的文化情感歸屬。三是讓原本已經喪失消費能力的經營場所,以文化為核心重新回歸消費場景,對消費者形成新的吸引力,書店就是典型的例子。文創等商業形態的加入,讓消費者重新回歸書店,在重新贏得人流后,書店就有了產生其他商業價值的可能。某種程度上是文創挽回了實體書店的閱讀功能,而不能簡單說是對于消費者的附和。
贏得人流、挽回閱讀。這就是為什么,西西弗無論是產品還是活動,從來不是定位文青。它在沒有許知遠這樣的大V 背書的情況下,做到遠超單向街的用戶數和下沉度,靠的是更大眾化的定位,賣有文學價值的書,也賣正能量雞湯和成功學以及各式各樣的活動和產品,把非閱讀人群吸引過來轉化為讀書人。這個過程也許漫長,但卻是有效的。它沒有標榜讀書這種高端生活方式,而是把讀書滲透到大家的生活中去,真正拓展了閱讀這個垂直領域的圈層。
追隨市場并不意味著淪陷和附和,大眾不意味著盲目和低俗,它也有自我調節和提升的能力。
國外文化產業都是靠親民化的多元開發才延續百年,連英國皇室都放下架子把自己頭像到處印、花式衍生。
其實所有的文創,一直以來從未損害根莖分毫,反而讓它更為根深蒂固。在長袖善舞和死心眼這二者之間,有一個非常大的閾值,可以讓我們自由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