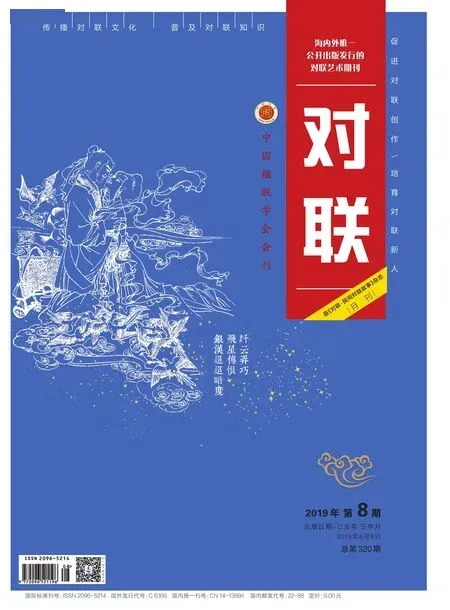明聯與一代之文學
□ 咸豐收
(402160重慶市永川區昌州大道三八八號桓大中央華府)

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古典文學領域一直流行這樣一種說法——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此一說言簡意賅,概括精當,遂對中國文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來,筆者沉埋于故紙堆,整理明代對聯之史料,沉思考索之余,若有所得,且就『一代之文學』這一話題一申管見。
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學
最近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之觀點源自王國維為自作《宋元戲曲考》所寫之序言,是受六朝及元明以來『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和『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文藝思想的影響而產生。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序言寫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此段文字中,王國維先生將歷代有鮮明創見的時代文學一一列出,并借『后世莫能繼焉者也』表達了對歷代創設新文體之贊譽。王國維的這段論述,在近現代學界中受到普遍的激賞并影響頗深。當今學人多認為這一精辟論斷是對中國歷代文學的總體進程和文學史規律認識的集大成的觀點,因而被概稱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說。
審視一代文學思想之嬗變,我們可以發現歷代的文藝主張是有異有同的。最早認識到文學新舊代嬗的發展規律,并提出創見的是南北朝蕭子顯。他在《南齊書·文學傳序》率先提出:『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一若無新意,不能代雄。』此后的劉勰、沈約等人也都有類似的文學認識。但是,真正明確意識到文體與時代的聯系,并把文體遞嬗和時代變遷并舉,而提出鮮明一代文學論斷的則是元人。
元代虞集曾提出:『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后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開于氣數音律之盛。』此各代之『絕藝』的思想影響深遠。此后,元人羅宗信在《中原音韻序》中說:『世之共稱唐詩、宋詞、大元樂府,誠哉!』羅宗信將『宋之道學』改為『宋詞』,見解有所創新。元末明初的葉子奇在《草木子》卷之四上也提到了:『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獨北樂府耳。』他在闡述前人觀點的基礎上,順利補充提出了『晉以字』的文藝主張。
明代人在繼承發展的基礎上,甚至認為文體的選擇決定了作家的成就和地位。胡應麟在《少室山房類稿·歐陽修論》中認為:『自春秋以迄勝國,概一代而置之,無文弗可也。若夫漢之史、晉之書、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則皆代專其至,運會所鐘,無論后人踵作,不過緒余。即以馬班而造史于唐,李杜而拔詩于宋,吾知有竭力而亡全能矣。』胡氏在綜合元人文藝主張的基礎上,對文體時代意義的認識又有了超越。袁宏道與卓人月則肯定了明代民歌的地位。卓人月說:『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為我明一絕耳』。明代王思任則說:『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專,則言不傳。漢之策、晉之玄、唐之詩、宋之學、元之曲、明之小題,皆必傳之言也。』
到了清代,對于一代文學之主張,顧炎武、吳偉業、焦循等人也各有見解。焦循在全面總結元明以來文體代嬗的文學發展觀后,曾獨到地闡述:『…… 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于八股…… 洵可繼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立一門戶…… 夫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明八股』之文藝主張又與他說不同。
此后,王國維先生承襲總結,在《宋元戲曲考》序言中為確立元曲的地位,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胡適在提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時,提到了將白話小說列入了明清時期的代表性文體,應是『明清小說』文體代嬗發展觀的濫觴。
二、一代文學之新思考
章炳麟先生在《文學說例》中曾說:『韻文完具而后有散文,史詩功善而后有戲曲。』中國古典文學歷來有散文與韻文之分。如詩、賦、詞、曲和有韻的頌、贊、箴、銘、哀、誄等一類,人們喜歡將之稱為韻文,以與散文相對。而在『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一說法中,『唐詩、宋詞、元曲』明顯屬于韻文,『明清小說』則為散文(當然其章節中也會夾雜有部分韻文)。縱觀諸多一代文學之主張,一代文學觀之提出大多是韻散籠統。筆者便思酌,這樣將散文與韻文并列提出是否妥當、是否合適呢?我們該如何來界定分類才能更好地呈現中國古典文學之發展呢?這一問題或許值得我們思考。
對于歷代之文學,興起之初往往多不被人們所認可。《詩經》所收錄之詩,采集自民間,最初也未成大雅,直至經孔子刪選后,才被后世奉為經典。楚騷來自民間,因屈原之吟誦創作方一舉成名。此后復有漢賦之興盛、六代駢語特出。至唐代,因科舉所需,近體詩又成一代之文學。接下來就是宋之詞了,創設之初,宋詞地位也沒被時人所認可。至于元之曲,王國維先生之《宋元戲曲考》也提到了其最初的尷尬地位:『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托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于錄;后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且,王國維先生對于『一代文學』之論述也到此即止,于明清文學之代表沒有涉及。直至民國,胡適、魯迅等人在西方文學的影響下將小說提了出來,可能才形成了『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一代文學之新主張。
審視逐漸發展變化的文體代嬗觀,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思考。近來,不少學人鑒于此說之不圓滿,也紛紛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筆者不揣固陋,結合自己整理對聯史料之思考,現提出一點自己的看法。中國文學歷來有韻散之分,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應在韻文范疇(又或稱之為詩學)之列為好,而先秦散文、兩漢辭賦、魏晉小品、四六駢文、唐宋散文、明清小說倒是可以放在散文范疇之列。在這里,只有兩漢辭賦注重對偶對仗和音韻,有些不好分類,說是詩詞曲賦類的詩學,卻又篇幅長闊;說是散文,卻重聲韻對仗,且韻散結合。
在這里筆者思考的是,可否將從詩詞曲賦之對仗衍生而出的明代對聯文學,以及清代嘉道年間產生的詩鐘文學納入詩學范疇來考量,可為詩學陣地再添新生力量呢?明代對聯夠不夠得上是推陳出新之一代文學呢?它可不可以成為繼唐詩、宋詞、元曲之后,中國詩學陣地的一種新文學呢?雖然,清代對聯文學在繼承明代對聯文學的基礎上,在嘉慶道光以后,迎來了井噴式的發展,雖然,流傳至今的明代對聯從數量上不能壓倒清代對聯,但其應用之廣泛、技法之嫻熟、文采之飛揚,同樣不容小覷。這樣的話,『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聯、清詩鐘』或許更符合中國古典文學韻文發展之事實。至于為啥要將『明聯、清詩鐘』歸到韻文(詩學)范疇,只是因為他們也注重對仗,本來就為詩之余。至于散文,我們大可以另外排列,或許可以按照『先秦散文、兩漢辭賦、魏晉小品、四六駢文、唐宋散文、明清小說』來重新思考。
三、對聯為明代特出之文學
因為梁章鉅《楹聯叢話》之影響巨大,今人一般將『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以及『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作為較早的對聯來看。『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作為桃符題句,看做對聯是沒啥問題。但是『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作為對聯來看就有問題了。此句來自《五代史補》卷五周二十三條,原文為:『僧契盈,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游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游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越地去京師三千余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對曰:「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梁章鉅將原文做了篡改,說:『契盈因題亭柱云:「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弄得好像五代真有題署聯一般。另外,梁章鉅在《楹聯叢話》里提到了壽聯:『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鐘百歲人』也是將壽詩之摘句篡改而來。考宋代有桃符、春帖子題句之習俗,見之于宋代詩話者有不少。元代亦有題春之風俗,此時多稱之為春帖子,流傳下來的有蒲道源《閑居叢稿》中十四副春帖,以及虞集《道園學古錄》中十四副門帖。宋元兩代,也只停留在貼桃符、春帖子上。據此來看,筆者認為如果將唐宋元時期作為對聯文學的萌芽階段或許還說得過去。
明代開始,對聯文學似乎一夜蘇醒,被廣泛應用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舉凡節慶、饋贈、哀挽、祝壽以致題署,都可見其應用。作為對聯文學的專用名稱——『對聯』二字也正是在此時,正式被作為特殊門類的文學稱呼來使用的。目前看,最早提及『對聯』二字的,是明代陸深《金臺紀聞》中的一則聯話:『孝廟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朝作對聯云:「一雙探花父,兩個狀元兒。」時張宗伯升己丑狀元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為兵部主事。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己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瓚則壬戌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時喬梓,前此未之有也。』『對聯』在此時已經被作為一種文體名稱,且得到了當時人們的認可。陸深之后,更晚些的明代文人也都普遍認可了『對聯』這一文體及其名稱。如郎瑛所撰《七修類稿》、何良俊所撰《四友齋叢說》、李詡所撰《戒庵老人漫筆》、李樂所撰《見聞雜記》、沈德符所撰《萬歷野獲編》、王同軌所撰《耳談》、呂毖所撰《明朝小史》都沿用了這一說法。像我們所熟知的『春聯』『衙宇聯』『挽聯』『壽聯』『園林聯』,以及『對聯』『對語』『對句』『楹聯』『楹帖』『春帖』『春對』…… 等稱呼也是在明代被廣泛使用并得到人們認可的。可見,明代是對聯及其所屬各門類正式定名并興盛繁榮的時期。流傳至今的,疑似托名摘趒軒刊馮夢龍增編的《增補批點圖像燕居筆記》,在明末就已經將對聯按照其功用和刻掛場所分為六十類。
明代中后期,人們對對聯文學的認識也在不斷加深。特別要提到的是明末的張岱。因為仰慕徐文長,張岱將徐文長所寫文收集整理為《徐文長逸稿》,其中就收錄有對聯一類,并題寫序言:『昔人未有以柱對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長之逸稿始』。這才有了俞樾在《茶香室三鈔》中的評價:『按今人刻楹聯入集中,此其濫觴,然但知為楹聯,莫知為柱銘矣。』可見以張岱為首的越中文人已經有了強烈的對聯文體意識,很早就有在文集中刊刻對聯之風。而將對聯收入文集這股風氣,在更早之時便已遍布全國。從目前現有資料來看,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墨客,從蜀晉魯贛到江浙蘇杭,各地文人無不有對聯收入文集中,如《中麓山人拙對》《中麓山人續對》《小窗幽記》《娑羅館清言》《謝華啟秀》《偶譚》《罔措齋對聯》《半九亭集》等對聯匯集本的大量涌現,想來絕非偶然,應是當時對聯文學蓬勃發展的結果。綜合來看,從明初至明末,明代涌現出了李開先、喬應甲、楊慎、徐渭、任瀚、倪元璐、楊鶴、張岱等一大批對聯名家,涉及到成百上千人。以《笠翁對韻》《聲律啟蒙》作者為代表的一大批所謂清代對聯寫手,在鼎革之際也多身跨兩朝,起到了傳承發展之作用。再如,清代樓堂館所刻掛楹聯的習俗其實也是從明代繼承而來。
所以,筆者在此提出一個新觀點:從詩學范疇來看,明代特有之文學非對聯莫屬了。開創一代新文體之明聯,或許比民歌、八股制藝更能代表明代,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筆者提出此說,旨在與對聯界以及各界同仁共同交流探討,早日讓對聯在中國文學史上擁有其該有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