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筆下的陜甘蘇區
李榮珍
斯諾是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他的一生與中國結緣。早在1936年,當世界上大多數人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是否還存在的情況下,斯諾在宋慶齡的安排和幫助下,沖過重重封鎖,進入陜甘蘇區(當時陜甘蘇區剛擴大為陜甘寧蘇區),采訪了這塊土地上的許多人和許多事,用生花之筆,向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和他們率領下的陜甘蘇區軍民,介紹了舉世無雙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他對中國革命作出了超過一個記者職責的杰出貢獻,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這位老朋友的。
陜甘蘇區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這塊紅色區域很長時間不為人知。斯諾是向世界介紹陜甘蘇區的第一人,在他的筆下,我們看到了陜甘蘇區的成長史,看到了創建這塊根據地的英雄劉志丹等人,也看到了黨中央落腳后,這塊蘇區發生的新變化。
斯諾將陜甘蘇區的創建人劉志丹比喻為“羅賓漢”
斯諾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記》一書中,有專門的篇章,即第六章名為“紅星在西北”,是專門寫陜甘蘇區的,其中的開篇標題叫“陜西蘇區:開創時期”,通篇寫了被斯諾稱作“現代俠盜羅賓漢”——劉志丹的事跡。

1979年版《西行漫記》
斯諾筆下,說到江西、福建、湖南的共產黨人逐步建立反對南京政府的根據地時,中國其他地方到處都出現了紅軍。而在“西北方向的遠遠的山區里,另外一個黃埔軍校生劉志丹當時正在為目前的陜西、甘肅、寧夏的蘇區打基礎。劉志丹是個現代俠盜羅賓漢,對有錢人懷有山區人民的一貫仇恨。在窮人中間,他的名字帶來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財中間,他成了懲奸除惡的天鞭”。文章告訴人們,在南方,共產黨人在創建根據地,同樣在偏遠的西北,也有劉志丹這樣的共產黨人在創建根據地。
在敘述了劉志丹的身世和他領導的起義后,直接進入介紹劉志丹創建陜甘紅軍和陜甘邊根據地的艱難過程:“劉志丹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的生涯仿佛一個萬花筒,其間歷經各種各樣的失敗、挫折、搗亂、冒險、死里逃生,有時還官復原職,不失體面。他率領下的小支部隊幾經消滅。”斯諾寫了劉志丹的傳奇,寫了他的出生入死,也寫了他為之努力所換來的成功。“到一九三二年劉志丹的徒眾在陜北黃土山區占領了十一個縣,共產黨特地在榆林成立一個政治部來指導劉志丹的軍隊。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陜西的第一個蘇維埃,設立了正規的政府,實行了一個與江西類似的綱領。”從這些描述看,斯諾的采訪確實非常深入,了解到很多陜甘邊根據地初創時期的情況。雖然個別史實略有出入,但輪廓大致是對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確實初創于1932年,3月底至4月初,在甘肅正寧縣的寺村塬成立了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這可以視作陜甘邊的第一個蘇維埃臨時政權,而根據地的確立是以政權為標志的。但這個根據地在當年8月就失去了。1933年4月,在陜西銅川的照金再次成立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根據地已發展到方圓400余公里,涉及旬邑、淳化、三原、耀縣、宜君、正寧等縣域。而這時的根據地正如斯諾所說,是“正規的政府”,實行的是和江西的中央蘇區一樣的綱領。

周恩來歡迎斯諾到陜甘蘇區
斯諾寫到了蘇區的發展:“到一九三五年中,蘇區在陜西和甘肅控制了二十二個縣。現在在劉志丹指揮下有二十六、二十七軍,總共五千人”。“在南方紅軍開始撤離贛閩根據地后,陜西這些山區紅軍卻大大加強了自己,后來到一九三五年,蔣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總司令張學良少帥率領大軍來對付他們。”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大發展是在第三個時期,即1934年,在甘肅華池南梁地區又一次建立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成為這一地區的蘇維埃臨時革命政權,緊接著在蘇區大發展的基礎上于11月成立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這是正式的蘇維埃政權形式。政府主席由被稱為“娃娃主席”、只有21歲的習仲勛擔任,陜甘邊區軍委主席是劉志丹。到1935年2月,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和1935年1月成立陜北省蘇維埃政府的陜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坐在了一起,在周家鹼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由劉志丹任軍委主席。接著,在劉志丹指揮下,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并肩作戰,連續打下延長、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邊六座縣城,把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和陜北革命根據地連在一起,形成陜甘革命根據地。斯諾筆下雖然沒有細寫到這種程度,但從他的敘述中已能看到蘇區發展的端倪。
雖然后來陜甘蘇區發生的錯誤“肅反”背景有些復雜,但斯諾提到了這件事,并寫出了毛澤東帶領的黨中央到達陜甘蘇區后對這次錯誤的糾正。斯諾寫到:“就是在這個奇怪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南方的紅軍先遣部隊,即在林彪、周恩來、彭德懷、毛澤東率領下的一軍團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他們對這奇怪的情況感到震驚,下令復查,發現大多數證據都是無中生有的”。“他們立即恢復了劉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職。”陜甘蘇區的“肅反”發生在中央紅軍到達前一個月,當時新成立的陜甘晉省委下令在蘇區進行“肅反”,結果把劉志丹、習仲勛等陜甘蘇區的黨政軍領導人抓捕起來,有些人遭到殺害,錯誤“肅反”給陜甘蘇區帶來嚴重危機,好在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及時到達陜甘蘇區,毛澤東下令“刀下留人”,并速查真相,解決了錯誤“肅反”問題,釋放了劉志丹、習仲勛等人,解救了蘇區危難。

劉志丹
斯諾寫到了劉志丹的犧牲:1936年為抗日而進行的東征,劉志丹“在那次戰役中表現杰出,紅軍在兩個月內在那個所謂‘模范省攻占了十八個以上的縣份。但是他在東征途中犧牲的消息,不像許多其他類似的消息那樣不過是國民黨報紙的主觀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領導游擊隊襲擊敵軍工事時受了重傷,但紅軍能夠渡過黃河靠他攻占那個工事。劉志丹被送回陜西,他雙目凝視著他幼時漫游的心愛的群山,在他領導下走上他所堅信的革命斗爭道路的山區人民中間死去。他葬在瓦窯堡,蘇區把紅色中國的一個縣份改名志丹縣來紀念他。”斯諾這段文字充滿了感情,贊揚劉志丹在東征中創立的不朽功勛,惋惜他真實的犧牲,并說到他在走上他引導的革命斗爭道路的陜甘蘇區人民中長眠。這句話正印證了毛澤東為劉志丹的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黨和人民為了永久紀念劉志丹,將他的出生地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讓他的英名與世長存。

斯諾的坐騎馳騁在陜甘寧邊區
陜甘蘇區的發展與劉志丹等人的正確領導是分不開的,但斯諾從個體作用看到了更廣闊的視角:“雖然西北這些蘇區是圍繞著劉志丹這個人物發展壯大的,但不是劉志丹,而是生活條件本身產生了他的人民這個震天撼地的運動。要了解他們所取得的任何勝利,不僅必須了解他們所為之奮斗的目標,而且要了解他們所反對的東西。”這一點也恰恰點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總綱領,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由此看,斯諾確實不僅僅是一個新聞記者,而且是有著敏銳眼光的觀察家,更是中國共產黨人最誠摯可靠的朋友。
斯諾筆下處處可見、生動鮮活的陜甘蘇區軍民
斯諾在陜甘蘇區的采訪不受任何限制,在蘇區和前線,從領袖、紅軍將領,到廣大干部、群眾和士兵,斯諾廣泛接觸各類人員。他不僅能采訪到蘇區領導人,也能接觸到蘇區的普通人士,因此,他筆下的陜甘蘇區多姿多彩,人物生動有趣。難能可貴的是,1936年7月底到9月下旬,斯諾和馬海德醫生還親自在前線目睹了彭德懷率領紅軍主力部隊浴血奮戰的場景。《西行漫記》不僅在當時讓人大開眼界,即使讓今天的讀者看來,依然讀趣盎然,引人入勝。
“打倒吃我們肉的地主!”“打倒喝我們血的軍閥!”“打倒把中國出賣給日本的漢奸!”愛憎分明的口號,是給斯諾進入紅區的第一印象。而這種印象,隨著斯諾深入蘇區,越來越深刻。
斯諾發現,紅軍住在村莊,與老百姓和睦相處:“紅軍能夠這樣不惹人注目地開進一個地方,是不是紅軍受到農民歡迎的原因?附近駐扎一些軍隊似乎一點也沒有破壞農村的寧靜。”斯諾和一群只有10歲左右的孩子們攀談,他問孩子們對共產黨員的印象,孩子們說:“共產黨員是幫助紅軍打白匪和國民黨的人”,“他幫助我們打地主和資本家”。斯諾又問,蘇區還有地主和資本家嗎?孩子們說跑了。為什么跑,孩子們說,是因為“怕我們的紅軍”。這讓斯諾認識到,共產黨員在蘇區是多么受歡迎,孩子們引以為自豪的主觀世界里,也擁有屬于我們自己的紅軍。

在陜北時期的斯諾
斯諾在《西行漫記》里,以專門的篇幅寫了他曾經看到的西北等地受災后的種種慘景,寫了人民深受地主盤剝的悲慘生活,也寫到人們想改變舊社會的心愿。他筆下,寫出了西北農村特別是陜甘邊境地區土地問題的實況:“在陜西,一個農民有地可以多達一百畝,可是仍一貧如洗。”為什么這樣說呢?這里人口不密集,人均占有土地多,但因為丘壑縱橫,自然條件不好,能用于耕作并能生產出果實的莊稼地并不多。所以,習仲勛主政的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在土地政策的制定上也是符合實際有自身特點的,比如土地政策中的分川地不分山地,青苗與土地一起分等具體規定,這就讓農民擁有真正的可耕土地,也能看到收成的前景。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贏得民心,廣受歡迎。因此,斯諾寫道,“我們得悉共產黨人在西北特別受人民歡迎,是不應該感到奇怪的,因為那里的情況對于農民群眾來說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都沒有根本的改善。”這里說沒有根本的改善是指國民黨統治下地主、富農的盤剝不可能改善的實際狀況。而在共產黨領導下一切都不同了。
人民把紅軍看成是自己的隊伍,動員自己的子弟參加紅軍,參軍的目的也很明確,大多數人參加紅軍是“因為紅軍是革命的軍隊,打地主和帝國主義。”斯諾采訪了許多紅軍戰士,有原紅一方面軍的,有原紅二十五軍的,更多的是原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的戰士及當地新入伍的戰士,這些戰士們搶著回答斯諾提出的各類問題,有的回答很精彩。其中一位戰士說起人民群眾對紅軍的幫助:“我在劉志丹的二十六軍里在定邊作戰的時候,我們的小分隊保衛一個孤立的崗哨,抵抗國民黨將領高桂滋的進攻。農民們給我們帶來了吃的和喝的。我們不用派人去搞給養,人民會幫助我們。高桂滋的軍隊打敗了。我們俘虜了幾個,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有兩天沒水喝了。農民們在井里放了毒逃走了。”一個甘肅農民出身的戰士說:“人民在各方面幫助我們。在作戰的時候,他們常常把小股敵軍繳了械,切斷他們的電話電報線,把白軍調動的消息告訴我們。”從這些回答中可以看出,陜甘蘇區軍民關系多么融洽和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厚魚水關系,兵民為勝利之本的道理在這里得到充分證明,陜甘蘇區之所以能夠得以發展鞏固,正得益于有著雄厚的可靠群眾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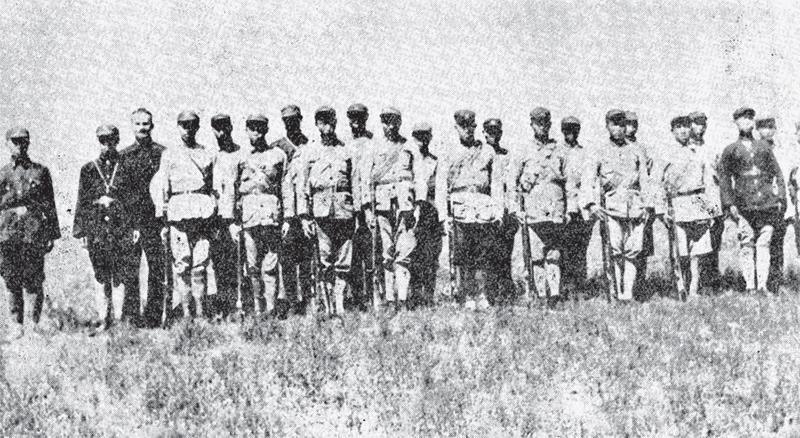
斯諾和紅軍指戰員在一起列隊
斯諾了解了陜甘蘇區人民反對的是什么,擁護的是什么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里,肯定地說,存在著早已成熟的實行變革的條件。這里,肯定地說,存在著人們要起來反對的東西,即使他們還沒有斗爭的目標!因此,當紅星在西北出現時,難怪有千千萬萬的人起來歡迎它,把它當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斯諾看紅軍長征落腳陜甘蘇區的意義所在
對于剛剛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來到陜甘蘇區的中央紅軍,斯諾為之震撼,他滿懷欽佩之情,對長征這一偉大事件做了激情澎湃的報道。他說:“冒險、探索、發現、勇氣和膽怯、勝利和狂喜、艱難困苦、英勇犧牲、忠心耿耿,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體現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歷史中了。”斯諾經過采訪,認為長征的統計數據是觸目驚心的,“紅軍一共爬過十八條山脈,其中五條是終年蓋雪的,渡過二十四條河流,經過十二個省份,占領過六十二座大小城市,突破十個地方軍閥軍隊的包圍,此外還打敗、躲過或勝過派來追擊他們的中央軍各部隊。他們開進和順利地穿過六個不同的少數民族地區,有些地方是中國軍隊幾十年所沒有去過的地方。”斯諾筆下的長征歷程,有詳細的敘述,從“舉國大遷移”起,長征途中的戰斗,經歷的苦難,走過的雪山草地,斯諾寫來都如同親身所歷,敘述真實感人。斯諾已完全被長征這一壯舉所吸引,他告訴每一位讀者:“不論你對紅軍有什么看法,對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什么看法(在這方面有很多辯論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業績之一。”在《西行漫記》里的“長征”這一篇中,斯諾是以毛澤東抄寫給他的一首詩作為結束語的,這就是毛澤東非常著名的詩篇——《七律·長征》,而這首詩恰恰是毛澤東對偉大長征所作的詩意的總結。

斯諾和紅軍指戰員在一起列隊
斯諾在馬不停蹄的采訪中,既記錄下每個時段、每個細節,也時時作出歷史的思考,作出一些判斷。從他的筆下,可以看到對長征勝利偉大意義的敘述,也可以看到長征落腳陜甘蘇區后,中國將發生新的變化。斯諾說:“他們筋疲力盡,體力已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終于到達了長城下的陜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即他們離開江西一周年的日子,一方面軍先鋒部隊同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在陜西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小小根據地的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這里,斯諾點明的小小根據地和二十六、二十七軍恰恰說的就是陜甘蘇區和陜甘紅軍,再次印證陜甘蘇區對紅軍長征落腳的重要作用。斯諾說:“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么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進軍到戰略要地西北去,無疑是他們大轉移的第二個基本原因,他們正確地預見到這個地區要對中、日、蘇的當前命運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后來的歷史證明,他們強調這個原因是完全對的。這種宣傳上的巧妙手法必須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造成英勇長征得以勝利結束的原因。”這是斯諾獨到的眼光所在,一個是北上抗日的萬里長征,另一個是到達能夠實現北上抗日的戰略區域。這些正是紅軍長征勝利后,能夠盡快投入抗日戰爭的原因和基礎,斯諾用他的筆又一次見證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度政治預見性。
斯諾筆下也可看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端倪。他說:“但在他們借用的過程中也有不少改動,俄國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經大加改動以適應具體環境而仍存在下來的。十年的實際經驗消滅了不分青紅皂白一概進口的做法,結果也造成蘇維埃制度中帶有完全是中國式的特點。”實際上,長征歷史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漸進式發展的見證。紅軍長征中的轉折點就是遵義會議,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地位,使中國共產黨能夠擺脫教條主義影響,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問題。

寫作《西行漫記》時的斯諾
斯諾在即將離開蘇區時,再一次與毛澤東深談,毛澤東談話里有著重大的信息,這就是抗日戰爭即將開始,中國共產黨人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后,中國時局將起重大變化。毛澤東對斯諾說:“我們堅持的團結的基本原則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則。為了要實現這一原則,我們認為必須建立一個國防民主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必須是抵抗外國侵略者,給予人民群眾公民權利,加強國家的經濟發展”。斯諾問這樣一個政府的法律是否也會在蘇區實施?毛澤東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這樣一個政府應該恢復并再次實現孫逸仙(孫中山)的遺囑,和孫中山在大革命時期提出的三個“基本原則”,即聯合蘇聯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聯合中國共產黨;保護中國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毛澤東認為,如果國民黨里開展了這樣一個運動,“我們準備同它合作并且支持它,組成反帝統一戰線,像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那樣。我們深信,這是拯救我國的唯一出路。”在對時局變化產生重要影響的西安事變尚沒有發生前,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這是偉大的家國情懷,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因此,斯諾說:“這肯定地必須認為是你們黨近十年歷史中最重要的決定”。
斯諾為時四個月的采訪,改變了他的一生,他在與陜甘蘇區軍民的密切接觸中,終于看到并深刻認識到中國的希望所在是中國共產黨。他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共產黨最忠誠的朋友也就是歷史的必然。他以自己的生花之筆,宣傳史無前例的紅軍長征,宣傳充滿希望的紅色中國,宣傳中國共產黨人的所思所想所為。他的報道,貴在真實可信,打破了國民黨方面對共產黨、對紅區的長期的歪曲宣傳,西方媒體也出于好奇大量刊發了斯諾的真實報道,使得紅軍的事跡、中國共產黨人的為民主張以及在陜甘蘇區的實踐能夠在國內外廣泛傳播。(編輯 黃艷)
作者: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