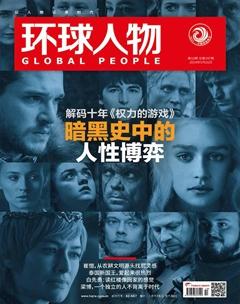家國情懷 福澤后學
蔣熙輝

2018年12月18日,87歲的王家福老師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稱號,獲頒改革先鋒獎章,獲評“推動依法治國的理論創新者”。獲悉這一消息,我十分欣喜。這是黨和國家對一位心系人民、追夢法治、勠力推動理論創新的學者的無上尊崇和極高榮譽。
十余年來,我與王老師從不識到相識、相知,雖未能榮列老師門下,卻獲益良多。時常想起他以深厚之家國情懷,心系黨和國家的法治事業,推動中國法學繁榮與法治進步,學問事業福澤后學,令我輩高山仰止。
山水迢迢,心系國家和人民
我在西南政法大學念本科時,初習法律不久,讀到《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一書,主編就是王家福,這是我第一次知道老師的名字。
后來得知王老師曾兩度到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領導講法制課,特別是1996年的依法治國講座,直接推動了依法治國方略寫入黨的十五大報告和載入憲法,心中十分崇敬。當時的我絕沒有想到,自己后來竟有機會與王老師見面,并近距離協助他工作。
從北京大學博士畢業后,我進入社科院法學所工作。在一次研討會茶歇時,我看到一群人簇擁著一位老人在討論,走近后才知道這就是法學大家王家福。只見他個頭不高卻氣宇軒昂,寬容謙和又望之凜然。在平靜地聽完論述者意見后,他條分縷析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平和的敘述中浸潤著法理。在回答聽者問題時,他簡明扼要,令聽者或點頭或沉思。
那時他已卸任行政職務,但兼任的學術職務不少,考慮到他已七十高齡,法學所就派我當其助手。剛接到這個任務時,我有些誠惶誠恐,畢竟要如此近距離地和大師級學術前輩打交道——想干好又怕干不好。記得第一次單獨見面,王老師只是簡單問了問我是哪里人、在哪兒上的學,得知我在西南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都學習過,他若有所思地“哦”了一聲,說:“我們還是校友!”一句簡單的暖心話,瞬間讓我放松不少。這樣幾次接觸下來,我就再無緊張之感了。
我的工作是協助王老師整理學術資料、進行學術交流、謄錄文稿。熟悉之后,去王老師家的次數也多了,每次和他談人談事,也說自己的困惑。王老師不健談,但總是微笑地看著我,關鍵時候點撥一句、叮囑一聲,師母則慈祥和藹、噓寒問暖,待我如同家人一般。
法治理論之深奧,人權法治事業之艱難,參與者和實踐者深知個中滋味。但聽王老師講法治,并無艱深之感。“民法典應寫入知識產權以加強對創新的保障”“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等論述,都以通俗易懂的話語闡述深奧的法理;“物權法是以人為本的法,沒有財產、沒有物權,談何尊嚴、談何體面、談何幸福?”看似家常話,卻透露出老師作為法學家超凡的智慧和擔當。
這份智慧與擔當在王老師年輕時就已深深埋下種子,同他深厚的家國情懷密不可分。
1931年,王老師出生于四川南充一個偏僻、美麗的小鄉村,家境并不富裕。新中國成立前,他在重慶求學,正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親眼目睹了日軍飛機對重慶的狂轟濫炸,目睹了3000多人死于轟炸的慘案,親身經歷了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獨裁和貪污腐敗,向往民主、自由、和平,期望國家的新生。因參加當時的“反饑餓、反內戰”游行示威活動,他被開除了學籍,重慶解放后才回到學校繼續學業。
1950年,懷著對新中國的熱愛和對未來的憧憬,王老師與同學一起北上,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在北大學習期間,他聽過錢端升先生講新民主主義理論,聽過張志讓先生講憲法課,參加過歡迎馬寅初先生就任北大校長的隆重儀式……1951年8月,他參加了中央土改團,赴廣西柳城搞土改工作。回憶起這段經歷時,王老師對我說:“這大大加深了我對中國社會特別是農村的了解,提高了我做群眾工作的能力。”
1952年7月土改結束,適逢國家院系大調整,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和浙大的法學院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王老師又與20多位同學一起奉調參與建校工作。1954年上半年,他參加了留蘇研究生考試并被錄取,于翌年進入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現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法律系,師從著名民法學家奧·沙·約菲教授,攻讀法學副博士學位。半個世紀后,王老師對我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滿懷深情:“國家如父母般為每一位留蘇學生細心準備了行囊,還通過學校給每位留蘇研究生提供每月700盧布的生活費,讓我們可以毫無后顧之憂地全身心投入學業。”
經過刻苦攻讀,王老師在1959年6月獲得了學位,懷著報效祖國的強烈愿望踏上了歸國之路。回國后,他被分配到法學研究所工作,想得最多的就是為國家多做一些事。經過幾十年的勤耕不輟、潛心鉆研,王老師厚積薄發,在民商法領域做了許多開創性研究。改革開放后,他和團隊提出的許多觀點可謂“石破天驚”,如提出土地使用權可以轉讓,提倡保護知識產權,建議制定公司法、科技合同法、反壟斷法等,后來均被決策層和最高立法、司法機關采納。
此外,王老師先后參與了《民法通則》《公司法》《物權法》《民法典》等多部民商事法律的起草,是民商事立法進程的參與者和見證者。著名民法學家江平老師曾極力稱道王老師的民法思想和高超智慧,稱他是民法學界的扛旗者,帶領民法學界確立了民法的應有地位和基本思想、基本體系,“體現了民法的平等精神,開創了法學學術領域的正氣”。

1984年,王家福(右二)帶領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民法室同事到武漢調研。

2005年,王家福出席學術研討會。
不改初心,勠力推動法治前行
王老師是依法治國方略確立與實施的推動者和見證者。對依法治國的研究,貫穿了他的學術生涯。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致力于推動國家治理法治化,是他治學的一個重要領域。
早在1979年9月,王老師與劉海年、李步云等專家參與起草中央《關于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時,就使用了“法治”的概念。王老師曾對我回憶,1996年2月,他在中南海懷仁堂為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主講依法治國課時,向中央領導闡釋用“法治國家”要比用“法制國家”好,因為“法制”涉及的是靜態的制度、規則、法律條文,而“法治”則涉及治理理念變革和治理思想轉型。從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是社會歷史進步的體現,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標志。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終被黨的十五大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兩年后,“依法治國”被載入憲法,其中凝結了以王老師為代表的法學家群體推動中國法治進步的心血。
王老師曾對我說:“做人要有一顆金子般的心。”他的意思是,做人要始終有感恩之心、報答之情、報效之志。無論境遇起落、事業順逆,王老師都沒有改變初心,堅定了要把社會主義建設納入法治軌道的信心,堅定了推動國家治理朝著法治化發展的信念。正是基于一片赤誠,他才有了那些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的理論創新。
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構想,是王老師治學的另一用力之處。1995年1月,王老師提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的論斷,并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設提出了諸多富有創建性的構想,為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完善奠定了理論基礎。
今天看來,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兼顧“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必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但在20世紀90年代,理論界曾認為只要搞了市場經濟,一切自然會好起來,但實踐證明,只有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才是好的市場經濟。王老師在20多年前提出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體系的構想,是具有深厚學術積累和勇氣智慧的。
2009年,王老師入選中國年度法治人物,那一年的主題是“法治的力量”。當時的頒獎詞是這樣寫的:“他(王家福)用50年時間做了兩件事:提出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想;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樣一個國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在頒獎現場,主持人問王老師:法治的力量是什么?王老師帶去了中國古代象征公平正義的獬豸(獨角獸)雕塑,鄭重地回答:“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這正是他堅持立足中國實際,從文化層面思考法治建設,深入研究、執著追求,努力推進中國法治事業的寫照。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全面依法治國高度重視、統籌推進。我去探望王老師時,曾向他報告這些新變化,他聽后非常激動,眼睛濕潤。看到自己念茲在茲的法治理想正在實現,這位深具家國情懷的老人無比興奮。
在依法治國理論創新和市場經濟法治構想之外,人權研究亦是王老師的重要研究領域。
改革開放初期,人權研究在我國一度被視為理論禁區。和王老師共同主編第一部中國人權百科全書的劉海年老師,曾回憶當時的情況:“人權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口號”“思想理論界不愿碰人權這個敏感的詞匯”。但王老師以堅定的人民立場、深厚的學術素養和創新的理論勇氣,一直努力推動人權的開拓性研究。1991年,他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性人權研討會;1992年,牽頭成立中國社科院人權研究中心;1998年,主編第一部中國人權百科全書。他多次帶團考察代表性國家的人權制度及其面臨的問題,為推動人權理論研究、更好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事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今天,我們堅持把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已經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王老師當年領導的團隊篳路藍縷的開拓性研究功不可沒。
回望改革開放歷程,王老師對中國法學繁榮和法治進步做出巨大貢獻。他開辟的學術道路為后人奠定了基礎,他提出的學術思想影響了一代代后輩學人。
潤物細無聲,桃李共葳蕤
王老師令人愛戴和敬仰的不僅在于學問,更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他寬容謙和、淡泊名利,有君子之風,被法學界同行形容為“溫潤如玉”。王老師曾對我說:“國家、社會給我的太多了,我做的只是一個學者的本分。”
我曾協助王老師組織法學學科調研、擬定國家社科基金年度課題指南,參與者很多是他的晚輩。當時已是古稀之年的王老師,廣泛吸納建議,充分聽取意見,既堅持原則立場又不失靈活變通,定分止爭又讓同仁心平氣和,他的嚴謹、寬容、儒雅讓人如沐春風。

2007年,王家福與作者在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合影。
王老師桃李滿天下,學生中既有大法官也有大律師,既有法學大師也有學界新銳。無論是否曾授業于王老師,都交口稱贊他的道德文章及對后輩的提攜與關懷。
引進、推薦優秀法學學者,關心他們的工作生活,對年輕才俊獎掖提攜……王老師懷著惜才愛才之心,厚植對晚輩后學的殷切期望之情。他曾寄語年輕學者要潛心讀書、刻苦研究,甘坐冷板凳;要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做真正的學者;要關心改革開放實踐、社會進步和老百姓的福祉。話短情長,微言大義。我當時耳濡目染,身在福中而不知,獲益匪淺反不覺。
學莫便乎近其人。王老師親自引導我走上依法治國研究之路,還抽空作序推薦我的著作,告訴我好文章要有好的架構,要反復推敲修改,手把手指導我刪改文章。2007年,他鼓勵并指導我撰文,圍繞依法治國方略實施開展研究,建議組建依法治國領導小組,總結法治建設基本經驗,對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進行總體部署與規劃;2008年紀念改革開放30年之際,王老師再次指導我撰文,深入論證依法治國領導小組的建立和依法治國實施綱要的制定。所有這些,既是對依法治國研究的執著追求,也是對后學晚輩的栽培與期許。
那時,我經常到王老師家中求教。師母總是端出上好熱茶,并不斷續杯,我每次告辭時都戀戀不舍。2009年,我被組織選拔赴江西工作,王老師和師母在中日友好飯店專程為我設宴餞行,小坐敘談。當時兩位老人均年近八旬,拳拳憐愛之意令我至今感懷。
離開法學所后,我一直想念著二老,經常去看望。有了些成果,送去給王老師瞧瞧;有了點成績,和他說說;有了些進步,和他嘮嘮。王老師和師母多是聽我說,偶爾插上一兩句話……歲月在不知不覺間給我們帶來許多改變,但我每次去,王老師總是用他的方式表示“我在聽著呢,你接著說”。現在的我總想著,如果時間可以停駐,王老師能一如從前,多好!
古人云:“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堅忍不拔之志。”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尊重和保障人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普遍要求。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在更高水平上推進人權事業和法治進步,需要跑馬拉松般的定力和韌勁,需要衣缽傳承數代學人“接著講”,需要火炬接力般一茬接著一茬干。王老師深厚的家國情懷、堅定的人民立場、不變的法治初心、深邃的學術思想和高超的政治智慧,都令人心馳神往,更讓我們堅定地沿著他追求的法治夢想和道路破浪前行!
謹以此文祝福王老師和師母健康長壽!
王家福
1931年生于四川南充。著名法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終身研究員。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委員、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2018年入選改革開放杰出貢獻百人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