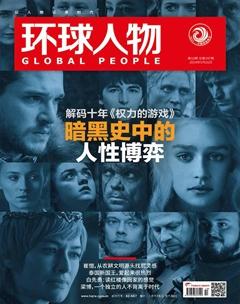葉錦添,無問西東
王晶晶

2019年4月23日,葉錦添在北京今日美術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本刊記者侯欣穎 / 攝)
葉錦添的新展設在北京著名的藝術地標今日美術館。展覽出口處偌大的白墻上,有矯若游龍的幾行書法,寫的是葉錦添在國內舉辦過的那些藝術展的名字。字有大有小,墨或濃或淡,名字看似散亂,卻被一筆重重的、沒有封口的墨圈攏聚起來,像是逐個走過葉錦添不同的藝術階段后,又回到同一片地方,落下不同的一個點。
對葉錦添來說,新展的確帶有這樣的意思。12年前,他第一次在內地辦個展“寂靜·幻象”,就是在今日美術館。按照中國傳統,12年是一個生肖輪回。時間和空間,兜兜轉轉,仿佛給葉錦添畫了一個圓,似乎沒變,又似乎完全不同。“我覺得很奇妙。經歷過很多不同的展覽,我開始去了解人與時間、空間的關系。它們對人本身到底有什么樣的影響?”葉錦添輕聲細語地說道。
成名于大眾影視領域的他,是唯一獲得過奧斯卡最佳藝術指導的華人藝術家。從吳宇森的《英雄本色》到李安的《臥虎藏龍》,從李少紅的《大明宮詞》到丁黑的《那年花開月正圓》,葉錦添與不同的合作者都有極好的碰撞,留下一部部膾炙人口的經典,影響力巨大。但他其實并不屬于那種容易被大眾所理解的藝術家。回答問題時,他的思維跳躍很快,言辭如同迷宮,需要聽者全神貫注地跟隨,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理解他的所思所想。“他其實有點像哲學家”,多年前,與他合作過的現代舞大師阿庫·漢姆就如此評價。
發現了這個世界神秘的一面
一條長長的甬道,黑黑的幔布高掛兩側,從屋頂綿延至腳下,甬道兩邊的地上各放著一排“蠟燭”,雖然不見真火,卻也用特殊材質做出了燭光搖曳的效果。就是這樣一條儀式感很強的甬道,把觀眾引入葉錦添的新展——“全觀”。“全觀”的英文展名叫“Mirror”(鏡子),象征著葉錦添要佇立回望,觀看自身與世界。
整個展占據了三層樓,一層由《精神DNA》《大腦》《反物質》《懸浮城市》等作品構成;二層主要是葉錦添設計的服裝;三層則是他這么多年持續創作的“Lili”——一個狀態不斷變化的人體模型,這一次則化身為孕婦和人工智能機器人。
這個展,是葉錦添首次跨界科學與藝術,“我其實從小就喜歡科幻,對外星文化之類的東西很有興趣,因為我喜歡想象。”葉錦添對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雷德利·斯科特的《銀翼殺手》、呂克·貝松的《第五元素》等科幻電影印象極其深刻。“20世紀是科技與想象力交錯在一起的時代,想象力受科技的沖擊而產生前進的力量。”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
因為舉辦這個展覽,葉錦添走訪了中科院基因組研究所、動物所和一些國家重點實驗室。他多次與中國科學院基因學家于軍交談,“我們談了非常多的東西,談到最后,我發現,科學跟藝術的確很不一樣。因為科學是要證據的,不允許任何想象,但藝術上全都是想象,而且沒辦法提供證據。那么,這兩者怎么融合在一起呢?我后來就看了非常多的科學資料,里面有很多漂亮的DNA圖像。”

葉錦添設計過的戲服,亮相于他在今日美術館舉辦的個展“全觀”上。

葉錦添的藝術作品《懸浮城市》。(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葉錦添的藝術作品《孕婦Lili和機器人Lili》。
看久了之后,葉錦添突然感覺,顯微鏡下的DNA,好像有一層東西是看不見的。“我就跟于軍提出這個看法,然后他問我,那你看到了什么?我說應該還有一層是‘精神DNA 。世間萬物,生長運動都是有規律的,一定有一個精神性的東西在推動著所有,就像人們總被情緒牽動著。我們看到了一個單細胞,其實(從這個單細胞身上)還長出了另外一個看不見的單細胞。這就是精神DNA,它藏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
發現精神DNA的過程,葉錦添說如同發現了這個世界神秘的一面,“我好像窺探到某種正常范圍以外的東西在左右著世界的變化”。
而Lili的創作,則是他對虛渺與真實、空間與時間的持續思考。
2013年,在個展“夢·渡·間”上,Lili正式亮相——形象上是個年輕女孩,裝有關節,可以調整坐姿、站姿。Lili脫胎于葉錦添的一件裝置雕塑作品《原欲》,眼睛處是空洞,配合水的使用,可以流淚。葉錦添曾說:“方力鈞、岳敏君(都是當代藝術家)作品里的人物,都是有所指的,有固定的社會性、歷史性,是某種圖騰,有自己的故事……《原欲》卻是無定的,她的內涵是空,你可以把自己投射在她身上。”
葉錦添把Lili帶到世界各地,打扮得和當地人別無二致,再拍下“她”在各種場合的影像以及別人對她的反應。
“有很多人問過Lili對我來講到底是什么?我覺得她是一個我擺出來的空間。在那里,我永遠不需要擔心時間的問題,因為她永遠都是17歲,她的時間是停下來的。你可以把她跟我們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隨意貼合在一起。她好像一個黑洞,把周圍人的時間都吸收到一個虛無里面去。”
“只要你足夠瘋,就可以找回一個時代”
葉錦添的好友、“全觀”的策展人馬克·霍本是這樣評價他的,“他對世界有著不同層面的思考:一個層面是作為設計師,他有獨特的能力可以做出令人感到驚艷的設計;另一個層面是作為藝術家,他擁有對未來世界強大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以及對于精微世界中不同層面的考慮”。多年前,作為設計師的葉錦添,就是用他在電影中的獨特審美驚艷了世界。
1986年,因為在香港繪畫比賽上拿到的獎項,葉錦添被徐克看中,在其引薦下作為《英雄本色》的執行美術,闖入了電影圈。他本來是學攝影的,最初常常以多重身份穿梭在劇組,做美術的同時,也在報上開攝影專欄,一度還想以攝影為業。
是關錦鵬的《胭脂扣》把他拉進了古典世界。在這部戲里,他費盡心思尋找過去的花露水和香煙廣告,打造屬于那個年代的妝容、空間,并且明白了一個道理:“只要你足夠瘋,把所有細節都弄對了,就可以找回一個時代。”等影片拍完,葉錦添已經深深迷上了這種重塑時空的藝術。
他習慣先“考古”,再想象,讓作品在歷史與現實間流動。
1999年,葉錦添接下《臥虎藏龍》的藝術指導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找來一張老北京的地圖,了解整個故事發生的背景和地理位置。影片設定的朝代是清朝,在葉錦添看來,“清朝的顏色系統是‘炸裂的,很艷、很俗。”但他想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將清朝服飾中最常用的青花瓷元素、建筑中的紅柱子元素全部拿走,走清淡、素雅的路線。
導演李安給人物造型的要求是“不要復雜”,但是簡單不意味著不麻煩。給楊紫瓊飾演的“俞秀蓮”定妝,一個發型就花掉近20個小時。楊紫瓊坐在那里,只覺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自己在鏡子里的發型好像沒任何變化,其實葉錦添一直在給她調整發髻——盤了拆、拆了再盤,只為找到那個最符合她沉穩、隱忍和俠女擔當的造型。楊紫瓊熬不住了,叫李安來做決定。李安一進工作間就說:“好漂亮!好漂亮!”楊紫瓊松了口氣,想這次終于可以定造型了。誰知道換第二個造型再叫李安來,他還是說:“好漂亮!好漂亮!”
憑借《臥虎藏龍》拿下奧斯卡最佳藝術指導后,葉錦添的電影邀約越來越多。2008年,吳宇森找他合作《赤壁》,6億的投資,是當時影史上最貴的華語片。據說葉錦添花掉了其中的1億——他和美術班底在籌備初期就開始搜集數據,每天和不同領域的專家交流,像考古研究人員一般,從家具、建筑、兵器、服裝、船等各個方面還原東漢末年的場景。葉錦添還跑去日本,向三國史專家請教。在日文研究資料中,他發現了很多細節,比如鎧甲甲片的縫制、徽號的分野、古兵器的制造等。
在所有參與過的影視劇中,葉錦添設計服裝數量最多的是馮小剛的《一九四二》,難民服、軍裝加起來有1萬多套。他研究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剪裁,細心到連紐扣的位置都要考證一番。過去的軍用棉如今已很少見,葉錦添到處都買不到,最后只能把幾種棉料合在一起做。

1987年,葉錦添在電影《胭脂扣》劇組拍攝的照片。

電影《臥虎藏龍》劇照。
找到和人家不一樣的東西
近年來,葉錦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舞臺劇、跨界藝術上。他本來就是個跨越東西、不愿意限制自我的人。
葉錦添生于香港,從小接受到的文化就是跨越東方和西方的。他對傳統藝術的研究,開始于中學畢業后的一段時期。“那時候的香港,對傳統的理解幾乎是空白的,傳統只是陳舊與死板的代名詞。外國文化才是主流,人們都向往西方,遠離自身文化。”
葉錦添希望找到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在朋友的建議下,他背起行囊,浪跡歐洲,在盧浮宮、在文藝復興的繪畫中,感受東方與西方的藝術。
回香港后,正是香港電影工業的起飛年代,葉錦添將自己投入到這個洶涌的浪潮中。因為電影《誘僧》(1993年),他結緣當代傳奇劇場的創始人吳興國,受邀去臺灣參與創作年度大戲《樓蘭女》。“我當時有很多超現實的想法,在香港那種商業社會,這些想法都實現不了。接到吳興國邀請之后,我提著一個皮箱,帶著一臺縫紉機就去了臺灣”,葉錦添后來回憶。
《樓蘭女》根據希臘悲劇神話《美狄亞》改編,講述了一個復仇故事。葉錦添用夸張的西方剪裁,拼合各個國家各個時代的造型特色——文藝復興時期帶骨架的大裙子、中國式的大袖子、藏民造型的張揚濃烈、大洋洲的圖騰拼貼……超現實的設計完全顛覆了當時大家對舞臺服裝的認知。一經演出,《樓蘭女》就引起了轟動。云門舞集的創始人林懷民說這樣的舞臺設計“從來沒有過”。主角魏海敏上場,每次都得適應一段時間服裝才不至于跌倒。有人建議她換個戲服式樣,但她堅決不肯。
那時的臺灣文化界,正是個群星璀璨的時期。云門舞集、當代傳奇劇場、漢唐樂府、優劇場(優人神鼓)等,都是葉錦添的合作對象。1996年,林懷民邀請葉錦添赴奧地利,為格拉茲歌劇院秋季大戲《羅生門》設計服裝道具。這是葉錦添第一次把自己的藝術推向國際。舞臺設計師是美籍華人李名覺,作曲是旅德日本作曲家久保摩耶子。如何讓西方歌劇演員的表演融入東方戲劇的質感,葉錦添一直在思索。他整理、研究日本各種古典服裝,想盡辦法把歌劇演員高大的身材隱藏起來,一方面把服裝細節簡化,一方面把色彩凈化到極致。《羅生門》的成功,讓葉錦添在西方藝術世界打出了名號。
憑借《臥虎藏龍》拿下奧斯卡最佳藝術指導后,葉錦添在西方的名頭更加響亮了。他提出了“新東方主義”的概念,游走于舞臺藝術、電影美術、當代藝術創作之間,將現代嫁接于傳統,又由傳統演繹出時尚。
他曾說過,自己并不是刻意在做東方的東西。“我很討厭主義。提出‘新東方主義,也有重建的意思,洗牌重來,重新定下游戲規則……中國元素和西方現代在我的作品中是沒有沖突的。”
多年前,葉錦添在自己的美學著作《神思陌路》里寫道:“當我接觸藝術,才知道它處于一種無界定的狀態,就好像沒有人可以為它作出人間的定義。直到今天,藝術的定義無法涵蓋一切、透徹表達,可能文字也不夠用。”葉錦添的藝術,也是這樣。
葉錦添
1967年出生于香港,畢業于香港理工學院高級攝影專業。從1986年參與第一部電影《英雄本色》起,游走于電影美術、服裝設計、藝術創作等多個領域。曾憑借電影《臥虎藏龍》獲得奧斯卡最佳藝術指導,是唯一獲此殊榮的華人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