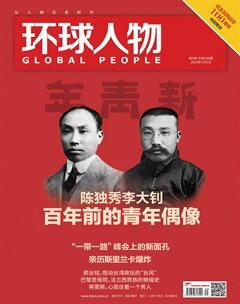茶中覓詩吳德亮

徐學
2012年6月,在距臺灣68海里的福建第一大島——海壇島,我策劃的兩岸跨界詩會如期開幕。其中,吳德亮作為臺灣全方位藝術(shù)家聯(lián)盟負責人出席,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這位寫過三十幾本書、辦過個人畫展、當過大刊主編的學者長得像個農(nóng)夫,身材健碩敦實,面色褐黑中透出紅潤,戴一頂寬邊帆布帽,一派天真,笑聲不斷。
飲茶賦詩
詩會那天,高談闊論、酒酣耳熱之后,德亮招呼我們到他房間,拿出他的紅印普洱茶款待我們。他溫盞后注入沸水,深褐色茶湯如泉涌般溶出。首泡湯色褐紅,不同于那些立即散發(fā)醇厚香氣的茶品,紅印普洱只有淡淡的木質(zhì)香若隱若現(xiàn),茶入口略黏稠,圓潤恬淡而微甘。第二泡湯色明顯黝黑,茶面則泛起陳茶特有的層層油光。幾泡茶湯飲盡,入口時乍現(xiàn)的老陳檀木香逐漸明朗,醇厚陳韻在喉間回蕩,杯底茶香濃郁,一股熱氣自丹田直沖腦門,蔓延至臉頰耳根,手掌泛紅微熱。
德亮一邊沖泡,一邊品嘗,一邊侃侃而談,說起他在烈日風霜中如何艱難輾轉(zhuǎn),有一茶未見之識之飲便不罷休。他在茶氣氤氳中談茶事,讓我們卻俗忘塵,一杯續(xù)一杯,頓感茶逢知己亦是千杯少。
當晚,我有感而發(fā),寫了首詩:“迷離七竅,云霧氤氳的遠山/皴染唇舌,驟雨初歇的芬芳/醇厚入喉,如登云海鼓動陽剛滿腔/澀后回甘,悲欣苦中藏/杯雖小,長長光陰滿滿流淌/一把壺,誰說它不是道場。”作家亮軒更是豪興大發(fā),當場潑墨揮毫,寫了首茶詩,詩曰:“極品產(chǎn)自靈猴,盧仝詩出茶樓。凍頂乘槎渡海,武夷噴雪浮甌。普洱騾車待發(fā),屯溪舟楫暢流。妙手人稱博士,名實傲視王侯。”德亮歡喜異常,后將亮軒的詩裱起,掛在他工作室最醒目的墻壁上。
客家之子
之前,和余光中先生喝茶時,我還不認識德亮,就聽先生提到德亮的詩和畫。德亮曾邀余光中夫婦去他的小屋里喝茶,先生對德亮寫作、待客的小屋——“阿亮工房”贊不絕口。后來,我再到臺北,若想喝茶,就舍去茶道師周渝的紫藤廬,直奔臺北教育大學對面的臥龍街,上午10點以后,大半可以在“阿亮工房”里找到德亮。這里是他品茗、寫詩、作文、畫畫的筑夢空間。屋不大,滿墻的油畫,滿桌的民俗工藝品,還有很多詩畫集。墻上的客家土樓油畫和梯田照片,追溯的是他的客家原鄉(xiāng)。

吳德亮和他的故鄉(xiāng)臺灣花東縱谷。

吳德亮的“阿亮工房”,桌上擺著茶罐、民俗工藝品,墻上掛滿了油畫。
“阿亮工房”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制作的頗具后現(xiàn)代風格的藝術(shù)品:桌上的彩繪貓咪陶茶盤,以砧板雕刻而成的鐘馗,用茶票紙寫的書法,以普洱茶汁染成的圖畫……德亮說:“很多人知道我用砧板作畫,就將廢棄的砧板、洗衣板、不要的木頭和椅子送過來。”他又指著茶幾旁一張刻有彩繪舢舨的長板凳說:“這是被遺棄的板凳,我以漆料雕繪成船,坐上去的感覺就好像在海上。”長板凳旁邊還掛著件白族女裝,他在衣領(lǐng)開口處嵌入木片,還題了詩:“解開傳統(tǒng)的束縛,需要五千年的勇氣。”他的書法亦不求規(guī)范,跡近隸而隨心賦形,勾、挑、撇、捺、折皆夸張破格,血氣充盈。
德亮的多血、活力來自故鄉(xiāng)——云霧繚繞的花東縱谷。在那里,前邊是最潔凈碧藍的太平洋;后邊有海拔3000米的玉山山脈;山上住著阿美族和平埔族;山下有客家小村星星點點;山坡上梯田里稻穗搖曳……巍峨與浩瀚中,五彩繽紛的花木,淳樸多元的民風,德亮耳濡目染。故鄉(xiāng)厚植了他的藝術(shù)根基。
德亮一家是從臺灣北部苗栗縣遷到花蓮縣的客家人。花蓮客家人自有耕讀傳統(tǒng)。“作一等人忠臣孝子,只兩件事讀書耕田”,這是他們門上的對聯(lián),也是家族的規(guī)訓。臺灣教育界都知道,花蓮客家的“特產(chǎn)”是中小學校長,單是鳳林一鎮(zhèn),60年來就有95人當了校長。
我和德亮相聚,他總會提起他的父親,一位注重課外教育的鄉(xiāng)村校長,也是德亮攝影、寫作、繪畫的啟蒙老師。德亮至今珍藏著他的第一臺相機——一臺單鏡頭手動照相機,這是父親花了3個月薪水為他買下的。
年輕時,德亮對詩歌創(chuàng)作非常投入,先后結(jié)識了王禎和、胡品清和痖弦等名家。胡品清介紹他讀法國詩歌,告訴他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的一句話——“人生還不如波德萊爾的一行詩”;痖弦曾說:“一日為詩人,終身為詩人。”這兩句話德亮終身不忘。高中時因為忙著寫詩文、結(jié)詩社、編校刊,大學聯(lián)考時他幾度落榜,但也有意外收獲。正是因為深知聯(lián)考壓力下學生之痛,他寫了首敘事長詩《國四英雄傳》。這首詩獲得“時報文學獎”,后被改編成電影,由吳念真執(zhí)導(dǎo)。古詩云,國家不幸詩家幸,這件軼事或許可以說是學生不幸影視幸吧。
清貧藝路
有一年,我得到一本《德亮詩選》,讀后覺得德亮寫亡妻的詩尤為動人。在《六西病房》一詩中,德亮寫自己一手拭淚,一手握亡妻的手,竟嫉妒起病房里一位看護男子,因為他可以與癱瘓的妻子長相守。《晚餐》一詩寫到只剩一人的房間:“準時回家/與妻共進晚餐,聊天說笑/……我繼續(xù)說著笑話/只有不小心/滴落的淚水,在泡面浮腫的保麗龍碗內(nèi)/微弱地映出/妻的遺照。”欲重溫往日幸福,被淚點破,突然定格,落在墻頭的遺照。
中國人的境界本來就不在書齋,他們仰觀天象、俯觀地法得以品味哲學,他們從白鶴騰空、瀑布斷流中悟出武學境界,他們以四時佳興、草木榮枯建立美感……
當然,德亮還寫了很多更具特色的詠茶詩。《水鄉(xiāng)茶樓》《鷺鷥環(huán)抱的八卦茶園》《茶馬古道上的馬幫》《金瓜貢茶》都是杰作,里面不僅有茶,還可以看到美景和古跡、風俗和信仰,看到山、人和茶的相得益彰。
1997年,德亮愛妻病逝,他本想以旅游攝影療傷,最終卻迷上茶事。為寫好普洱茶,他跋涉3年,從臺北經(jīng)香港或澳門至昆明,前后飛了十數(shù)次,再加上從昆明前往思茅、西雙版納、紅河、麗江、大理等地的距離,還有深入偏遠山區(qū)步行、騎馬、乘舟的路程,總行程少說也有8萬里。他曾扭傷、摔傷,也幾次路遇洶涌的泥石流,險象環(huán)生。
他尋茶時也受到不少誤解,每次過海關(guān),海關(guān)關(guān)員都用懷疑的眼光看著他:那么一大包膠卷,是要長途販賣嗎?還有一次,一個村子的干部把德亮扣留了,他們憤憤不平:這個臺灣客專門來看我們這陳茶干嘛?我們現(xiàn)在都喝立頓紅茶了,他是來揭我們瘡疤的吧!后來,他求助了國務(wù)院臺灣事務(wù)辦公室,才得以被放行。
德亮自追詩攝影而入茶,又在尋茶觀物中不斷寫詩作畫,用心專注,自成一家。尋幽探奇產(chǎn)生了生動的詩文,描寫他走過的八萬里路云和月,配以百張精美照片,烘托出中國邊陲的韻味風采。
十年間,他一發(fā)不可收地出版了很多寫茶的書。他追求寫出平實又有人物和故事的書,他要在找茶喝茶里培養(yǎng)出人們對萬事萬物的美感和品位,讓我們對生活更好奇更感激。在我看來,他的書最為人稱道的,是在專業(yè)茶史之外對茶人茶事充滿人文氣息的入微觀察,和對生態(tài)環(huán)保的思考。

吳德亮的書《德亮詩選》和《找茶,就是找故事》。
德亮寫了許多詩許多書,卻依然買不起臺北城區(qū)的一間工作室,但他并不在乎。一縷茶香把他引進千古風流,一張茶票讓他窺見百年滄桑。中國人的境界本來就不在書齋,他們仰觀天象、俯觀地法得以品味哲學,他們從白鶴騰空、瀑布斷流中悟出武學境界,他們以四時佳興、草木榮枯建立美感……在我看來,茶學也是一種詩學,一種美學。與自然萬物相傍者天下滔滔,誰能成為一個得物趣、通物情、能友物、能契物的人呢?
從商的友人見到德亮,曾憤憤不平地說:“唉呀,你這十多年來為人作嫁,自己得到了什么?”弄文的前輩也對他專心寫茶大表惋惜:“讀者會把你這位詩人忘記啦!”德亮對此一笑置之,依舊以畫家之眼、詩人之筆、惜物之心寫其所想。他不會忘記浩瀚與巍峨之間孕育的少年夢想;不會忘記愛妻臨終時的囑托,“你要好好創(chuàng)作”;更不會忘記父親的話,“沒有愛就沒有藝術(shù)”。
2016年,我們在福州舉辦了第三屆兩岸詩會,主題是“兩岸客家詩歌”,為這個詩會,我主編了一本《桐花客韻——海峽兩岸客家詩選》,收入29位兩岸客家詩人的詩歌,其中就有德亮的詩歌,依舊是茶事,依舊是客家。他依舊在這條清貧而莊嚴的藝術(shù)之路上行走,就像多年前花東山谷里那個歡歡喜喜的孩子,走在歡歡喜喜的陽光里,覺得世間萬物都和自己有親有故。
徐學,生于廣州,長在閩西南,1977年入廈門大學,獲文學碩士后留校,專攻臺灣文學。30年間問學島內(nèi),深交名家,曾任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著述20余種,獲文學獎若干。吳德亮,生于1952年,臺灣花蓮縣人,知名茶文化學者、詩人、畫家,曾出版《德亮詩選》《臺灣找茶》《找茶,就是找故事》等。
吳德亮
生于1952年,臺灣花蓮縣人,知名茶文化學者、詩人、畫家,曾出版《德亮詩選》《臺灣找茶》《找茶,就是找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