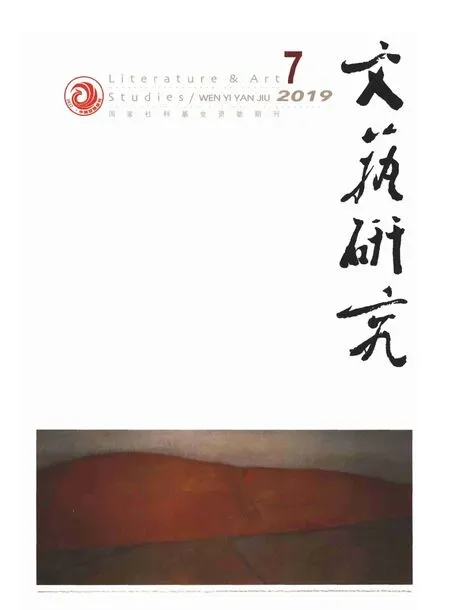秦腔史研究的理念、視野與態度
——高益榮《20世紀秦腔史》缺憾剖析
郭富平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戲曲研究的全面推進,劇種史寫作成了一種學術熱潮并涌現出一系列豐碩成果①。就秦腔史研究而言,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雖然出現了焦文彬主編的《秦腔史稿》等五六部專著②,但總體來看還相當薄弱,與秦腔在中國戲曲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稱。20世紀是中國傳統戲曲的生存環境、觀演方式、傳播途徑等發生巨變的重要轉型時期。對于秦腔來說,自然也不例外。在秦腔面臨嚴重生存危機的今天,全面梳理20世紀秦腔的演進軌跡與發展脈絡,總結其利弊得失,不僅具有推進學術研究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促進秦腔傳承與保護的實踐意義。在此背景下,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高益榮教授的《20世紀秦腔史》(下文簡稱“高著”)③,作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結項成果得以面世④,確實令人振奮。這是第一部秦腔斷代史,同時也是第一部專論20世紀秦腔的理論著作,在秦腔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⑤。然而展讀之后,不得不說,這部意在“具有總結意義”,“為振興秦腔做點實際的工作”(第1頁)的秦腔史著作存在著諸多缺憾,而且相當一部分缺憾為當前的秦腔史研究與寫作所共有。因此,本著推進相關研究的建設性態度,筆者擬不揣淺陋對其缺憾進行一番剖析。
一、編寫理念的混亂與研究視角的游離
戲曲是一種涵納了文學、音樂、舞蹈、美術等多種藝術樣式的綜合性表演藝術。基于其綜合性特點,戲曲史的寫法也多種多樣。相對來說,以劇本和劇作家為核心的戲曲文學史最為常見。即便戲曲史呈現出“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特點,但就一部具體的戲曲史著作而言,無論選擇哪一種寫法,都應該有明確的寫作理念,且應將之貫穿于寫作實踐始終,否則,會有邏輯混亂、思路不清之弊。高著的一大缺憾恰恰在于編寫理念的混亂以及由此導致的研究視角的游離,這使得20世紀秦腔的演進脈絡隱而不顯。
關于編寫理念,高著有兩處較為明確的表述:
眾所周知,戲曲屬于綜合藝術,但劇本創作與演員表演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大要素,直接決定著戲曲藝術水平的高低,故在梳理20世紀繁雜豐富的秦腔歷史時……以“劇作家的劇本”和“表演者演員”作為兩個中心來結構全書,力圖在有限的篇幅內既全備⑥、全面,又富有代表性地勾勒出20世紀秦腔發展的歷史。(第24—25頁)
此處,著者確認劇本創作與演員表演為戲曲“最重要的兩大要素”,進而將“劇作家的劇本”和“表演者演員”作為結構全書的兩大樞紐。這一編寫理念在“后記”中得以重申與強調:“主要從最關鍵的因素即‘劇作家’和‘名角’入手……勾勒出秦腔發展的脈絡。”(第379頁)暫且不論僅以劇本和演員為中心能否支撐起一部戲曲史,問題的關鍵在于,高著還存在與此齟齬不合的另一種編寫理念:“在20世紀上半葉的表述里以易俗社為重點,下半葉以陜西戲曲研究院為重點。”(第379頁)顯而易見,著者在確立了以劇本和演員為核心的寫作理念的同時,又特別強調了戲曲班社之于戲曲史的重要意義,并將易俗社和陜西戲曲研究院分別作為20世紀上、下半葉秦腔歷史敘述的重點。如此一來,問題隨之產生:關于20世紀秦腔的歷史敘述究竟是以劇本和演員為中心,還是以班社為中心?高著的研究視角到底是什么?若以劇本為中心,則更接近于“20世紀秦腔文學史”;若以演員為中心,則更接近于“20世紀秦腔演出史”;若以班社為中心,則更接近于“20世紀秦腔班社史”。可見,高著的編寫理念是混亂的。
編寫理念的混亂必然導致研究視角的游離,而研究視角的游離難免會引發敘述話語的內在沖突。在整體結構上,高著的內容大致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秦腔概說”屬于提綱挈領性質的概論,是為第一部分;第二章“20世紀最有影響的秦腔班社——易俗社”、第三章“其他有影響的秦腔班社”以及第四章“陜甘寧邊區時期的新秦腔”集中探討20世紀上半葉的秦腔歷史,構成第二部分;第五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至‘文革’時期的秦腔:秦腔的改革與繁榮期”、第六章“‘文革’十年的秦腔:艱難的堅守”、第七章“新時期的秦腔藝術:在輝煌與困頓中前進”重在梳理20世紀下半葉的秦腔歷史,構成第三部分。因為“20世紀秦腔史”這一論題的限定,高著的著力點顯然在后兩個部分。從具體的章節安排與話題設置來看,第二部分主要以易俗社為中心,側重研究20世紀上半葉秦腔的主要班社,兼及這一時段的重要劇作家與演員,而第三部分主要通過對重要事件、主要劇社、著名演員及劇作家等綜合因素的勾勒呈現20世紀下半葉的秦腔歷史。綜而觀之,不難看出,作為高著主體構成的后兩部分,研究視角各不相同,因此敘述內容各有側重、敘述體例迥然有別。或者說,此兩部分分屬兩種不同的寫法、兩套不同的筆墨,這致使兩者處于互不相干的割裂狀態,從而嚴重損害了一部秦腔史本應具有的完整性與統一性。因此,這部“20世紀秦腔史”實為20世紀上半葉秦腔班社論與20世紀下半葉秦腔史的雜糅與拼湊。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包括秦腔史在內的戲曲史的寫作應包含哪些核心要素并應堅持怎樣的原則?雖然在以批判性、消解性和顛覆性為鮮明特征的新歷史主義看來,歷史不過是一種敘述,不同的敘述者可采取不同的敘述視角,特定視角之外的一些史實可以棄置不顧。然而,基于戲曲的綜合性特點,戲曲史的寫作無論如何不能隨意刪減其基本“構件”——聲腔、劇本、演員、舞美、班社等戲曲的核心要素,否則就無法成其為自身。就此來看,僅以劇作家、名角、劇社為主要視點的高著因過度瘦身而顯得營養不良。除此之外,戲曲史作為“史”,必然是一種歷時性敘述,在體現歷史連續性的同時凸顯重要的歷史節點,強調此節點與彼節點之間或承續或斷裂的關系應是一種基本原則與常規做法,否則,會有線索不明、重點模糊之弊。但是高著并未將20世紀秦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進與嬗變作為研究重點,而“執著”于對20世紀秦腔班社和秦腔劇作家進行靜態考察,其結果是未能呈現出一個較為清晰的關于20世紀秦腔的歷史發展脈絡。
二、學術視野的褊狹與問題意識的欠缺
學術視野的廣闊與否直接關系到學術質量的高低。只有將特定的研究對象置于廣闊的學術視野中進行考察,其價值與意義才能得到準確定位,所形成的觀點也才能經得起推敲,此即學術研究中“小題大做”的內涵之一。然而,高著的學術視野不僅談不上廣闊,而且顯得異常褊狹,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嚴重的地域偏見是高著學術視野褊狹的最突出表現,它首先體現為對“秦腔”這一研究對象所涉地域范圍的界定。眾所周知,秦腔作為西北地區的第一大劇種,廣布于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省區,其流播范圍遠達山西、四川、河南、內蒙古、西藏等地。因此,從研究對象的外延來講,一部力圖總覽20世紀秦腔發展軌跡與整體風貌的著作,立足秦腔的流行區域、放眼秦腔的傳播范圍似乎是題中應有之義。然而通覽高著,除了第一章第四節“秦腔的流派與傳播”對秦腔在甘肅、新疆等地的傳播有所涉及外,其他各章始終以陜西秦腔作為唯一的研究對象,而將陜西之外的秦腔完全排除出局。固然,從經典劇目、演員陣容、社會影響等多個方面來說,陜西當屬20世紀秦腔的龍頭與翹楚,但秦腔流行于整個西北地區而不局限于陜西卻也是不容爭辯的客觀事實。即使單就陜西秦腔而言,也絕非鐵板一塊式的封閉性存在,而是始終處于與西北其他各省區秦腔的互動之中,無論劇目的創作與改編、演員的遷移與流動,還是唱腔技巧的互相影響、表演風格的彼此滲透等等,概莫能外。同時,秦腔在整個西北地區也并非整齊劃一的無差別存在,例如陜西派秦腔與甘肅派秦腔的劃分就是主要基于秦腔在不同地域審美風格與文化特征的差異。高著在20世紀秦腔研究中“以陜西代西北”的地域偏見客觀上會強化人們的一種錯誤印象:秦腔,顧名思義,就是起源并流行于以“秦”為特指的陜西省的一個地方劇種。秦腔是否天然姓“秦”?“秦”與陜西之間是否可以劃等號?從歷史視角審視,并非不證自明。概而言之,陜西之外的西北其他四省的秦腔是20世紀秦腔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任何抹煞其實際分布的秦腔史都是不可靠的。
不僅如此,高著的地域偏見也體現在對既有研究成果的參考與引證方面。通覽高著所列的68種“參考文獻”,直接關涉秦腔的研究論著與資料匯編約占八成之多。就著者或編者的所屬省份來看,其中除了《絲綢之路戲曲研究》出自新疆學者陸暉之外,其他陜西省外學者的論著均未收入。此外,在全書多達41萬字的篇幅中,陜西省外學者關于秦腔的學術觀點總共僅被引用了7次。就秦腔研究而言,諸如王正強主編的《秦腔詞典》等屬于必備的工具書之一⑦,可是此類書籍在高著的參考文獻中卻付之闕如,遑論參酌、引證。總之,高著抱有嚴重地域偏見的做法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其學術視野的褊狹。
學術視野的褊狹必然導致對一些基本史實棄置不顧,而任何類型的歷史書寫都必須建立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之上,沒有史實作為支撐的歷史書寫無異于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高著對秦腔流行區域的隨意刪減是對20世紀秦腔史史實的無視,更是對作為學術研究第一要義的求真精神的背離。就此而言,高著雖然名為“20世紀秦腔史”,但充其量只能稱得上是一部并不完善的“20世紀陜西秦腔史”。另外,在對秦腔研究現狀缺乏充分了解與全面省察的情況下,高著表現出對20世紀秦腔的學術誤判。
有必要特別指出的是,囿于褊狹的學術視野和地域偏見是當前地方文化研究中較為普遍的現象,在包括秦腔研究在內的地方戲曲研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就當前來講,專門從事秦腔研究的大多是一些地方學者,人數較少,主要集中于陜西、甘肅兩省。然而,無論是研究材料的占有還是研究方法的交流或者學術觀點的互動,陜、甘兩省的秦腔研究并沒有形成互通有無、相互促進的良好局面,基本上處于各自為陣、自說自話的境地,甚至在牽涉地域問題時不乏非學理化的“叫板”。例如,關于秦腔起源地的考辨本是一個嚴肅的學術話題,但陜西學者幾乎眾口一詞地將其認定為陜西,而甘肅學者又不約而同地將其認定為甘肅,并分別“落實”到一個具體區域。事實上,不論孰對孰錯,以現行的行政區劃來嚴格對應研究對象所涉之地域范圍,本身就是非學術或偽學術的做法,其實質與前幾年關于名人(包括神話人物、小說人物)故里論爭的鬧劇并無二致。可見,地域偏見已成為制約與阻礙地方戲曲研究進一步拓展與深入的重要因素之一。相比其他地方劇種的研究,秦腔研究的嚴重滯后與這種動機并非純正的地方保護主義不無關系。
與學術視野的褊狹緊密相關的是,高著整體上還存在問題意識欠缺的弊端,這影響了研究本應具有的深度。概括來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一些重要問題被遮蔽。作為一部論述20世紀秦腔發展史的學術著作,有些問題是無法回避而理應予以深入探討的,如20世紀秦腔是在怎樣的歷史語境中發展的?它與此前的秦腔存在著怎樣的承續與轉化關系?在20世紀中國戲曲發展的總體情境中,秦腔的歷史演進有何獨異之處?易俗社以“補助社會教育,移風易俗”⑧為宗旨的秦腔改良運動與戲曲高臺教化的傳統以及晚清以來的啟蒙思潮之間有何關系?20世紀50年代的“戲改”運動在秦腔界如何開展并應給予怎樣的評價?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市場化浪潮對秦腔的生存與發展產生了什么影響?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然而,這些問題在高著中要么被完全忽略,要么存而不論。
其次,抽離語境的非歷史化傾向。未將20世紀秦腔置于特定的歷史語境與中國戲曲發展的總體情境中加以考察,而將研究對象從具體時代割裂出來進行孤立的靜態化研究是高著的一大特點。試舉一例。馬健翎是高著著墨較多的秦腔劇作家之一(第222—241頁),他在20世紀50年代對《竇娥冤》等傳統劇的改編曾引起戲曲界的熱烈討論,這種討論與“戲改”運動不斷深入的特定時代背景密不可分,可謂“戲改”運動具體開展的典型案例之一。然而,高著對之采取的是一種漠視態度,遑論站在20世紀秦腔史的高度以一種反思性思維予以觀照。一部好的信史須瞻前顧后、左右開弓,也就是說,對于研究對象既要進行歷時性的縱向考察,又要進行共時性的橫向比較,唯有如此,才能對其予以準確定位。抽離語境實乃治史之大忌,其結果必然是歷史脈絡的含混不清與總體風貌的隱而不顯,所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最后,材料羅列與泛泛而談。高著中真正具有學術意義的話題較為鮮見,更多是諸如演員生平簡介、劇目故事梗概、社團發展歷程等常見資料的羅列,屬于學理性不強的低水平重復。即使對一些重要問題有所涉及,也大多是泛泛而談或淡化處理。例如,第二章單設“易俗社的文化精神透視”一節,其中的“文人化品位與民眾化情趣的關照”⑨(第32—33頁),本是一個饒有興味的話題,它牽涉到秦腔這一進入現代語境的地方戲曲如何適應新的生存環境以及作為民間文化形態的地方戲曲如何與精英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相契合等重要問題。然而高著在具體論述中卻淺嘗輒止,使得讀者對易俗社這一百年老社究竟如何調和“文人化品位”與“民眾化情趣”間的關系仍是一頭霧水。因為既少有新材料的發現,又缺乏對舊材料的新闡釋,在已有不少同類著作的背景下,高著明顯新意不多且學術含量不足。
在有序鋪排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運用反思性思維予以整體觀照,通過總結其間的利弊得失探尋其內在規律,應是歷史敘述的理想追求。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實現鑒古知今的目的。然而,因為問題意識的薄弱與欠缺,高著關于20世紀秦腔史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呈現史實、就事論事的淺表層次,若想從中獲取為當下秦腔發展可資借鑒的經驗不過是一種奢求。值得注意的是,問題意識的欠缺是秦腔研究中的一大通病,也是秦腔研究相對滯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中國戲曲研究已呈現出多種學科相互交叉、多重視域相互融合、多種方法綜合運用的整體性特點。然而,不少所謂的秦腔研究尚未上升至學理探討的層次,其成果大多表現為資料匯編、劇目賞析之類的材料羅列與感性描述,普遍存在著邏輯梳理和理性分析嚴重不足的缺陷。與表面化、淺層次、重復化的研究相一致的是,一些缺乏學理依據的觀點在眾多研究者中間陳陳相因,例如“秦腔乃百戲之祖”“秦腔是中國梆子戲之祖”“秦腔開創了戲曲音樂板腔體的先河”等等。當然,制約秦腔研究走向深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問題意識的欠缺之外,還與學術理念陳舊、學術視野褊狹、研究方法單一等緊密相關。
三、知識硬傷的頻現與治學態度的粗疏
客觀來說,要完全避免或徹底杜絕學術研究中的錯誤幾乎是不可能的。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講,這是由研究者作為個體,其學術生命的有限性決定的。然而,這種“同情之理解”不等于對學術研究中主觀臆斷與草率任性的認同。相反,秉承嚴謹態度、遵守學術規范、規避知識硬傷是研究者理應堅守的底線。試想,一部學術著作如果知識性錯誤層出不窮,無論其研究方法多么新穎、觀點多么有力,其學術價值究竟能有幾何?這樣來看,我們不無遺憾地發現,高著的知識硬傷并不鮮見。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史實層面的謬誤。
在有關20世紀秦腔史上一些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及重要劇目的相關敘述方面,高著存在著多處前后表述不一、名稱相互混淆、與歷史事實不符等錯誤。比如,第一部秦腔電影藝術片《火焰駒》的拍攝與公映是20世紀秦腔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全國有著廣泛而深入的影響。然而,高著對其拍攝時間竟有三種不同的表述:
1957年,他⑩參加了秦腔戲曲片《火焰駒》的拍攝工作,扮演王強?,將這位狐假虎威、邪惡兇殘的家奴塑造得入木三分。(第135頁)
1958年他?參加拍攝秦腔電影藝術片《火焰駒》,飾李彥榮。(第154頁)
1960年,以社長蘇育民為首的一批演職人員參加了秦腔戲曲片《火焰駒》的拍攝。(第148頁)
仔細查閱相關資料,即可明確如下事實:1957年10月,負責拍攝《火焰駒》秦腔電影藝術片的陜西省秦腔電影劇團成立;1957年11月,陜西省秦腔電影劇團赴長春電影制片廠開始拍攝;1958年4月28日拍攝完成?。
對20世紀30年代三意社因內部矛盾而發生分社風波的具體時間,高著也有著不同的說法:“1937年三意社發生分社風波”(第144頁)、“民國二十七年(1938)春,該社內部卻發生了一場糾紛”(第146—147頁)。綜合多種材料可知,其準確時間應為1938年春夏之交?。
關于易俗社發起人之一孫仁玉的生年,高著的表述是:“孫仁玉先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3)生于臨潼縣東北方渭河北岸古鎮雨金鎮孫家村的一個農民家庭。”(第54頁)首先,清同治十一年應為公元1872年而非1873年。其次,從《孫仁玉傳》等資料可以查證,孫仁玉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農歷五月二十五日?。與此相關的是,高著第二章第六節“易俗社早期的其他劇作家”中對胡文卿有如下介紹:“胡文卿(1887—?)……盡管他只比孫仁玉小三歲,但他對孫仁玉非常崇拜,兩人早有來往。”(第104頁)按其生年,二人年齡相差14歲之多,胡文卿怎能“只比孫仁玉小三歲”?
高著第二章第七節對易俗社早期的著名丑角演員蘇牖民有如下介紹:“列‘易俗六君子’之列,有‘酥麻糖’之美譽。”(第121頁)此說大謬不然。“酥麻糖”本是觀眾對20世紀20年代西安易俗社三大名丑蘇牖民、馬平民、湯滌俗的合稱,取三人姓氏諧音而成,并非單指蘇氏一人?。
除此之外,因疏于校對,高著中將人名、劇名寫錯,將新劇目的創作與傳統劇的改編混為一談等不勝枚舉,茲不贅述。
其二,論證層面的偏差。
在有關20世紀秦腔的論證與闡釋方面,高著存在著多處偏差,試舉例證之。第二章第七節在介紹易俗社早期著名演員、衰派名角劉毓中時,這樣界定“衰派”:“所謂‘衰派’即泛指處于‘衰微’‘衰敗’‘衰落’處境的白須,也可指時運不佳的黑髯人物,如《逃國》中的伍員、《殺惜》中的宋江等。”(第122—123頁)這種解釋有失準確。首先,“衰派”是著眼于表演風格而非劇中人物劃分出的戲曲行當名稱,屬于“老生”行。這類行當在舞臺表演上以做功為主,身段較多,且因為大多扮演年紀衰邁或生活窘迫的人物,所以也被稱為“衰派老生”?。其次,所舉例子不夠恰切,秦腔《逃國》中的伍員向來被視為典型的硬派須生應工,而非衰派老生應工。
第二章單列“魯迅易俗社看秦腔”一節,專門討論魯迅與易俗社以及秦腔的關系,其中數次引述孫伏園《魯迅和易俗社》一文。然而現已證實,因記憶不確,孫文關于魯迅在易俗社看戲的具體時間、次數以及主要演員的姓名等多處記述與事實不符,有學者著文加以糾正,以正視聽?。對此,高著未加辨析,仍照搬舊說,難免會產生以訛傳訛的負面效果。
其三,觀點層面的臆斷。
高著關于秦腔的起源地、形成時期、傳播路線、流行地域等重要問題的論述,要么沒有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而因襲舊說、人云亦云,要么對尚有爭議的問題在缺乏學理支撐的前提下主觀臆斷、妄下定論,導致很多觀點顧此失彼,漏洞百出。例如:“秦腔誕生于陜西,以關中為中心而形成,此地古稱秦,流傳此地的音樂便稱為‘秦腔’,亦稱‘秦聲’。”(第1頁)秦腔的起源地歷來是秦腔研究中最具有爭議性的問題之一,至今尚無定論,如此斷語,實難服人。不僅如此,針對同一問題,高著中不乏自相矛盾的對立性表述,例如:“秦腔產生于秦隴大地,此處也是周秦文化的發祥地。”(第4頁)
再如,關于秦腔的傳播路線,高著認為:“順著絲綢之路,秦腔由陜西出發,經甘肅直達新疆,完成了融入西域音樂因素,形成豪邁粗獷之秦聲,再流播西北、唱響大西北的歷史回環。”(第16頁)“秦腔在西北的傳播正是絲綢之路的功勞,順著絲綢之路,經過清代和民國時期,秦腔傳遍了大西北,成為西北人最喜歡的劇種。”(第21頁)這一觀點僅可聊備一說,缺乏足夠的學理依據。誠然,在學術研究上,“大膽的假設”非常必要,但須與“小心的求證”緊密結合,否則便會陷入一廂情愿的自說自話或任性草率的主觀臆斷。
知識性錯誤向來被視為學術研究之大忌。通觀高著中層出不窮的知識硬傷,有些確實屬于無傷大雅的細枝末節,似乎不該苛責,但由此反映出的治學態度問題卻不容小視。事實上,高著中的大多數硬傷并非是因為研究材料的稀缺或學術能力的不足等客觀原因造成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治學態度的不夠嚴謹、審慎。當下,學風浮躁已成為時代痼疾之一,學術研究中只求數量與速度而不求質量、求大求全而不求精、隨意立論而不求實證的現象甚為突出,這嚴重背離了學術研究的求真精神。其實,如果秉承求真務實、嚴謹審慎的治學態度,高著中的很多硬傷本來可以避免,可惜著者并未力行。
綜上所述,高著是當前秦腔史研究的一個典型樣本,其中編寫理念混亂與研究視角游離、學術視野褊狹與問題意識欠缺、知識硬傷頻現與治學態度粗疏等諸多缺憾的存在,說明20世紀秦腔史的研究與寫作尚有廣闊的提升空間。
① 參見康保成《中國戲劇史研究入門》“附錄”,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230頁。
② 當前可見的較有代表性的秦腔史著作有:焦文彬主編《秦腔史稿》,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楊志烈、何桑:《中國秦腔史》,陜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版;蘇育生:《中國秦腔》,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版;焦海民:《秦腔:1807年的轉折》,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4年版;吳民、鐘菁:《中國秦腔史》,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等。
③ 高益榮:《20世紀秦腔史》,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4年版。引文出自該書者,均隨文標注頁碼。
④ 高益榮主持申報的“20世紀秦腔史”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批準號:07XZW13),2014年以《20世紀秦腔史》結項,成果鑒定等級為“良好”。參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網站,http://fz.people.com.cn/skygb/sk/index.php/Index/seach。
⑤參見楊惠玲《一部別開生面的劇種史新著——評高益榮教授〈20世紀秦腔史〉》,載《陜西理工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躬耕《秦腔史研究的新成果——讀高益榮教授〈20世紀秦腔史〉》,載《當代戲劇》2015年第3期;孟建國《〈20世紀秦腔史〉序》,載《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雒社陽《老樹綻新花今朝更好看——〈20世紀秦腔史〉評析》,載《光明日報》2015年7月21日;趙興勤《秦腔史研究的新收獲——簡評高益榮教授〈20世紀秦腔史〉》,載《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13期。
⑥ 原文如此,疑為“完備”。
⑦ 王正強主編《秦腔詞典》,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⑧ 孫仁玉、李桐軒:《易俗社章程》,紀念西安易俗社成立七十周年辦公室編輯組編《西安易俗社七十周年資料匯編(1912—1982)》,內部資料,1982年,第55頁。
⑨ 原文如此,應為“觀照”。
⑩ 指易俗社丑角演員樊新民。
? 此處有誤,應為“王良”。
? 指三意社秦腔表演藝術家蘇育民。
? 參見劉寬忍《秦腔百年》,太白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頁;姚春鐸《秦腔情結》,太白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頁。
? 參見蘇育生《中國秦腔》,第199—200頁;姚春鐸《秦腔情結》,第26頁。
? 玉振:《孫仁玉傳》,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頁。
? 王正強:《秦腔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頁。
? 上海藝術研究所、中國戲劇家協會上海分會編《中國戲曲曲藝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頁。
?蘇育生:《舊話重提——關于魯迅與易俗社質疑》,西安戲曲志編輯委員會編《西安戲曲史料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3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