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的詩學
一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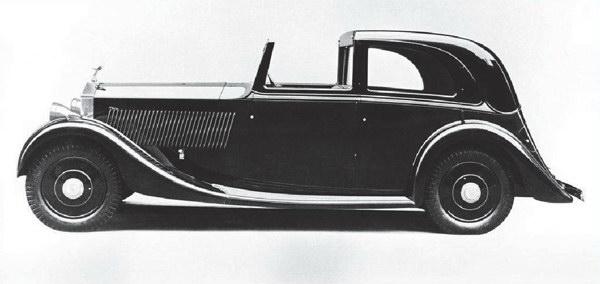
誰曾聽聞車的詩學?沒有。因為詩來不及對車作出反應,因為詩遭遇了一種完全陌生異己的物質。詩對車的喧鬧報以沉默,詩意在車轍處藏起了自己的足跡。
車是反詩意的。
在古代,車僅是代步工具,或是戰場的利器,因此它屈居于鄉思或戰爭的借代轉喻。在古詩中車沒有完整的形象。“晨起動征鐸”,只有聲音被征召入詩;或者作為軒蓋華幕暗指豪門貴族。這并非源于古代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車,車在古代是被忽略的。它只能在部件上附帶詩意,或作為象征性的符號。至如莊子的螳臂當車的寓言,車卻完整地缺場,表現為抽象性的力量,這恰好預示了它的現代身份。
依濟慈、莎士比亞的要旨,劉勰的意旨,詩有挫萬物于筆端之力,為何在現代依舊回避車?車的機械身軀迥異于詩歌水乳交融的肌體嗎?車的風馳電掣超越了詩的意蘊嗎?車的財富象征玷污了詩的田園夢想嗎?如朱光潛言,詩人的觀感組織為意象,并在回味和融洽中至于詩境。但車不容人的回味,人們面對川流不息的車輛,只有驚訝可言。龐大的身影在彈指間歸于虛無,這是和“逝者如斯夫”大相徑庭的印象。不止如此,車輛還以其狡黠的外殼抵抗人們的注視,以轟鳴的噪音打斷詩人的冥想。即便是現代詩也少有車的出現,實則兩者有潛藏的血脈,現代詩借來不協調的形式、沖動的情緒和刺耳的音韻。
車解構了詩學的結構,魔力所至,更重組現實的時空。遑論車如何使“山長水闊知何處”成為了陌生的抒情,車輛還打散了時間和空間的組合。人在車中,燈光璀璨化成流動的如夢似幻的光帶。車輛以空間的穿梭騙取了時間,時間被車輪度量。而面對這種變幻而重復的景象的路人,卻恍然有時間停止之感,刺痛他的,是車掠過身邊的痕跡對空間的切割。愛倫·坡小說中的人物沉迷于徜徉街上與陌生人打照面的快感,然而現代城市中車輛、公路及周邊商場吸納了這一切。游蕩者不復感于人的物化,他的詩由流動的物的暴露組成。一個詩人在街上必須提防來往車輛,這是城市緊張感的微觀。車改造了城市的功能,高速公路和現代化的馬路劃分了不同區域,人必須服從他長期習慣的世界的變動。
那么,車所不在處,正是車的詩學。詩中難能有車,車卻成為小說或更多更微妙零散的詩意的元素。車提供一個安逸、功能齊全的封閉空問,它是身體的物質延伸。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摩托車與轎車催生的公路小說,似乎驗證了車如何成為心靈反抗靈魂的同謀。人們在車里找到獨立或孤獨感,車即沉默的詩學。
詩學對車的否認中,多少有一絲尷尬與羞恥,車的神話與詩的神話爭光,車使詩不得不承認其詞語與音響的偶然外殼,車以反詩意的灑脫構建自足的詩學。人們以為找到了特立獨行的反叛,卻回歸到了古老的歡欣與疼痛。
(編輯:于智博)
評點:宗銀軍
這是一篇匪夷所思的佳作。作者的思想天馬行空,讀來讓你步步驚心,時時意外,又不得不被作者的奇思妙想所折服。作者把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車與詩學扯在了一起,卻為的是證明“車是反詩意的”,然后一路搖曳生姿,“車”與“詩”生發出一派旖旎風光,種種悖論神奇地互相對峙又互相支撐,行文與語言別致新穎,自成一派,既有“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琳瑯滿目,又有萬變不離其宗的清晰線索,同時還有自圓其說的邏輯結構。作者對詩與詩學都有深刻的體驗與認識,所有材料信手拈來,運用自如,整篇文章豐贍圓熟,深厚大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