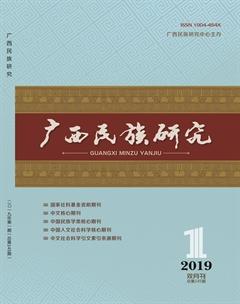邊疆民族地區網絡民族輿情治理探索
張麗君 黃明濤



【摘 要】邊疆網絡民族輿情主體的民族性與多元化、輿情議題的敏感熱度與復雜性以及輿情傳播方式的交互性與開放性,共同擴大了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的破壞性與建設性兩面相的影響力。因此,以整體治理理論為范式,分析出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治理現狀中立法相對紛雜混亂、治理主體核心的政府組織機構龐雜低效、輿情監測研判體系缺失、互聯網行業與民族大眾參與度低等問題;并針對現有問題,以整體治理理論為度量尺,嘗試繪出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的整體性治理愿景。
【關鍵詞】邊疆民族地區;網絡民族主義;網絡民族輿情;整體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9)01-0054-011
一、思路與進路:網絡民族主義再思考與整體治理理論
源起于網絡輿情的“網絡民族主義”最早出現在2003年,從“網絡詞語”到“爭議性學術概念”的發展過程中,①學術界對其的定義業已呈現出多樣性和爭議性,②這些爭議的焦點集中在“網絡”和“民族”兩個關鍵詞上:“網絡”即“互聯網”引起的變革性意義,以及“民族”內涵界定及使用情況的混亂。
若同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一樣將媒介本身視為信息,[1 ]18冠以“網絡”媒介的網絡民族主義則不僅是網民“思維模式”轉變的塑造因素,也是這一轉變結果之體現,那么以“自媒體”新發展為主的社會化媒體③時代帶給“網絡”的變化就再次給“網絡民族主義”區別于傳統民族主義而相對獨立的存在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網絡民族主義所呈現的到底是什么“民族”的民族主義呢?對于我國而言,我們所言的“中華民族”則與西方語境中國家意義層面之“民族(Nationality)”對應,而中文語境中的“少數民族”則應以“群族(Ethnicity)”稱之更為恰當。[2 ]但是在中文中既已然約定俗成稱為“民族”,那么為了避免再次引起不必要的混亂,可將“民族”看作是Ethnicity和 Nationality的復合概念,并且視語境而分別使用“中華民族”和“少數民族”。而恰恰正是這樣的爭議和混合使用,讓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所展現出的“邊疆網絡民族主義”具備了成為“網絡民族主義”組成部分的可能,從而也打破了只談論“國家民族層面的網絡民族主義”{1}的局限。這不僅是對網絡民族主義范圍的重新思考和確立,更為重要的是:基于這樣的再思考,有助于正確理解和分析我國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的現狀,并且還是進一步探索如何實現對邊疆民族地區網絡輿情治理體系建構的前提性條件。
在現今金字塔式官僚層級體系之下,《立法法》修訂后賦予市級政府部分立法權,從而再次分割了權力,“政府碎片化”特征加劇;而同時,對于邊疆民族地區而言,一貫行之有效的“民族區域自治”將民族地區特殊化處理在某種程度上亦是“政府割裂”態勢的表現之一。而“整體治理( holistic governance)”就是指通過縱橫相接、制度化、經常化以及有效跨界合作協調,實現預期利益的治理模式 [3 ],并且實現整體治理的關鍵在于協調與整合、制度化與責任感、信息化與參與感(join-up)等 [4 ]。因此,核心在于“重整碎片”和“彌合割裂”的整體治理理論,就為網絡民族主義浪潮下的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治理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以確保邊疆穩定安全、健康全面發展,同時這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的環節之一。
二、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網絡民族主義結構化分析
除去地理因素外,文化和政治等因素也可以成為邊疆的界定標準,[5 ]盡管對“邊疆”的界定標準并不完全一致,在我國,邊疆民族地區是指沿著國界線與外國領土接壤的內蒙古、甘肅、新疆、西藏、云南、廣西六大行政省所覆蓋的區域。{2}邊疆民族地區網絡民族輿情則是指這片區域所出現的網絡民族輿情,即在互聯網上對邊疆民族問題發表和傳播各種觀點、立場等信息的總和。
(一)邊疆網絡民族輿情主體結構及其面相
邊疆網絡民族輿情也呈現出“網絡民族主義”的建設性與破壞性共存的表現,這就體現為多元的民族性輿論主體以及其復雜面相。
1.民族大眾:民粹式宣泄與正當訴求表達
根據統計顯示(見表1),幾乎人人為網民,其中普通民族大眾網民則是基數最為龐大的群體,他們均有可能成為網絡輿情的制造者、傳播者、關注者。作為民族集體中的一分子,他們所展現的觀點則被稱為大眾民族主義——與知識分子民族主義、官方民族主義共同構成以“一國民族主義者身份”判斷標準劃分的民族主義類型。[6 ]295-316
戈夫曼 (Gofman)的社會擬劇論認為,“個體在特定時間內交往活動的場所總是可以分為‘前臺和‘后臺,人們在前臺的表現與社會期望值相符合,而在無人在場的后臺或非正式的場合,個體在其中所展示的大多是自我沖動、自發和具有個性的成分” [7 ]。互聯網創造的虛擬空間恰恰放大了“后臺”之“無限可能”,誘發部分網民發表嚴重情緒化的激動言論,在網絡民粹主義的刺激和推動下走向極端網絡民族主義,形成了極具破壞性、危險性的網絡輿情危機。當然,這種虛擬與真實、前臺與后臺、表達與內心相互交織的環境,也是一種對網民積極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的潛在鼓勵,讓“沉默的大多數”敢于也能夠以社會一員的身份參與輿論探討,因為“網絡空間具有強大的信息聚合功能,為凝聚多元意見,尋求‘最大公約數提供了重要平臺” [8 ],為達成基本共識奠以基礎,進而推動實現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
2.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意見領袖:煽動性主推手與理性“滅火器”
“由于用戶的身份在網上并不明顯,因此他們可以在創建自己的互動空間時扮演任何身份。人們能夠在一個可以以多種形式塑造和重塑的空間中跨越社會以及身份的‘邊界。” [9 ]網絡民族輿情中的主要觀點制造者、爭論焦點制造者均可被認定為意見領袖,但現實中他們是何種身份則具有多種可能。對于宗教文化濃厚的邊疆民族地區而言,在宗教方面具備領導者權威的人物就極有可能成為意見領袖。其次便是具備一定學歷的民族知識分子,他們因其學識和民族身份,更容易獲得其所在民族群體的認可而成為群體代表者。或者民族研究人員的觀點被利用,利用者就“順理成章”成為意見領袖得到“擁戴”和“認可”。
2.民族性以及高危敏感性
邊疆的政治屬性、安全屬性以及多民族常態,也意味著邊疆網絡民族輿情具備民族性以及高危敏感性。社會發展不平衡之下的“相對被剝奪感”以及“沉默的螺旋”{1}推動的群體極化,共同作用于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的生發、傳播以及刺激社會沖突升級。正如尼葛洛龐帝所言:“網絡真正的價值越來越和信息無關,而和社區相關……而且正創造著一個嶄新的、全球性的社會結構。” [25 ]213故而,變革時時都潛伏在現有社會結構的表象之下,變化時刻都在發生,如何正確處理具備一定“涉外”屬性的邊疆民族地區網絡民族輿情必定還需要顧及全球化趨勢,對政府治理而言挑戰再次升級。
“人人都是麥克風”時代帶給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的這些新特征、新變化加劇了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治理的政治風險,也正廣泛并深刻地改變著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的政治生態。網絡媒介建構了民族輿論場以供民族大眾情緒宣泄的同時,也拓寬了我國邊疆民族地區民眾的參政議政渠道,這已然改變了民族大眾表達訴求的思維,即在表達訴求時第一時間往往想到是通過網絡媒體宣傳呼吁支持和關注。并且多民族雜居、互融和自治的邊疆民族地區,由于民族文化、傳統習俗、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的不同,各民族在認知、情感、行為傾向上都存在差異,這種差異直接關系到他們的政治行為,影響到各民族在村民自治中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26 ]這也引發了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治理問題的再思考。
三、邊疆民族地區網絡民族輿情治理現狀與困境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27 ] “治理”替代了“管理”,此宏觀觀念上的轉變在應對邊疆網絡民族輿情而言具備轉折性意義,但是如何完善仍處于發展中狀態的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治理體系,仍充滿重重困難和挑戰。
(一)基本秩序建構:依托立法,但有待完善
1.一般性立法:從無到有、從法律效力低位階到高位階
由最根本的《憲法》所賦予的公民言論自由(第35條)與其限制(第51條),再到《國家安全法》《網絡安全法》以及《反恐怖主義法》所共同堅守的國家安全統一之根本、反對一切分裂行為以維護國家網絡空間主權和安全,是目前已有的治理邊疆民族地區網絡輿情具有頂層設計意義的有力法律依據。
在三部狹義意義上的法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委員會制定并頒布的法律)之前,國務院早已頒布了諸多針對互聯網管理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肩負著維護我國互聯網安全、健康發展的重任。行政法規方面,從1997年的《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修正)》到2011年《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修訂)》和《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實現了我國互聯網立法的從無到有,目前共計有9項與互聯網相關的行政法規。而部門規章方面則更為具體、全面,涉及視聽節目傳播、網絡文化管理、服務市場秩序、用戶信息保護等,以及上述狹義法律的配套管理規定等共計9項。規范性文件則共計15件,主要針對各大互聯網服務者如微博、論壇、直播平臺等進行了服務規范的規定。
簡言之,中國互聯網發展三十多年后,直到2016年我國才將網絡自身安全即網絡安全與作為媒介方式之一的網絡所可能引發的網絡輿情危機及其可能刺激引發的現實公共危機事件等安全問題,在狹義法律層面上加以區別規范。對后者的立法主要仰賴于盡管靈活性較高但法律位階相對較低的行政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等,這可能會導致對地方性立法的靈活性約束過多。并且,若地方性立法中并無對狹義法律如何實施進行立法,那么原則性、一般性更強的基本法律如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則會被打上一個問號。
2.邊疆民族地區地方性立法:差別明顯且無區(省)際合作
在立法數量方面看,新疆在六個地區中相對最佳,并且一直與時俱進,而甘肅地區則相反;各地均有涉及處罰的法律規定,并且六地區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皆已步入正軌;關于電子政務方面,僅廣西、云南兩地頒布了政府規章,其他四地區均無。簡言之,六個省區就同一事項的規定卻以不同法律位階的法律規范呈現,是否是一種隱性的沖突?地方性法律法規具備的地方區域界限,在面對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的波及無界限性時是否對區際合作立法治理提出了要求?就現在區際合作為零(立法層面無從體現)的現狀來說,這些都是挑戰。
(二)立法中的規范化制度:多種但分散
1.對互聯網用戶身份管理從匿名制到部分實名制的轉變
自2010年起我國開始了部分互聯網行業實行實名制,比如網絡游戲實名制、網絡交易平臺實名制、手機用戶實名制等。如上述新疆、西藏、云南三地均出臺了地方性法規或地方政府規章規范電話和互聯網用戶真實身份管理。此外,自2017年10月起,我國相繼頒布4項規范性文件針對不同類型交互式互聯網信息平臺:一,論壇社區、新聞跟帖評論,采取先審后發制度,實時巡查、應急處置等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二,公眾賬號,采取分級分類管理;三,互聯網群組,實施群組責任制;四,微博,采取“后臺實名、前臺自愿”的用戶管理認證原則。針對這四者均實行分級分類管理、信用等級管理和失信黑名單管理制度。
2.許可和備案制度
國家對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實行許可制度,對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實行備案制度。比如,針對新聞信息,實行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制度;針對視聽節目,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主管部門實施監督管理以及許可制度。
3.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內部建設管理制度
首先,針對互聯網新聞類從業人員(提供新聞信息服務者),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內容管理從業人員管理辦法》規定了相應的行為規范、教育培訓以及監督管理。其次,各大負有主體責任的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均應當建立健全從業人員教育培訓等制度,具有安全可控的技術保障和防范措施,配備與服務規模相適應的管理人員,比如微博、公眾號服務提供者應建立總編輯制度(信息內容安全負責人崗位)等。
4.國家和地方網信辦建立了行政執法督查制度
網信辦行政執法督查制度其中包括:執法人員持證上崗、培訓制度;執法過程采取從“管轄、立案、調查取證、聽證與約談、處罰決定與送達、執行與結案”標準規范化程序。
(三)相關組織機構:改革背景下的種類紛雜與職能重合
2018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印發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管理調整為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管理,后者還負責全國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工作以及監督管理執法工作。此外,中宣部以及各省區市黨委宣傳部負責輿情監測、引導和應對,培養和把控正確意識形態。
根據互聯網工作板塊的不同,國務院多部門實現了分工負責:一,公安部計算機管理監察機構負責有關國際聯網的安全保護管理工作;二,工業和信息化部則對全國的域名服務實施監督管理;三,文化部負責制定互聯網文化發展與管理。
六大邊疆民族地區均設立地方網信辦。此外,為應對邊疆網絡民族輿情還必須通過各地政府組成部門及其直屬管理單位共同完成,他們的級別不同但是職能卻有重合。以新疆為例:一,中央駐疆通信管理局內設機構“網絡安全管理處”“互聯網管理處”,前者負責網絡安全事務,后者負責對互聯網行業(包括移動互聯網)進行管理并配合相關部門和行業做好有害信息、違法違規網站處置工作等。二,區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區工信委)內設機構“信息化推進處”負責指導和協調與自治區信息化相關的事務。三,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區發改委)的直屬及管理單位“區信息中心(區電子政務外網管理中心)”則負責推進電子政務工作。四,區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負責對互聯網視聽節目、網絡新聞的內容等進行審查以及對新聞單位、記者進行管理,把握和引導輿情走向和創作導向等。
一方面,治理主體以政府為中流砥柱,故而組織機構(治理主體)的治理理念尤為重要;另一方面,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不同性質級別的組織機構紛雜;再則,六個省區間也存在區別,并且市縣級的組織機構設計也隨之相區別,比如云南省盡管是六個地區唯一的非自治區,但是云南有自治州,情況則更為復雜。
(四)動態治理流程現狀
1.監測預警體系未建立導致監測水平良莠不齊
目前,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的監測主要通過各政府采購企業研發的具備“輿情監測”功能的技術設備進行。如新疆公安邊防總隊網絡輿情監測系統采購項目成交公告、西藏高院與北京人民在線網絡有限公司合作輿情系統開發和監測研判服務公告、呼和浩特市宣傳部微博輿情檢測系統中標(成交)公示、內蒙古網信辦互聯網輿情應急指揮平臺中標(成交)公告等。據此,不難發現,監測預警的作用無須強調,但是由于重合職能組織機構眾多,監測預警的權限以及運行并不明了;并且盡管均采取政府采購的方式進行合作式監測預警,但是在邊疆民族六地區政府網站“信息公開”中不能快速查詢這些公告,這就反映出各地政府網站的運行管理能力、信息公開工作水平都還有待提升。
2.分析研判
(1)信息研判標準過于寬泛。互聯網信息研判標準,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為成文法律,二為社會道德風尚,后者亦以成文法律的形式得以體現,主要為:行政法規《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15條;國務院規范性文件《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第6條“七條底線”;地方性法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防范和懲治網絡傳播虛假信息條例》第13條列舉了10項標準,該標準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的“九不準”多了“宣揚宗教狂熱、破壞宗教和諧的”一項。進入了法律的規定范圍社會道德風尚衡量標準,主要體現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商業道德”“公序良俗”等,如《互聯網用戶公眾賬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第4條、《互聯網群組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第4條以及《互聯網論壇社區服務管理規定》第10條。
(2)網絡輿情分析師等專業人才培養,雖靈活但缺乏制度管理。現在得到普遍認可的網絡輿情分析模式為“三結合模式”: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軟件與人工分析相結合、分析師與專家會商相結合。[28 ]2014年前后,由國務院工業和信息化部“全國網絡輿情技能水平考試項目管理中心(NPST)”負責組織輿情管理師資格考試與授予證書,但是目前從工信部官網已無法查證該考試是否還在進行;而后由人民網推出的“人民慕課”開設“輿情培訓”專項工作,為目前全國相對權威的網絡輿情分析師的培養組織。網絡輿情分析師資格全國性考試的取消,一方面靈活了專業人才培養方式,但是也意味著網絡輿情分析師這一“職業”并未形成政府體系性管理,六個邊疆民族省區的治理輿情的各層級、各屬性的組織機構中有多少是“合格”的輿情分析師也并無統一標準進行判斷。
3.已有治理方式缺少活性
網絡問政是邊疆民族地區民族大眾進行正當訴求表達的重要渠道,能發揮對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的疏導作用。“網絡問政”的出現可以追溯到2001年,隨著2008年6月國家主席胡錦濤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2009年2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網友在線交流并接受中國政府網與新華網聯合專訪,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互聯網政治時代,[29 ]各地方政府也逐步開展網絡問政服務。
但是,如表4所示,新疆網絡問政平臺建設相對更為全面,幾乎覆蓋所有市縣;而內蒙古則相反,幾乎空白,雖然孫友和楊曉輝“以目前辦得較有影響力、在網絡問政方面敢為人先的內蒙古新聞網(www.nmgnews.com.cn)為例”分析了內蒙古的網絡輿情與網絡問政問題,但這一網站并未進入表2中人民網全國網絡問政黃頁。其他區(省)的網絡問政網站數量也寥寥無幾,絕大多數沒有“有效活性”。
四、邊疆民族地區網絡民族輿情整體治理愿景
以“整體治理”理論為基礎,不僅是以整體治理理論為方法論分析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治理現狀,還是“度量尺”“測試劑”,衡量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治理是否還具備可提升空間的體系框架。
(一)貫穿始終:正確意識形態培養與媒介素養養成
“網絡虛擬社群不系統的意識形態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沖突,其本質是網絡虛擬社群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侵蝕和消解”? [30 ],并且在社會化媒體時代,網民“具有明顯的主體性特征,主體性的發揮不再是被約束和控制的單主體性發揮,而是雙向互動的平等對話、彼此交流的關系” [31 ]265。這就意味著若任由絕大多數網民組成的“民族大眾”個體主體性特征趨勢愈發凸顯,“自我獨立”的意圖亦會隨之增強,若又缺乏媒介素養,則一定會加劇其破壞性。因此,媒介素養涉及的主體就不應再局限于僅“傳媒業者”,而應囊括“民族大眾”及“政府官方”。
對于一個平衡的、積極的信息傳播系統來說,公眾媒介素養、傳媒業者媒介素養、政府官方媒介素養三者缺一不可。[32]政府官方作為民族輿論場域的“生態質量”監測、維護者,應具備“管理者素養”和“媒體使用者素養”,即在觀念和制度上所應體現出的素質能力,主要包括:打破工具性看待媒體的局限,尊重并保障媒體行業權利,接受監督;合理運用社會化媒體處理社會化媒體輿情,以疏導為主,保障言論自由;開放性交流常態化,以預防性處理為核心,主動搭建暢通交流平臺;保證信息源真實權威和傳播方式之公眾可接受度;以法制宣傳教育為主要依托,充分利用互聯網特性實現政府工作人員、互聯網行業者、民族大眾法治愛國意識提升。
作為信息生產者與消費者,互聯網行業者不僅是網絡服務的“供應方”,更是信息的“過濾器”;不僅是配合政府治理履行職責成為邊疆民族大眾網絡言行的監測員,還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網絡言行的監督人;不僅應當是保持職業精神、不斷提升專業素質的行業人員,還應當是邊疆民族大眾網民、政府工作人員的標桿與塑形框。
邊疆民族大眾是在國家整體之內的部分,對民族特性的肯定與強調不等于與國家統一相違背或脫離,恰恰只有在具備“國”的觀念下,邊疆民族作為國內之某“族”才具備存在的可能;而這樣的觀念需要政府的教育輸出與邊疆民族大眾的觀念養成與實踐。邊疆民族大眾的受教育程度與其網絡言論的理性程度相關,所以除了被動接受政府官方的法制宣傳教育——教育輸出的一部分——以外,主動發展“自我理性”,遵紀守法,亦是邊疆民族大眾成為合格中國網民的必修課。
意識與思維決定行為及其表征,因此媒介素養養成與正確意識形態培養是克服邊疆網絡民族主義破壞性的思想前提,是對邊疆網絡民族輿情主體理性思維的建構,亦是實現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基礎,故而貫穿于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治理環節的始終。
(二)制定全國電子政務法,完善立法體系,搭建層級式電子政務統一平臺,為整體治理可行性提供立法保障
波利特(Pollit)認為,整體性治理能夠“排除相互破壞、腐蝕的各種政策情境,更好地共享稀缺性資源,促使某一公共政策領域中不同的利益主體間團結協作,為公民提供無縫隙而非分離的公共服務” [33 ]。
在我國,部分政策是我國正式的法律淵源,因為可以通過政策的靈活性彌補法律僵化可能;并且在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之下,邊疆民族地區(包括云南省的自治州)享有變通立法權,同時,2015年新修改的《立法法》賦予了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有限立法權,這都給予邊疆民族地區相當高度的自治空間,為整體性政府的建立以及優化立法和政策提供了優質土壤。因此,六地區應當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權,制定切實可行的法律規范,與時俱進地、及時不斷地修改法律法規以適應互聯網新時代對政府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竺乾威教授認為“在一定程度上,整體性治理是從技術角度來理解的,技術要求從分散走向集中,從部分走向整體,從破碎走向整合” [4 ]。因此,在當前中國互聯網技術逐步成熟的狀態下,推行全面電子政務不僅可能還成為必要。盡管當前各邊疆民族地區政府通過政府網站、即時通訊通信工具(社交交互平臺)等現有互聯網信息平臺開展電子政務工作,但是這樣看似多元的方式并未形成統一管理,這對政府工作人員不僅是一個挑戰,對邊疆民族大眾而言也是困擾。在立法方面,六個邊疆民族地區中僅內蒙古、云南和廣西制定了電子政務相關政府規章。因此,制定全國性電子政務法,構建全國到地方各層級的統一電子政務平臺,迫在眉睫。
(三)以“網信辦”為協調機構,聯通政府內部機構,搭建政府外部溝通機制,實現整體治理之多方主體參與式協同治理
希克斯指出整體性治理就是在政策、規則、服務供給、監控等過程中實現整合,整體性治理體現于不同層級或同一層級內部,不同職能間,政府、商業性組織與非政府間等三個維度中。[34 ]28-31
目前,合并職能相同的不同層級的政府組織機構這一辦法過于單一,而整體治理的關鍵在于建立協調機制,因此以“中央和地方網信辦”為協調機構是當下可操作性強的方式。其進步意義在于:一,對政府內部而言,可以消解已有的多重多種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治理主體“中央駐地方行政機關、省政府組成部門(內設機構、直屬管理單位)、省政府直屬機構”間可能存在的職能沖突;二,對政府外部即政府與社會而言,“網信辦”為非行政性質組織機構以及大眾的“自下而上”的合法參與提供了合法渠道。{1}
(四)建立監測預警與分析研判體系,提升政府治理邊疆網絡民族輿情能力
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的產生與現實社會中的事件問題的關系,會成為影響治理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的要素之一,因此區分“原生型(網絡誘發型)”(網絡曝光本體現實事件而后輿情引發變體事件)和“伴生型”(本體現實事件的網絡討論形成輿情且無引發變體事件)邊疆網絡民族輿情就具備一定實踐意義。故而,政府應對情況的良好與否就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邊疆網絡民族輿情已然形成后是否還會再次引發變體現實事件。
目前,國內具有代表性的輿情監測中心僅有:人民網輿情數據中心,依托于人民日報社與北京人民在線網絡有限公司(人民在線)成立;中青輿情監測室則由中青在線和北京中青華云新媒體科技有限公司聯合打造,隸屬于中國青年報社。因此,鼓勵發展第三方輿情監測室(中心),充分發揮其技術手段,以中央和地方網信辦為主軸開展政府與社會組織間多方位的合作,實現“統一的監測研判平臺”的搭建,做到政府各層級部門或單位間技術共享、信息共享、人才流動等,是實現整體提升政府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治理能力的有效方式。
網絡輿情分析師不僅是將監測預警與分析研判兩個流程連接起來的橋梁,也是連接政府與社會的紐帶,并且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就是專業人士的儲備、培養,因此,依托于統一的監測研判平臺培養網絡輿情監測分析師也是必需。故而,六個邊疆民族區省應當建立“地方網絡輿情監測、分析師培養培訓機制”,如培養具備使用少數民族語言能力、了解本地民族風俗習慣的網絡預期監測師、分析師,尤其是對于易出現極端網絡民族主義性輿情的新疆、西藏地區,還應當培養同時具備使用少數民族語言與外語(英、德、印、法等)能力的網絡民族輿情監測、分析師。
邊疆民族地區政府還應當效仿其他地區的先進模式,與高等學府共同建立人才培養、資源共享的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研究中心,比如浙江省委宣傳部和浙江工業大學合作建立的浙江省輿情研究中心、重慶大學輿情研究所與新疆烏魯木齊報業集團建立的輿情研究基地等,這些研究中心的建立亦可以納入“統一監測研判平臺”體系建立中。
五、結 語
整體治理邊疆網絡民族輿情是對傳統行政管理、公共服務模式的突破,但也是“未竟的事業”,需要政府與政府的協調、政府與社會的共治、政府與市場行業的合作、政府與公眾的互信。探索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的整體治理是實現我國政府成為整體政府、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種科學實驗,并且是預防和遏止邊疆網絡民族輿情破壞性結果、發揮和利用邊疆網絡民族輿情建設性意義的最佳方式。
正視邊疆民族輿情,即正視邊疆民族關系,因為,網絡空間已然與現實世界密不可分,是意識形態流動與較量的新場域,是現實社會問題的鏡像與寫照。故而,治理邊疆網絡民族輿情就是治理網絡民族主義,就是民族大眾參與本民族事務治理,實現民族自治權、表達權、監督權的路徑,也是推動邊疆民族地區政府決策優化、電子政務發展的關鍵,同時對維系邊疆穩定與國家穩定、維護我國網絡主權、提升我國互聯網大國國際競爭力、共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也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2] 馬戎.關于“民族”定義[J].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1).
[3] 胡穎廉.行政吸納市場:我國藥品安全與公共衛生的治理困境——以非法疫苗案件為例[J].廣東社會科學,2017(5).
[4] 竺乾威.從新公共管理到整體性治理[J].中國行政管理,2008(10).
[5] 楊鹍飛.“邊疆”再探:概念、類型與治理路徑[J].廣西民族研究,2017(2).
[6] [日]青三瑠妙.冷戰后中美關系中的大眾民族主義[G]//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7] 曾堅朋.虛擬與現實:對“網戀”現象的理論分析[J].中國青年研究,2002(6).
[8] 張勤.網絡輿情的生態治理與政府信任重塑[J].中國行政管理,2014(4).
[9] Gado Alzouma.The state and the rebel:Online nationalisms in Niger[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2009(4).
[10] [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馮克利,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11] [美]凱斯·R·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M].黃維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2] 楊佩.從交往合理化看民族共識的生成機制[J].廣西民族研究,2017(3).
[13] 楊吉.數字時代的必修課——楊吉TMT百部全說[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4.
[14] 王小東.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論[J].戰略與管理,2000(5).
[15] 王軍.試析當代中國的網絡民族主義[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2).
[16] Lloyd Cox.Neo-liberal Globalisation,Nationalism,and Changed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for Secessionist Mobilisation[G]// Aleksandar Pavkovic and Peter Randa,eds.The way to statehood,Secession and Globalisation.Hampshire:Ashgate Press,2008.
[17] 韓磊.“國家聲援西藏運動”組織藏獨活動研究(1988-2010)[D].吉林:東北師范大學,2015.
[18] 張莉莉,王嵩楠.“藏獨”網絡恐怖活動應對措施初探[J].西川警察學院學報,2009(5).
[19] 趙國軍.新媒體時代“疆獨”網絡分裂主義及其治理[J].廣西民族研究,2015(2).
[20] 阿地力江·阿布來提.境外“疆獨”勢力對新疆的網絡滲透及其危害[J].現代國際關系,2013(7).
[21] 相德寶.國際自媒體涉藏輿情及輿論斗爭的規律、特征及引導策略[J].情報雜志,2016(5).
[22] 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2018-01-31)[2018-08-14].http://www.cac.gov.cn/files/pdf/cnnic/CNNIC41.pdf.
[23] 2016年中國社交應用用戶行為研究報告[EB/OL].(2017-12-27)[2018-08-20].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sqbg/201712/t20171227_70118.htm.
[24] 劉建明.輿論傳播[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25] [美]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26] 閔衛國,錢素華.提升政治心理品質、促進民族雜居地區村民自治的健康發展[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
[27]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EB/OL].(2017-10-27) [2018-08-22].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1027/t20171027_524003098.shtml.
[28] 王偉.關于建設新疆互聯網輿情監測體系的幾點思考[J].學理論,2014(10).
[29] 張廷.網絡問政:社會管理科學化的重要路徑[J].電子政務,2011(12).
[30] 楊嶸均.論網絡虛擬空間的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策略[J].馬克思主義研究, 2015(1).
[31] 張春華.網絡輿情:社會學的闡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32] 彭蘭.社會化媒體時代的三種媒介素養及其關系[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
[33] Christopher Pollit.Joined-up Government:Survey[J].Political Studies Review,2003(1).
[34] Perri 6.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New Reform Agenda[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
EXPLORATION ON THE NETWORK PUBLIC OPNION MANAGEMENT IN THE BORDER ETHNIC AREAS:BASED ON THE THEORY OF “HOLISTIC GOVERNANCE”
Zhang Lijun ,Huang Mingtao
Abstract: The nationalit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main subject of the frontier network, the sensitive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 subject issues, and the interactivity and openness of the subject communication methods have jointly expanded the destructive and constructive influence of the frontier network. Therefore, taking the theory of holistic governance as a paradigm,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ethnic public opinion in the frontier ethnic areas, such as the relatively uncoordinated legislation, the complex and inefficient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the lack of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and judgment system, the low participation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and the national public, etc.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taking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theory as a measure, try to draw a vision of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of the frontier network nationwide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Frontier Ethnic Areas; network nationalism; network national public opinion; Holistic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