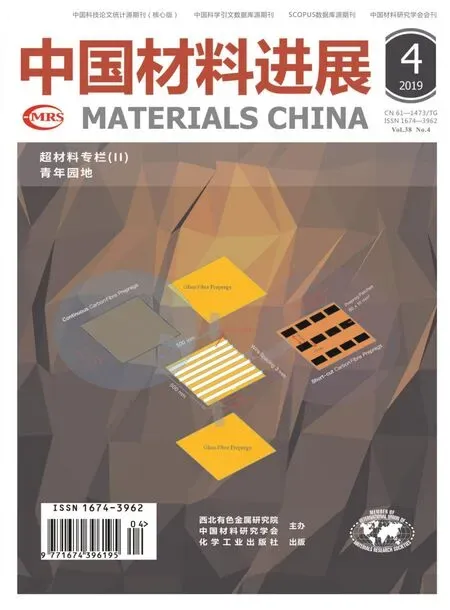負介材料:超材料的分支
范潤華
(1.上海海事大學海洋科學與工程學院材料系,上海201306)
(2.山東大學材料液固結構演變與加工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山東濟南250061)
1 前 言
材料的物性參數是選材用材的依據,例如抗拉強度、泊松比、導熱系數、電導率、磁導率、折射率等。這些參數通常都是正值,而且高性能材料上述參數的量級往往也“高”。介電常數是材料的基本物性參數之一,在電子元器件、微波器件等廣泛應用的射頻(1 MHz~100 GHz)頻段,介電常數用復數表示。材料的介電實部一直被認為正,高介材料一直是電介質材料的重要發展方向[1]。負介電常數早先未被注意,近來被視為超構介質(metamaterials,也稱超材料)的典型性質。超材料在性能方面的特點是負的物性參數,在結構方面的特點是相應于物理特征尺寸的周期性結構。清華大學周濟最早在國際上開展超材料和常規材料的融合[2-4],十幾年來已成為重要發展趨勢:一方面,將常規材料引入超材料,提升超材料的性質和功能;另一方面,發揮超材料的可設計優勢重構常規材料,結合超材料的負物性“超常”性能重新審視常規材料,拓展材料性能空間。
關于周期性陣列構造的超材料及其負物性參數,業已開展了大量研究,常規材料的射頻負介電行為報道較少。其它超材料的性質主要決取于陣列結構,是一種“人工”性質,而材料界更關注的是物相組成和微觀組織。因此,如果能從材料學角度,基于材料“本征”性質實現負介特性,將會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如果可以把某些超構介質看作是一類有序的導體/絕緣體復合結構,那么導電相和絕緣相隨機復合并對其微觀組織進行調控,無序的、隨機復合的導體/絕緣體復合材料也有可能具有負介電等性能。基于上述思路,作者研究組[5-12]研究了這類常規材料的負介電性能,建立了負介材料這一超材料分支。
2 導體/絕緣體復合構筑負介材料
導體/絕緣體復合材料兩異質相的電學性質差異巨大,屬于逾滲復合材料。導電相為金屬,絕緣相為陶瓷的情況下,這種復合材料事實上是工程上早已廣泛應用的金屬陶瓷,可以采用粉末冶金或特種陶瓷工藝制備。圖1是熱壓燒結制備的Fe/Al2O3金屬陶瓷微觀組織,照片中襯度淺的物相是Fe[11]。Al2O3陶瓷基體中,金屬Fe導電相的連接和聚集隨其含量變化很大。單相金屬的射頻復介電常數很難也沒必要定量研究,一般認為是個虛數,即實部為量級很大的負值,虛部為量級上比實部更大的正值。在陶瓷基體中加入金屬,當其含量達到一定臨界值時,復合材料的介電性能發生顯著變化,由類絕緣體性質轉變為類金屬性質,這就是逾滲現象,臨界的金屬體積分數稱為逾滲閾值。逾滲閾值取決于金屬的類別、形貌,及其在陶瓷基體中的分布狀態。

圖1 不同Fe含量的Fe/Al2O3金屬陶瓷光學顯微照片[11]Fig.1 Optical images of Fe/Al2O3cermets with different Fe content[11]
為了更好地控制微結構,發展了原位制備技術。首先燒結制備多孔陶瓷,然后采用液相浸漬技術將金屬前驅體負載到多孔陶瓷中,最后還原處理,在陶瓷的孔壁上形成不同形貌的金屬相[6]。其特點是:與通常的金屬陶瓷制備工藝相比,可以比較方便地對材料微結構進行剪裁,金屬相的形貌、粒徑可以比較方便地控制;制備溫度可以降低到300℃,避免了金屬與陶瓷兩相的反應,適用于更多種類金屬陶瓷。圖2為不同Ni含量Ni/Al2O3的介電譜[6],由圖可見,Ni質量分數為17%的Ni/Al2O3(圖中的Ni17),其介電常數和氧化鋁類似;Ni含量增至26%時(Ni26),介電常數仍為正值,但是數值增大,頻散變得顯著。Ni含量進一步增加至31%時(Ni31),較低頻段介電常數為負值,并在530 MHz附近出現法諾共振。可見,體積分數逾滲閾值相應于該質量分數。Ni含量進一步增加至35%(Ni35),復合材料的介電常數在整個測試頻段均為負值。此外,同樣技術、不同工藝條件下制備的多孔化Fe/Al2O3等復合材料中也發現了類似現象[7]。
逾滲復合材料為負介性能調控提供了豐富的手段,導電相可以是金屬、碳材料等不同類別,可以是顆粒、纖維、片層等不同形貌;絕緣相可以是陶瓷,也可以是樹脂。與陶瓷基復合材料相比,樹脂基復合材料易于成型加工,并可用于柔性器件。以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為基體,加入不同體積分數的多壁碳納米管(MWCNTs)作為功能體,采用原位聚合工藝制備了PDMS/MWCNTs薄膜復合材料,在1 GHz附近觀察到了負介電常數[10]。以丙烯酸聚氨酯為基體,加入石墨烯作為電學功能體,獲得了具有良好柔韌性的樹脂基復合材料,其頻散特性符合Drude模型。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浙江大學 Peng等[13,14]多年致力于結構功能一體化超復合材料研究,做出了開創性工作。該團隊在樹脂基體中利用鐵磁金屬線構筑低損耗負介材料,通過改變構筑方式或金屬線本身的性質對負介電行為進行調控,技術路線與典型的纖維復合材料一致,特別適合工程化。

圖2 原位技術制備Ni/Al2O3工藝流程示意圖和介電譜[6]Fig.2 Shematic of in-situ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dielectric spectra of Ni/Al2O3composites[6]
3 負介電機理
3.1 電感和電容功能體
在樹脂或陶瓷絕緣基體中加入各種導電填料的逾滲復合材料,其介電性能研究已有很長的歷史,為何這類材料可以具有超常的負介電行為?
Xie等[9]的研究發現,絕緣基體中連通的導電相形成逾滲網絡具有電感效應(L)導致負介電,孤立的導電相具有電容(C)效應并通過LC諧振影響負介電頻散特性,從而明確了逾滲復合材料呈現負介電性能的微結構特征。圖3是FeSiB非晶金屬與環氧樹脂所組成逾滲復合材料的顯微結構與介電頻譜。FeSiB顆粒進行絕緣包覆作為電容功能體,形成逾滲網絡的未包覆FeSiB顆粒作為電感功能體,兩種功能體適配可以精確調控復合材料的負介電性能。

圖3 FeSiB/EP復合材料兩類功能體構筑與性能精確調控[9]Fig.3 Construction and property manipula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dielectric fuctional units in FeSiB/EP composites[9]
3.2 體等離振蕩
介電常數反映了材料存儲電場能量的能力,其值為負并不違反能量守恒定律。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負介電常數是自由電子在交變電場中運動狀態的描述。當自由電子在交變電場下簡諧運動時,任意時刻電場力的方向與電荷的運動方向均相反。也就是說,材料內部的感應電場方向與外電場方向相同,這就意味著負介電常數的產生。自由電子在交變電場下的這種簡諧運動,稱為等離振蕩,用Drude模型描述[5]:

其中,ΓD是阻尼因子,ωp=2πfp是角等離頻率,fp是等離頻率,neff是等效電子濃度,meff是等效電子質量,e是電子電荷(1.6×10-19C), ε0是真空介電常數(8.85×10-12F/m)。可見,負介電行為是金屬等導體的固有屬性。金屬的等離振蕩頻率在光頻附近,低于該頻率,金屬的介電常數為負,所以負介電行為在光學或紅外波段很常見,Drude模型可以定量描述金屬等導體在光學或紅外波段的負介電常數。然而,在頻率遠低于光頻的射頻頻段,單相金屬的介電常數實部是量級為108的負數,而虛部是量級更大的正值,金屬等導體的射頻介電常數實際上是虛數。根據公式(1)和(2),射頻段有實際意義的負介性能,需要材料的等效電子濃度降低到適中。有兩種途徑,一種是電子濃度適中的半導電單相材料;另一種就是導體/絕緣體復合材料,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導體的自由電子濃度被絕緣體“稀釋”,達到適中的“等效”電子濃度。
等離振蕩是載流子濃度的漲落。只有當載流子在復合材料內部能夠自由運動,不受到區域的限制時,才能有載流子濃度的波動,產生等離振蕩效應,從而表現出負介電行為。因此,導電相的表面狀態及其在絕緣基體中的分布狀態對等離振蕩效應有很大的影響。
3.3 材料學參量
由等離振蕩理論可知,負介電常數取決于兩個材料學參量:載流子濃度和載流子遷移率。在某一頻段,只有當載流子濃度達到相應量級時,材料才會產生負介電現象,但是載流子濃度過高,會造成復介電常數為虛數,因而材料載流子濃度需具有可調性;載流子遷移率則影響損耗,其值越高,損耗越低。單相材料可以通過摻雜、能帶工程調控載流子濃度;對于復合材料,可以將導電相與絕緣相異質混合作為調控手段。導電功能體本身決定了載流子遷移率和損耗機制,其在基體中的含量和連通狀態等因素決定了復合材料等效載流子濃度和相應的負介電數值。
從逾滲復合材料的微觀結構特征可知,隨著導電相含量的升高,復合材料中形成逾滲網絡,產生負介電常數。增加導電相含量,實質上是提高復合材料的等效載流子濃度。在可見光頻段,電子濃度區間是1021~1022cm-3,單相負介材料通常為金屬材料;而在紅外波段,要求載流子濃度在1019~1021cm-3之間,一般為半導體或半金屬材料。因此,在設計負介材料時,材料的載流子濃度需具有可調性。半導體可以通過p型或n型摻雜調控其載流子濃度,金屬材料能通過合金化的方式達到控制其載流子濃度的目的,從而在可見光和紅外波段調控負介電常數的數值和頻散特征。
但是,對于射頻段負介材料,要求載流子濃度更低(108~1011cm-3),而金屬的載流子濃度遠高于此濃度范圍。通過異質復合構建的逾滲復合材料解決了此問題。控制逾滲復合材料中導電相的含量,可有效地控制復合材料的等效載流子濃度。同時,導電相的幾何構型也顯著影響等效載流子濃度。當導電相呈低維度構型時,即呈纖維狀或片狀時,能使得等效載流子濃度降低。因此,逾滲復合材料為載流子濃度的調控提供了豐富的手段。
在設計負介材料時,除了考慮負介電常數的量級,往往還兼顧到介電損耗,這涉及到載流子遷移率,其值越低,損耗越高。低的載流子遷移率,載流子在傳輸的過程中產生的碰撞越多,將導致高的傳導損耗。載流子遷移率主要受載流子的等效質量和散射概率影響。等效質量越大,則遷移率越低。材料中的雜質和缺陷越多,以及晶格振動越大,則受到的散射的概率越高,載流子遷移率越低。圖4給出了各類單相材料的載流子濃度和遷移率[15]。帶間躍遷也將產生額外的能量損耗,因此盡量選擇具有高的載流子遷移率和低的帶間躍遷損耗的材料。除了金屬和半導體材料,石墨烯由于具有高的載流子遷移率(25 000 cm2/(V·s))也被用作負介材料的功能體,能有效降低介電損耗。實際上,逾滲復合材料的等效載流子遷移率除了受導電相本身的載流子遷移率影響之外,其在基體中的含量和連通狀態等因素也影響復合材料的等效載流子遷移率。例如,低維度的導電相可以限制載流子在某些方向的熱運動,偏向于朝特定的方向運動,從而提高了其特定方向的等效遷移率。其次,導電相在逾滲復合材料中既呈連通態分布又有孤立態分布,僅連通的功能體相對復合材料的等效載流子遷移率有貢獻。

圖4 不同單相材料的載流子濃度和遷移率[15]Fig.4 Concentration and mobility of charge carriers in different single phase materials[15]
4 討 論
4.1 超材料的內涵
超材料一詞中的“超”,并不是簡單得意味著“超級”。超材料發端于電磁。追根溯源,從Veselago經典論文建立在負介電常數和負磁導率基礎上的構想[16],到Pendry提出金屬陣列實現射頻等離態真正開啟超材料[17],盡管未使用這個詞,但是超材料的內涵仍不離其宗:一是負的物性參數,二是陣列結構。不過,在廣義上,不必拘泥于兼具負參數和陣列結構。即便對于介電常數和磁導率,也不一定像最初的那樣,要求在某頻段同時為負。
經過多年的發展,超材料已涵蓋電磁、光學、聲學、力學、熱學等領域,與光子晶體、等離基元相伴發展。與常規材料相比,超材料是一類通過精確設計的結構單元實現其負物性參數等超常性能的材料;受超材料啟發而發展出的具有超常物性的常規材料在廣義上也被納入超材料范疇[18]。超材料的性能主要決定于人工結構,其設計摒棄了基于自然結構的材料基因,而是通過精確加工的微納甚至更大尺度結構單元重構材料基因,簡化了影響材料的因素,進而突破制約常規材料性能的極限,發展出某些新型材料[2]。
4.2 單負與雙負
介電常數和磁導率是基本電磁參數。單負是指只有一個電磁參數為負值的情況,而雙負是指在某頻段兩者同時為負值的情況。雙負情況下,材料會表現出許多諸如逆多普勒效應、逆契倫科夫效應和負折射率等獨特的性質。應該更加重視單負材料研究,一方面其本身在無線電力傳輸、磁共振成像和電磁屏蔽等工程領域具有重要的應用前景;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材料物相組成、微觀結構及外加場的調控,在單負材料基礎上獲得雙負性質。
4.3 負折射率和其它衍生特性
單負或雙負衍生了諸多新穎特性。除了耳熟能詳的負折射率,也有強吸收、倏逝波等。負折射率是對透明、透波材料而言的,其關鍵是如何降低損耗。與此不同,吸波等損耗材料則談不上負折射率。目前基于負參數的損耗和吸波研究較少。常規材料負介性質的發現,為微波吸收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
4.4 近零電磁參數
研究超材料獨特的電磁特性,不僅僅追求負的電磁參數,實際上正電磁參數接近零也是“超常”性質。負介材料的頻散曲線中,存在跨零的頻段,波長會擴展,空間場和時間場變量解耦,可以實現對波的控制[19]。此外,正介電和負介電構建的疊層材料,有望在電子元器件應用方面取得重要突破[12,20,21]。
4.5 電磁參數反演
復介電常數和復磁導率這兩個電磁參數在微波段事實上密不可分,除非確保其中一個參數可以忽略,例如非磁性絕緣材料可以忽略磁導率,即μ=1。矢量網絡分析儀測試電磁參數是由散射參量反演計算得到的,現有的反演方法不一定適用負參數情況。但是在低于1 GHz的頻段,這兩個參數可以利用阻抗分析儀、數字電橋分別測試,所得到的規律對于超過1 GHz的微波波段也是適用的,MHz和GHz頻段電磁性質都屬于經典電磁學的范疇,物理本質相同。
5 結 語
新性能是材料科學持續不變的追求,負參數為新性能探索提供了空間。負介電常數、負磁導率是電磁超材料的主要特性,但其并非陣列結構超材料獨有,常規材料也可以實現這類某些特性;超材料的物性參數也不一定限于負值,負參數也既可以涉及到單一參數又可以涉及到同時為負的多個參數;超材料既可以在紅外、可見光波段,也可以在相對較低頻的射頻頻段發展。
超材料著重通過結構來獲得人工性質,常規材料從材料本征特性出發來實現負的電磁參數;超材料與常規材料的融合成為今后發展的趨勢,充分結合超材料的“人工性質”與常規材料的“本征性質”。負介材料,作為“具有超材料某些性能的常規材料”,或者說“利用常規材料技術實現的超材料”,也許是這種融合的一個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