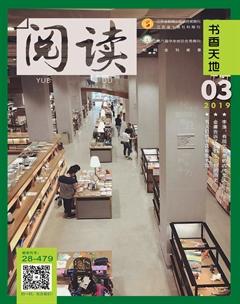朱光潛:真誠坦蕩 唯美是求
向學
朱光潛,字孟實,現當代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我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主要著作有《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西方美學史》《談美》等。朱光潛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溝通了西方美學和中國傳統美學,使東西方美學得以融會交流,溝通了唯心主義美學和馬克思主義美學,連接了“五四”以來中國現代美學和當代美學。他為中國美學事業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一、一顆讀書的種子
1897年9月19日,朱熹第26世孫出生,生于桐城陽和的岱鰲山下(今樅陽縣麒麟鎮岱鰲村朱家老屋人)。這個書香世家為他取名——朱光潛。
朱光潛為長子,下有兩個弟弟朱光澄、朱光澤和五個妹妹。祖父朱文濤是貢生,父親朱黼卿是個鄉村私塾先生。
朱光潛從小便喜愛讀書。有一年春天,朱光潛在家門口放牛,自己坐在旁邊念書,逐漸的,他就把放牛的事情忘記了。那頭大水牯牛本來在田埂上吃草,不知道什么時候,已跑到附近田里大口大口地嚼起來。幾個時辰下來,一大片稻秧遭了災。后來,朱光潛的父親只好賠了人家的稻谷,朱光潛被父親狠狠地教訓了一頓。
朱光潛自幼十分聰穎,興趣廣泛。朱光潛家鄉陽和鄉岱鰲村在桐城東鄉,窮鄉僻壤,買書很難。距家二三十里地西南面,有一個牛王集(牛集鎮),每年清明前后,附近幾縣農民都到此買賣牛馬。因為人多,各種商人都來兜生意,省城安慶的書賈也來賣書籍文具。這年春天,一個族兄去牛王集買了一批書回來,慷慨地借給朱光潛看。父親不許兒子讀圣賢以外的書,族兄買的書,對于朱光潛來說是一個盛典。族兄買書,沒有固定的愛好。他買什么,朱光潛就借來看什么,如試帖詩、《楹聯叢話》《麻衣相法》《太上感應篇》等,只要族兄有的書,朱光潛都借來看。結果,朱光潛涉獵較為廣泛,為其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自6歲到14歲,朱光潛在父親鞭撻之下,也打下了扎實的古文功底。朱光潛在岱鰲山下,花了7年時間,背誦了《四書》《五經》的大半,學會了寫策論、時文。1910年秋,14歲的朱光潛來到離家十幾里路的孔城中街,上了“洋學堂”——桐鄉高等小學堂讀書。只讀了一年,他就轉入桐城中學。
1916年,朱光潛又考入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中文系,成為免費師范生,隔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從五所高等師范學校里考選20名學生,到香港大學去學教育。
他盼望著去香港。順利選入20人的朱光潛,在港大入學考試時,因為數學、英語不及格,他被迫先補習一年。直到1919年,他才正式被香港大學教育學錄入。
就讀香港大學時,朱光潛與朱鐵蒼、高覺敷三個人都是從內地來的,三人都不愛運動,走哪又都帶著書,同學們就給他們起了個稱號“三個哲人”。確實,1921年,剛讀大二的他,論文處女作《弗洛伊德隱意識與心理分析》就在當時全國標志性刊物《東方雜志》上發表。港大的師生都說:“這個內地的學生,真不簡單。”
朱光潛學習勤奮,治學嚴謹,在香港大學求學時。他以“恒、恬、誠、勇”這四個字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恒,是指恒心,即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撓。恬,是指恬淡、簡樸、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質上的享受。誠,是指誠實、誠懇,襟懷坦白,心如明鏡,不自欺,不欺人。勇,則是指勇氣、志氣,勇往直前的進取精神。
二、時代與婚姻
1919年,法國召開巴黎和會,英美法決議把德國人手里的山東出讓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輿論嘩然,爆發了意義重大的“五四運動”。青年人崛起,開始向封建余力示威。不久后,在朱家也發生了一場新舊角逐。
1922年夏,朱光潛回家探親,他這時已經25歲了。家里為給他安排了一位陳姓女子,兩人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快就結婚了。
妻子是小腳女人,比他小一兩歲,個子中等,性格溫順。兩人婚后生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出生時,他還在香港讀書,按照家族輩分,就為他取名為朱世粵了。
1923年6月,27歲的朱光潛自香港大學畢業,來到上海中國公學任英文教師。朱光潛到中國公學后,把二弟朱光澄安排在本校讀書。弟弟班上有一位同齡的女同學奚今吾,剛滿18歲,四川南充人,溫婉美麗,擅長數學。而他的父親奚致和,正是四川名紳。這個聰明漂亮的四川姑娘,秉性不俗,只是因為剛開始學習英文,很是著急,因此得到了英文老師朱光潛的格外關心。同時,她也給獨自在上海的朱光潛,帶來了許多甜蜜的時刻。
此時,朱光潛與陳氏已經結婚,并育有一子,但包辦婚姻是沒有戀愛和感情基礎的。遇到奚今吾后,朱光潛內心常冒出和陳氏分手的念頭,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但他害怕父親阻止,內心深處十分痛苦。
江浙戰爭爆發后,朱光潛利用這短暫時間回了老家,與陳氏談分手的事。朱光潛的話一說出口,父親立即暴跳如雷,并大發脾氣,說:你要休妻,就不要進我的家門!
其實,世粵上小學時,朱光潛與原配陳氏的婚姻已經風雨飄搖,父親似乎早就預感到了破裂的可能,給孫子改名為“朱陳”。他雖然滿意這個兒媳婦,架不住朱光潛執拗,苦苦支撐數年以后,還是同意兒子和陳氏離婚了,也還是父子倆不斷斡旋的結果。10多年后,他自海外歸來,撲在父親的棺材上大哭一場,稍補為人子的孝心。
關于愛情,朱光潛有自己的見解。
他在書里寫道:“一般人誤解戀愛,動于一時飄忽的性欲沖動而發生婚姻關系,境過則情遷,色衰則愛弛,這雖是冒名戀愛,實則只是縱欲。我為真正戀愛辯護,我卻不愿為縱欲辯護;我愿青年應該懂得戀愛神圣,我卻不愿青年在血氣未定的時候,去盲目地假戀愛之名尋求泄欲。”
所以,對于他自由戀愛的第二任妻子奚今吾,他展現出一個男人的成熟和堅定,兩人從一見鐘情到白頭偕老。
三、讀書人的風骨
1924年,處在婚姻困境中的朱光潛,得到了夏丏尊的幫助。他被邀請到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教英文。當時,這里還有豐子愷、朱自清等教師。
但在春暉中學,不久后卻發生了一起教師集體辭職事件。
原因是體育課上老師帶領全班喊口號,一個學生聲音蓋過了老師。體育老師認為這是對他的不尊重,要求開除該生。但朱光潛及另一位老師匡互生極力反對,將處罰改為了“取保留校察看后效”。
原本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但出差回來的校長亨頤得知此事,憤然不平,他認為“這樣的學生非開除不可。”
匡互生索問開除的理由,這位校長竟說:“開除一個學生,要同他們說什么特別的理由?就算要說出理由,那就給他‘品性不良,不堪造就八個大字已夠了!”
匡互生是性情中人,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故而辭職,朱光潛等其他幾位老師也拂袖離開春暉中學。
走的時候,很多學生來挽留恩師,后來干脆一起來了上海,加入這群民主人士創辦的立達學園。后來擴充師資力量,請來了葉圣陶、胡愈之、夏衍等一批大家。
在20世紀30年代之時,朱光潛曾為自己立下座右銘。座右銘共6個字:“此身、此時、此地。”此身,是說凡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決不推諉給別人;此時,是指凡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決不推延到將來;此地,是說凡此地(地位、環境)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決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在這條座右銘的激勵下,朱光潛先生不斷地給自己樹立新的奮斗目標,他在80多歲時,依然信心十足地承擔起艱深的維柯《新科學》的翻譯任務。
讀書人的風骨是不容小覷的。
四、異國求學,歸國教書
朱光潛不光教學生,還敏銳地觀察到國內現代美學方面的空白,寫出了第一篇美學論文《無言之美》,讓摯友朱自清、夏丏尊都驚嘆不已。1925年夏天,他深覺故國之落后,吾身之粗淺,經過繁雜的考試,朱光潛通過了英國庚子賠款基金會的考試,被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錄取,教育廳贊助他每年20英鎊的學費。
歐洲大學一年中只上半年的課,余下時間可以自由安排。朱光潛在倫敦、巴黎大學都選修了課程,兢兢業業。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時。朱光潛發現美學是他最感興趣的,于是把研究美學作為自己終身奮斗的事業。當時,他的指導老師、著名的康德專家史密斯教授竭力反對。他告誡朱光潛說,美學是一個泥潭,玄得很。朱光潛先生認真思索后,決定迎難而上。這時,他給自己立下一條座右銘:“走抵抗力最大的路!”從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學研究中,終于寫出了《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等具有開創意義的論著。
后來他從愛丁堡大學畢業,還在讀書,這邊官費停供,原本就不寬松的生活,更加捉襟見肘。
他從大學起就上課、寫作兩不誤,不僅靠稿費養活著自己和赴歐的奚今吾,他還抽空撰寫了多本書,《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藝心理學》《談美》等。這樣高效用的工作習慣,為他一生的學術研究都奠定了基礎。
他在《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規勸年輕人:“人類學問逐天進步不止,你不努力跟著跑,便落伍退后,這固不消說。尤其要緊的是養成讀書的習慣,是在學問中尋出一種興趣。你如果沒有一種正常嗜好,沒有一種在閑暇時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東西,將來離開學校去做事,說不定要被惡習慣引誘。”這番話,放到現在依舊適用。
1933年秋天,朱光潛自歐洲學成回國,經胡適力薦,到北大外語系任教。后在北大文學院講西方名著和文學批判史,課上經常給學生普及美學教育。
時人評述,他在當時對中國現代美學具有拓荒作用。
但這里也有一個小插曲。
到北平后,朱光潛常去北海看朋友或買東西。他去北海,可走后門向西,拐一個彎,但需要買門票;也可以一直朝北走,走后門大街去北海,不需要買門票。一般情況下,他喜歡走大街。倒不是朱光潛舍不得花20枚銅子,他是嫌多了一層手續。
秋天的一個傍晚,朱光潛在北海里的白塔頂上,望北平城里的樓臺煙樹,望到西郊的遠山,望到將要落下去的紅艷艷的太陽,他想起李白“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名句,覺得目前的境界真是蒼涼而雄偉,突然產生了自己不應該再留在這個世界里的念頭。
這次想法,真是來得突兀。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同時,自信自己的精神是正常的。
凡事都是事出有因。1925年夏天,朱光潛通過了英國庚子賠款基金會的考試,出國留學。幾年之后,在浪漫之都巴黎,他又一次邂逅奚今吾。奚今吾大約在1928年去歐洲,在巴黎大學學習一般女生望而生畏的數學專業。雖然兩人已經分別了幾年時間,卻一點沒有生疏之感,并且愈發地感覺到相互之間磁石般的吸引力。朱光潛再也壓抑不住內心的情懷,向楚楚動人的四川姑娘表達了他的愛情。幾年后,當他們共同留學于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時,一朵并蒂蓮花盛開了。
新婚一年的漂亮妻子在法國繼續讀書,而朱光潛因為北大的工作,不得不丟下妻子先期回國。一種強烈的想見到妻子的愿望而不能實現,這個愿望在一個黃昏幻化成了絕望。在后來幾次談到自己輕生的念頭時,朱光潛把這個真實的輕生誘因,深深地埋在心底了。
妻子終于忍不住對于丈夫的思念,而未等畢業就提前回國了。
五、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朱光潛在校園里堅守著一方講臺,教書育人。直到1966年,北大校園里,站在三尺講臺的老師而今成了批斗臺上的“罪犯”。這一年,朱光潛已經70歲了,以他為主導的美學研究正在國內開花。此時,一切都戛然而止。
有人聽說他是研究美學的,在批斗會上大聲諷刺他:“這樣一個瘦干巴老頭一點兒也不美,根本不配有美學家的稱號。”朱光潛答:“我看上去不美,是因為我把美獻給了社會。而有些人看上去好像美,是因為他占有了社會的美。”他身體是孱弱的,講話總是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態。
1968年,朱光潛和馮友蘭、季羨林等教授一同被關在牛棚里,直到春節也不能回家。家里面大外孫出生了,他都沒得及看一眼。牛棚條件極差,很多人擔心朱光潛撐不下去了,揭發他的大字報張貼得到處都是。但朱光潛卻開始鍛煉身體了,他要活下去,還有很多書沒翻譯,還有很多課沒上。
早上,他跑到角落里做一套自己設計的太極拳,晚上躺在被窩里,他也堅持做動作。有一回,正在打“太極拳”的朱光潛被發現了,監管的人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一通痛罵。挨罵后,朱光潛還是接著練,挨罵不要緊,活下去才重要,同屋的教授看他這么堅持,一面震動,一面也為他捏著一把汗。
夏玟后來問他:“為何能這般從容?”朱光潛謙遜地說:“人有時不得不面對自己無法左右的處境,那就只能平靜地承受它。這樣的沖擊對我也有幫助,使我靜下心來重新審視自己。”
不要忘記,朱光潛是一位美學家、教育家。他希望從美學的角度來解釋人生的種種現象,比如用美詮釋輕生,剖析其自殺念頭的起因。這樣的他,想必心下自是“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如”了吧。
在1936年,朱光潛曾在北大寫文章說:“我現在還記得在一個輪船上讀《少年維特之煩惱》,對著清風夕照中的河山悄然遐想,心神游離恍惚,找不到一個安頓處,因而想到自殺也許是唯一的出路;我現在還記得15年前—還是20年前—第一次讀濟慈的《夜鶯歌》,仿佛自己坐在花蔭月下,嗅著薔薇的清芬,聽夜鶯的聲音越過一個山谷又一個山谷,以至于逐漸沉寂下去,猛然間覺得自己被遺棄在荒涼世界中,想悄悄靜靜地死在夜半的薔薇花香里。” 坐船是一次經歷,讀詩時是另一次經歷。
“在一個輪船上”,就是指1924年9月乘船過焦山那次想沉江的經歷,這次自殺的念頭起源于婚姻波折和與舊式家庭的決裂。
詩人濟慈在《夜鶯歌》里說:現在死像比任何時都較豐富。朱光潛對濟慈詩中“死”的意念產生共鳴,1947年寫文章說:“他(指濟慈)要趁生命最豐富的時候死,過了那良辰美景,死在—個平凡枯燥的場合里,那就死得不值得;甚至于死本身,像鳥歌和花香一樣,也可成為生命中一種奢侈的享受。我兩次想念到死,下意識中是否也有這種奢侈欲,我不敢斷定。”
朱光潛兩次起了輕生的念頭,但他沒有輕生,因為他是反對自殺的。所以當下的處境只是為他的人生和學問又多添了一份感悟和體驗罷了。
早在1926年夏天,朱光潛在得知其一個學生自殺的消息后,寫了一篇文章。他認為,和絕我不絕世的人比,自殺是有欠缺的,即少了一層“舍己為群”的意味!因此,選擇自殺,不如選擇出家為僧,或隱身山中。
但釋迦牟尼提倡,“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更是值得青年人學習的。墨子、甘地等人,都是從絕我出發,走到淑世的道路上去的。
這種對于“生命的美學”的“知”和“行”,貫串了朱光潛的一生。
1970年,朱光潛回了家,北大需要人翻譯材料,就把他派到學校“翻譯改造”。他掃完廁所,就能在辦公室做文字翻譯了。有一天,找資料時,他意外找到了自己翻譯的黑格爾《美學》第二卷的譯稿。意外之喜,朱光潛又陷入擔憂,這份譯稿還沒編校,就被抄家抄走了,他心里還想繼續校對。
朱光潛偷偷地告訴翻譯組人馬士沂:“這些譯稿尚待校改,但我已經寫過‘認罪書,說不再搞這些東西了。我想拿回來,但不敢去拿,你看怎么辦呢?”馬士沂知道譯稿的重要性,也深知此事的危險性,但還是說:“既然你以前放了毒,現在再把全書好好看看,錯在哪里,批判批判也好嘛!”黑格爾《美學》一共有三卷,共計100萬字,朱光潛此前只完成了一半,那時他已經73歲了,要完成剩下的工作實在是任重道遠。
翻譯組特意掩護老人,將他的桌子挪到了里屋,也不再給他分配改造的翻譯任務。朱光潛每天爭分奪秒埋頭翻譯,他把稿紙寫得密密麻麻。 監管的人看到,也不知他在寫什么,還說:“這個老頭還挺努力的。”
馬士沂又找了位女士重新謄寫,在謄寫中,她主動將遺漏托人傳達給朱老,兩人合力完成了《美學》第二卷的翻譯。
當時朱光潛每個月只有20元生活費,這位女士在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謄寫后,分文不取。在動亂的年代,兩個對學術近乎赤誠的人,合力完成了一本經典譯注。他們翻譯的是《美學》,其行為更是人性的“美學”。
在1979年恢復工作后,朱光潛又開始寫《談美書簡》。
每天從家里走到辦公樓,他都疾步前行。這天下雪,路滑,他特意拄了拐杖,還在鞋子外面纏了一圈草繩,結果還是不慎摔倒。83歲的他,倒在校園小徑上,被路過的學生及時送進了校醫院,這一跤摔得可不輕,光臉上一處傷口就縫了五針。
這下辦公樓也去不成了,回家休息吧,而他還是閑不住,又在床上翻譯起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
有人來探望他,被嚇了一跳,因為他的手、臉都涂滿了紅藥水,還咧開嘴對來人微笑。
“為什么跌倒了?”
“走路快了。”
前半生不愛鍛煉的朱光潛,在恢復自由身后,反倒養成了積極鍛煉的習慣。為了延續生命,每天下午四點都圍著校園跑步。他說:“在動蕩的時候,耽誤了太多時間,往后得養好身體才能把事做完。”他后來生存的每一天,都為了翻譯更多書稿,寫下更多專著。
豐子愷與師父李叔同提倡用“美育”感化人間,朱光潛后半生用闡釋美學。為做學問,他仿佛不知疲倦,但他的身體實在太累了。
1986年3月6日,89歲的朱光潛在北京溘然長逝,留下了十幾本著作,和300多萬字的翻譯作品。
(摘編自“人民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