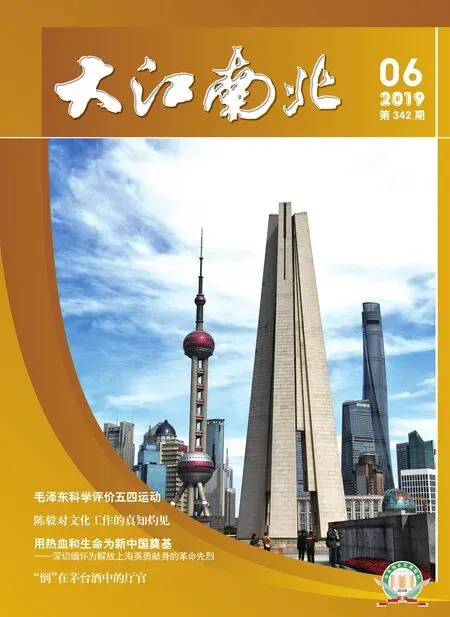患難之交羅晴濤
□丁星
一
1970年9月的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到家里,見到一張客人來訪未遇留下的字條:“我已來南京,很高興即將與你共事。我們住靈隱路15號,是你的鄰居。”署名是羅晴濤。
前幾天我已得知,原任浙江省軍區政治部主任的羅晴濤,即將結束在五七干校的勞動,來任《新華日報》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分管政治工作。我一直興奮地期待著他的到來。我匆匆吃了晚飯,立刻到他的住所回訪。我們緊緊地握手,很有點劫后重逢的感覺。
我和羅晴濤相識很早,但并無深交。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歲月,才有了彼此關切、休戚與共的友情。

羅晴濤
現在的史書說“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其實,1965年12月批判總參謀長羅瑞卿已經揭開這場悲劇的序幕。我多年負責南京軍區《人民前線》報的軍事宣傳,因此1966年6月就被批判為“羅瑞卿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吹鼓手”。事發突然,我惶惶然不知所措。在杭州的羅晴濤聽說了,托人帶口信給我:“沉住氣,相信黨,是非曲直總是會澄清的。”雖然無助于改善我的處境,但這種安慰使人心里溫暖。
幾個月以后,羅晴濤的處境就比我難得多了。
1966年12月23日深夜,浙江的一個造反派組織借口浙江省軍區窩藏省委“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組織一千多名群眾沖進省軍區機關。這是全國首次沖擊軍事機關。浙江的形勢急轉直下,省委和省政府完全癱瘓,造反派再次沖擊并占領省軍區營區。
1967年3月15日,中央鑒于浙江兩派武斗嚴重,局勢極為混亂,決定成立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由省軍區政治委員龍潛為主任,羅晴濤任秘書長。他們為維護社會穩定,堅持生產建設,保護黨政領導干部,日夜操勞,四處奔走。
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開解決浙江問題的會議,后稱“一月會議”。會議宣布毛澤東確定的方針:各自多做自我批評,不要批評對方。“一月會議”結束,羅晴濤回不了浙江了。他先到學習班,然后到了五七干校。
在羅晴濤他們十分艱難的日子里,我們在南京做過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我們不便多聯系了,只能默默地祝愿他們平安。
那時,我任《新華日報》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和編輯部領導小組組長,不參與人事工作。但辦報需要人才。在那個特殊年代,有些人對知識分子的家庭出身、社會關系、歷史問題、思想作風處處苛求,抱有成見。在討論編輯人員去留時,我常常要與別人爭論甚至爭吵。羅晴濤的到來,使我如釋重負。他熟知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愛惜人才,尊重人才。我再也不需要為了留住人才而據理力爭了。
二
1971年春節臨近,羅晴濤向《新華日報》黨的核心小組組長韋明建議,應該到同志們的家里去看看,表示慰問。我們三個走遍報社的各個宿舍區,到了每一位編輯人員和每一位印刷工人的家里。天寒地凍,韋明和我都冷得呵手跺腳,比我們年長的羅晴濤卻精神抖擻。他笑著說,我們還有過穿單衣過冬的日子呢!
于是羅晴濤給我們講了他的那次經歷。
羅晴濤是1938年7月參加新四軍的。1939年春,他所在的新四軍第4支隊挺進皖東敵后,在津浦鐵路兩側開展抗日游擊戰。這年年底,日軍兩千余人占領全椒縣古河鎮,燒殺搶掠,使這個皖東重鎮陷入災難之中。新四軍第4支隊司令員徐海東指揮兩個團星夜兼程,迎戰敵人。經過兩天兩夜的激烈戰斗,收復了古河鎮。時任民運組長的羅晴濤,奉命率全組來到戰場,動員逃難的民眾返回家鄉,組織他們互濟互助重整家園。
那時候新四軍還沒有建立敵后根據地,更沒有被服廠,棉衣都由老百姓手工縫制,數量有限。羅晴濤的民運組出發時,部隊正在分發棉衣。為了讓戰士們先有棉衣御寒,民運組只穿著單衣就動身了。戰斗頻繁,工作緊張,他們一直穿著單衣在冰天雪地里奔波。新四軍的反“掃蕩”戰斗不斷取得勝利,大大鼓舞了皖東人民的抗日信心,許多青年報名參加新四軍。這個冬天,部隊幾次分發棉衣,民運組都讓給了新戰士。看到新戰士穿上棉衣斗志昂揚地奔赴戰場,羅晴濤他們雖然寒冷,心里卻暖暖的。
有一天,中共蘇皖省委書記劉順元來檢查工作,看到民運組同志還穿著單衣,很受感動,立刻拿出錢來,派人買來干樹根讓他們烤火取暖。臨別時,劉順元說,今年前后方的同志大多數穿上了棉衣,唯獨你們還穿著單衣,我回去會派人送錢來,你們盡快就地縫制。三天后,錢送來了,按每人7元,民運組8人共56元,有紙幣,也有銀元。當年經費困難,顯然區區56元也是湊起來的。
那些日子民運組工作繁忙,駐地不斷變動,一直顧不上縫制棉衣。轉眼天氣漸漸暖了。羅晴濤召集全組開會,討論縫制棉衣的錢怎么處理。大家一致認為,國民黨當局不給新四軍發軍餉,前線部隊生活十分艱苦,我們就把這筆錢作為特殊黨費上交吧!
三
有一次,羅晴濤邀我星期天一起去六合走走。現在的南京市六合區,那時還是長江北岸的六合縣。羅晴濤要重訪抗日戰爭的舊戰場,寫一篇回憶桂子山戰斗的文章。
1943年8月中旬,新四軍第2師5旅13團由副旅長羅占云和團長饒守坤率領,從安徽省天長縣的汊澗地區南下,到六合一帶保衛秋收。8月17日,團偵察隊遭遇一股日偽軍。日偽軍仗著人多勢眾,對偵察隊緊追不放,一直追到了六合縣東北的桂子山下。
羅占云和饒守坤決定圍殲這股日偽軍,一聲令下,指戰員斗志昂揚,立即迎著敵人跑步前進。
日偽軍發現面對的是新四軍的主力部隊,一時亂了陣腳,呼叫后續部隊增援,對新四軍展開了瘋狂的反擊。在戰斗過程中,新四軍查明這股敵人共有500余人,其中日軍約有200余人。人數雖不占優勢,但裝備精良,每個班都有輕機槍,還有重機槍和九二步兵炮等武器。
在戰斗最為緊張的時刻,指揮由西向東突擊的副團長陳宗勝和團政治處副主任李秉初不幸中彈陣亡。團指揮所接到報告,立即命令羅晴濤快去1營接替指揮。
羅晴濤當時任團政治處宣傳教育股股長,正在團指揮所通過電話組織宣傳鼓動工作。他臨危受命,立即帶著通信員跑向1營陣地。他揮臂高喊:“要為犧牲的同志們報仇啊!”率領著戰士們奮力沖殺,奪占了路東的一些地方。下午五點,團指揮所傳來命令,要1營用火力掩護2營作短暫休整,擬在黃昏時再合力發起攻擊。他們繼續戰斗,直到暮色蒼茫時,傷亡慘重的日偽軍撤離桂子山,向八百里橋鎮逃去。
羅占云和饒守坤考慮到已經達到殲敵大部的目的,不宜戀戰,決定不再對日偽軍追擊,部隊連夜轉移。羅晴濤又奉命帶領偵察隊打掃戰場,尋找沒有撤離的傷員,掩埋犧牲的戰友。
這一仗,日偽軍傷亡300余人,損失慘重。幾天以后,殘敵就從八百里橋鎮撤走了。新四軍取得了保衛秋收、保衛根據地的重大勝利。

桂子山烈士陵園
這一仗,是羅晴濤第一次指揮一個營和敵人面對面地搏斗。這樣的經歷是很難忘記的。他在重訪桂子山時,默默地走了許多地方。他一定想起了當年的戰斗情景,也一定會想起那些犧牲在這里的戰友。
羅晴濤的回憶文章《血戰桂子山》起初發表在江蘇《新華日報》,1987年10月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淮南抗日根據地》,選入了這篇文章。這本書不久發行到日本,并且被一位參加過桂子山戰斗的日本老兵松原恒吉見到了。他立即給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寫信,打聽羅晴濤的住址,希望交流對桂子山戰斗的回憶。羅晴濤給他復信說:“過去日軍的侵華戰爭,是那些軍國主義頭目干的。你們應招入伍,也是被迫的。”“希望你作為一個歷史見證人,多做些中日友好的宣傳工作。”1988年8月12日,松原恒吉再次來信。他說:“首先向桂子山戰斗中陣亡的貴國軍隊戰士謹表哀悼。”又說:“羅先生的文章和書信,千葉縣、山梨縣、山重縣、兵庫縣等地當年小田大隊的隊員,不論當年戰斗參加沒參加,都一個人緊接一個人轉寄傳看了。他們都在七十歲左右,大家沉浸在當時的回憶中。”隨信還寄來日中友好紀念郵票三套,贈給羅晴濤作為紀念。
四
羅晴濤在萊蕪戰役中的特殊經歷,也很值得記述。
發生于1947年2月的萊蕪戰役,是人民軍隊的一個輝煌戰例。在國民黨軍對我華東野戰軍南北夾擊的嚴峻形勢下,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大膽地決定放棄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一面擺出西渡黃河的假象,一面秘密轉兵北線,求殲孤軍深入的北線之敵。接著,又對龜縮于萊蕪城內外的國民黨第46軍和第73軍采取“圍三闕一”的戰法,在萊蕪北邊布下口袋式陣勢,在敵突圍時聚而殲之。此役共殲國民黨軍七個師(旅)5.6萬余人,是國民黨發動內戰以來在一個戰役中被殲人數最多的一次。
當時,第46軍已經改編為整編第46師,但人們習慣地仍然稱為第46軍,仍然將這個師的師長韓練成稱為軍長。韓練成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對國民黨當局的“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不滿,秘密和共產黨建立了聯系。第46軍調到山東以后,他又秘密會見了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商定由膠東軍區聯絡科科長楊斯德化名李一明,留在韓練成身邊當聯絡員,公開身份是軍長秘書。楊斯德還有一個助手解魁,化名劉質彬,負責在兩軍之間傳遞情報。
在軍令逼迫下進了萊蕪城的韓練成,這時候處于非常為難的境地。他并不愿意指揮第46軍和解放軍交戰,何況他知道突圍已經困難。但他也沒有可能策動第46軍戰場起義。他雖然當了軍長,但這是一支桂系牢牢控制的部隊,師長海兢強是桂系首領白崇禧的外甥,另一個師長甘城成是桂系重要將領夏威的外甥,他們并不聽從韓練成。韓練成焦急不安,一再問楊斯德:“李先生,你說該怎么辦?”又要他們趕快同解放軍聯系,希望和陳毅司令員通電話。2月23日8時許,穿著國民黨軍軍裝的解魁舉著白布,以火線投降的辦法來到華東野戰軍第7縱隊陣地,見到了團長蕭選進、政委李正清和政治處主任羅晴濤。解魁報告了敵軍已經開始突圍的情報,轉達了韓練成希望和陳毅司令員通電話的要求。第7縱隊首長接到報告,電話指示說:“派一個得力干部和解魁一起進城,把敵軍突圍部署搞出來。告訴韓練成,華野前指在移動中,他現在不可能和陳毅司令員通電話;他們已經全部被包圍,為了減少傷亡,他應該命令他的部隊放下武器。”電話最后還說:“可以要你們政治處主任羅晴濤進城去,他過去執行過類似的任務。”
23日10時許,羅晴濤帶著便衣偵察員,從萊蕪城西門潛入城中,在西門城墻根的一個防空洞里,見到了韓練成。楊斯德向韓練成介紹羅晴濤說:“這是西門前線負責干部。”席地而坐的韓練成,站起來著急地問:“怎么樣?和陳毅將軍聯系上了嗎?”羅晴濤說:“華野前指正在移動中,電話聯系不上。你們全部被包圍了,突圍已不可能,為了減少傷亡,建議韓軍長下令放下武器。”韓練成一聽,很不高興地說:“讓我放下武器那不是投降嗎!請你們盡快讓我和陳毅將軍通電話。”羅晴濤又說:“韓軍長,和陳司令員通電話暫時做不到。仗打到現在,你也應該看得出來了,只有放下武器才是唯一出路。”韓練成不作回答,翻開一個筆記本,在本子上寫道:“陳毅將軍我兄,請你下令讓你的部屬尊重我的身份……”然后撕下這一頁,遞給羅晴濤說:“請你趕快派人送出去交給陳毅將軍。”
羅晴濤和楊斯德轉身出了防空洞,商量說:敵人正在突圍,我軍不可能因為韓練成而停止攻擊;既然他指揮不了第46軍,只有讓他趕快離開萊蕪。中午,在楊斯德、羅晴濤的催促下,韓練成出萊蕪西門,到了第7縱隊司令部駐地。
第7縱隊司令員成鈞和政治委員趙啟民說:剛才華野前指來電話了,白天有飛機,天黑后會派汽車來接韓練成,我們就不見他了,你們陪他吃飯。成鈞還說:“你們可以告訴他,李仙洲集團包括他的第46軍全軍覆沒,戰斗已經基本結束。”
羅晴濤、楊斯德和解魁陪著韓練成,吃了在戰場上可稱豐盛的晚餐。天黑后,華東野戰軍司令部派來一輛吉普車,接走了韓練成。
在萊蕪國民黨軍突圍的關鍵時刻,韓練成躲藏起來,接著離開戰場,使第46軍失去指揮,陷入混亂。混亂的第46軍又擾亂了第73軍的隊形。幾萬官兵像一窩亂蜂向萊蕪以北逃竄,落入了華東野戰軍的口袋陣。
2月28日,陳毅在蒙陰城外一個小山村接見了韓練成,肯定了他對萊蕪戰役的勝利是有貢獻的,轉達了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對他的慰問,并對他的去留征求了意見。韓練成認為他還可以回南京去,在國民黨營壘里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陳毅經過慎重考慮同意派人送他去青島,從那里經上海回南京,還派人幫助他編了“戰場脫險”的經過,對每個細節都做了嚴密的掂量。
韓練成回到南京以后的經歷,是另一個情節曲折的故事。這里只需要交待結局:1949年1月,韓練成繞道香港,到了河北省平山縣中共中央駐地;1955年9月,時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的韓練成被授予中將軍銜。
我還想借此機會,講一件后來的事情。
1989年10月,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聶鳳智的回憶錄《戰場——將軍的搖籃》。聶鳳智在這本書里說,萊蕪戰役中,他所在的華東野戰軍第9縱隊活捉了第46軍軍長韓練成。
這當然錯了。當年第9縱隊的任務,是在萊蕪東北之和莊、青石關一帶攔擊北逃之敵。韓練成去華東野戰軍指揮所見陳毅,是往萊蕪東南走,根本不會與第9縱隊照面。何況他有楊斯德、解魁陪同,還有羅晴濤率偵察員護送。楊斯德后來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在回憶錄里對萊蕪戰役中的韓練成有詳細記錄。
事實其實是清楚的。第9縱隊活捉的,是經吐絲口北逃的第73軍軍長韓浚。當年萊蕪城里,碰巧有兩個韓軍長。這大概是聶鳳智晚年回憶有誤的原因。
聶鳳智是我敬重的老司令員。他的回憶錄也很精彩。為了讓后人不必再做考證,我理應對他的這一記憶失誤作出訂正。
五
1979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對浙江省委《關于澄清“一月會議”是非問題的請示報告》作出批復。批復說:“1969年1月中央召開的解決浙江問題的會議即‘一月會議’,由于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轉移了會議的方向。會議產生的文件應予撤銷。對當時受打擊迫害的南京軍區領導人許世友、杜平、錢鈞、陳德先等同志,和省軍區阮賢榜、李國厚、羅晴濤、孟克明等同志,予以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一切污蔑不實之詞統統推倒。”
在這之前,羅晴濤已調回軍隊工作,任江蘇省軍區政治委員。有了中共中央決定的徹底平反,他就可以回到他所熱愛的浙江去了。1980年,羅晴濤調任浙江省軍區政治委員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們保持著經常的聯系。他因事來南京,我去杭州時,都會見面暢談。我們很少談及我們共同經歷的那十年動亂,談的是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在我們都離職休養后,談得最多的是關于新四軍的研究和宣傳,直到羅晴濤于2007年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