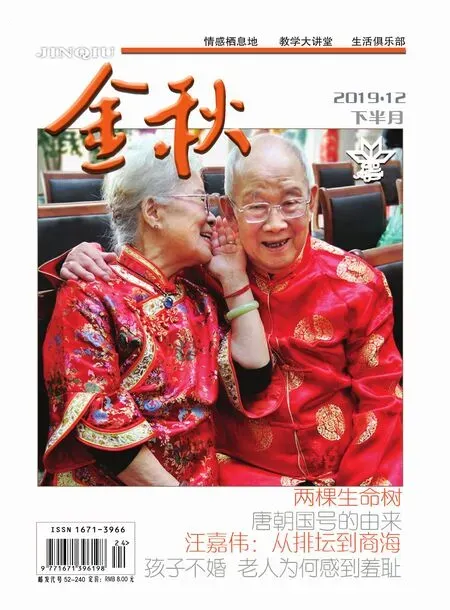讀《詩經(jīng)》:“無用之物”的力量與美
◎文/廣東·肖錫光

竊以為,《小雅·鹿鳴》是《詩經(jīng)》中最令人愉悅的篇章,通篇洋溢著祥和與歡樂,好似一曲曼妙的樂音,正從熱氣喧騰的宴會上傳來,并夾雜著人們傾心的交談和會心的歡笑。“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這樣的句子,讓漢語的音律之美,穿過宴飲之樂,穿過古人的生活,在千年后依然琤瑽回響。
鹿群呦呦,原野上長滿蒿草。舉座盡是嘉賓君子,共享著美酒歡歌。按照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小雅·鹿鳴》原本是周王宴請群臣時所作的樂歌,后來逐漸傳播到民間,在鄉(xiāng)人的宴會上也可以傳唱。
東漢末年,曹操還把此詩的前四句直接引用在他的《短歌行》中,后世也一再吟詠,可見其影響深遠(yuǎn)。《小雅·鹿鳴》通篇彌漫著熱情、祥和的氣氛,這是盛世才會有的場景,沒有曹操“對酒當(dāng)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憂思,而是全然的放松、自信和充盈。
鹿鳴呦呦,在肥沃的原野上,啃吃蒿草和蔓葦。“蘋”和“蒿”都是指柔嫩的蒿類植物,是食草動物喜食的植物。而“呦呦鹿鳴,食野之芩”的“芩”,則是指與蘆葦同屬的蔓葦。它“莖如釵,葉如竹”,和蘆葦一樣,在秋天開白花,遠(yuǎn)望去與荻花無異,也是食草動物所喜歡的。
雖然“芩”與“蘋”“蒿”同列于《鹿鳴》之中,但它也僅僅只在這一首樂歌中露了露臉,在《詩經(jīng)》的其他篇目中卻遍尋不著;在其他古典草本書目中,也幾乎找不見“芩”的身影,或許它可以算是古典文獻(xiàn)中“最受冷落的植物”之一了。
為什么這種動物喜食、身姿也清秀的野草不被人類所記錄呢?我想,大概是因為它的“無用”。因為蔓葦既不能作為菜蔬,也沒有什么藥用價值,特別是在“眾草皆可食”的遠(yuǎn)古農(nóng)耕時代,這樣一種沒有實際功用的野草,實在是無足掛齒。
蔓葦出現(xiàn)在《鹿鳴》中,倒是一個極有意思的隱喻。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人只有在超越了生計的困擾之后,才可以專心享受一些“無用之物”的美妙,比如音樂,比如美術(shù),比如不可采食也不可入藥的蔓葦。所以,單純的“和樂且湛”,單純的享樂和審美,都是一種超越了生存焦慮的狀態(tài)下精神層面的更高追求和需要。“無用之物”的力量和美,也只有在這些時候會被注視和聆聽。
如今看到蔓葦成熟時的葦稈和花穗,會讓人聯(lián)想到日式插花,我覺得,它是很理想的花材,有一枝而知秋的寂靜和山野之味,又不至于過分蕭索。
想到兩千多年前它還在周王的宴會上被唱到;想到那遠(yuǎn)古的原野,蔓葦多么豐盛而自足,鹿群緩緩涉水而過,它們低頭啃噬著蒿草蔓葦,抬頭,是樂聲中流連的靜好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