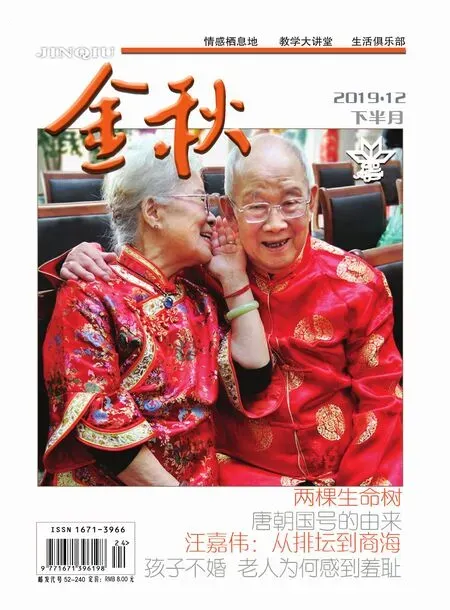幾回花下坐吹簫
◎文/北京·曹雅欣
簫,現為八孔,與笛同源,同屬于材質以竹制為主、不加簧片的單管類吹奏樂器,鼻祖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骨笛。因此,很多人感覺笛與簫較難分辨。
事實上,簫古稱“篴”,發音為“笛”,笛簫確實容易混淆。直到唐宋以降,才明確稱呼豎吹而無膜的為簫或洞簫,橫吹而有膜的為笛。因此,一橫一豎、有膜無膜,便徹底區分開了笛與簫。
這區別,便形成了簫不同于笛的特色。笛膜震動形成了竹笛清脆明亮的聲音,而由于無膜,簫的聲音在竹管里蕩漾而出時,音色就偏于悠遠、深邃、柔美、沉郁,就像蘇軾《赤壁賦》里所說:
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音裊裊,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簫就是這樣深邃,雖音量不大卻影響力強勁。這種幽幽沉沉、纏纏綿綿的氣韻,正是獨屬于簫的氣質。它能使人沉浸在深層體味中,開啟人的心扉,觸動人的靈魂,是一種以靜制動、以柔克剛的深沉力量。
事實上,聽簫,正是在月下才最有意境。比如清代黃景仁的《綺懷》所寫:
幾回花下坐吹簫,
銀漢紅墻入望遙。
似此星辰非昨夜,
為誰風露立中宵。
纏綿思盡抽殘繭,

宛轉心傷剝后蕉。
三五年時三五月,
可憐杯酒不曾消。
簫的陰性特征,使它的音樂大多都不是攻擊性的、直來直去的表達,而總是婉轉低回、悠遠輕柔的訴說。洞簫聲轉,如在耳邊幽幽長嘆,如是清風徐徐拂過,而輕輕帶走了人的心。
所以簫聲也最合憂傷的情緒,簫管里釋放出淡淡的愁緒、綻放出幽然生香的夜之花。伴隨著簫的心緒,是傷亦是美,比如清代龔自珍的詩《吳山人文徵、沈書記钖東餞之虎丘》,其中就寫過很美的句子:
一天幽怨欲誰諳?
詞客如云氣正酣。
我有簫心吹不得,
落花風里別江南。
簫心幽怨,離情別緒。簫聲正如人聲,動情于中,深情于外,似乎這樣的音樂不是演繹出來的,而是訴說出來、嘆息出來的,甚至,是哽咽出來的。比如蘇軾就形容簫是“如泣如訴”,而《秦樓月》中也這樣描寫道: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吹簫的時候,亦是體內氣韻貫通、氣息傾吐的時刻,吹簫人會感覺到胸中所有的郁氣、沉思、深情等等縈懷難抒的情緒隨聲線輸出體外。奏簫,是氣息吐納、換骨輕身的過程。所以深深的愁緒傾吐而出后,簫聲嗚咽如泣,而演奏者本人反倒輕松暢快了不少。
簫雖是吹管樂器,但是在演奏時并不需要太大的肺活量,與吹奏時更為“費氣”的笛子、嗩吶等樂器相比,簫是一種“養氣”的樂器。簫聲起落,是在和情養性,是在調理氣息。所以吹簫也被優雅地稱作是“吟簫”。
吹奏樂是一種線性的音樂表達,因而才會有“絲不如竹”的說法——以絲弦構造的彈撥樂是顆粒狀的音樂表達,它在感染力上遜色于線性樂器那綿延起伏、縈繞飄蕩的聲音。于是,似人語的簫,就常用于送別。被送別者,會在遠行路上感覺那簫聲久久回旋于耳邊,縈繞不絕,這就是線性樂器的魅力,也是簫聲輕柔低沉、輕飄婉轉的功力。所以徐志摩會在《再別康橋》里提到:
……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離別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其實,簫也并非只能淪于傷感,這種樂器由于音色柔婉,能適用于多種形式的演奏:獨奏清麗,協奏飄逸,合奏和婉。
于是,在節日、在樂坊、在喜慶場合,也少不了簫的出席。比如辛棄疾在《青玉案》中就寫道: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宋代柳永描寫在杭州繁盛光景的《望海潮》里也說到簫: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夸。
自古女子奏簫,本身就是極美的一幅畫,在古人畫作里也時有體現,比如五代時期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明代唐寅的《吹簫圖》等。而描寫女子情思的簫曲《妝臺秋思》,通過王昭君的思鄉寥落,充分展現了一份閨怨深深的女性形象。
在詩詞中也常見女子與簫為伴,最著名的要論唐代杜牧的一首《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
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
還有南宋詩人姜夔的《過垂虹》:
自作新詞韻最嬌,
小紅低唱我吹簫。
曲終過盡松陵路,
回首煙波十四橋。
其實,與簫最相合的樂器是古琴。琴簫合奏時,琴聲清麗,簫聲悠揚;琴聲如珠玉,簫聲如引線;琴如陽剛之男兒,簫如婉轉之女子。琴簫和鳴,天衣無縫。金庸著名武俠小說《笑傲江湖》中,就以大篇幅筆墨描寫了知己之間、情侶之間琴簫合奏、天地作合的逍遙場景。
古琴是一件格調高古的樂器,意境深遠,也正如簫,追求的不是花哨的技巧而是廣闊的意境。而且,琴,居于文人四藝“琴棋書畫”的首位,是君子必修的功課,它是樂教的工具,是君子的象征。所以簫與琴和諧,正說明簫也具有君子的格調,是品位不俗的樂器。
簫聲入耳,音量不大,音色悅人,它能越過耳目等表層感官,對人心進行一種深層次的浸潤。
最后用元代貢性之的詩《梅》來為洞簫的氣質構畫做收梢:
眼前誰識歲寒交,
只有梅花伴寂寥。
明月滿天天似水,
酒醒聽徹玉人簫。
簫聲曠古,遺世獨立,風姿灑然,靜夜花香。
一管竹簫奏青天,流云纖,鳥心閑。長吹千載,風花又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