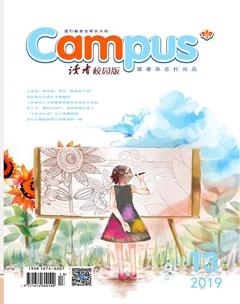主人,有人揍你的雞
權蓉
1
外公的朋友是個老夫子,他講《幽夢影》,說“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那一段,什么“莼鱸以季鷹為知己,蕉以懷素為知己,瓜以邵平為知己,雞以處宗為知己,鵝以右軍為知己……”
我那時小,又執拗,看不明白文人的寄情,說,就季鷹、懷素、邵平、處宗、右軍的莼鱸、蕉、瓜、雞、鵝有知己,關其他的莼鱸、蕉、瓜、雞、鵝什么事兒啊?
為此,他就惱了,說再不在我面前講這些了。
2
爺爺平時看不慣文縐縐的老夫子,所以得知他被我這個小娃娃給噎著了,非常高興,破例開了他菜園子的籬笆門,讓垂涎已久的我踏足。
爺爺的菜園子和別家的沒有什么不同,一樣是用來種四時的菜蔬的,不同在籬笆上。我家的是爺爺用矮紫薇樹編織的樹籬,四季常青,一到開花的時候,滿墻的藍色、白色、粉色花朵。其實我對園子里的青菜、蘿卜提不起興趣,我的興趣都在這些花上。若還有不同,就是我家菜園子里種了一株陽雀花樹。
3
因為是矮樹籬,對雞的防御力特別低。為此,爺爺早早授予我一個“大將軍”的頭銜,不做別的,專幫他攆啄菜的雞。我有時興起,東征西討,無差別驅逐。興致不高時,我就站在園子邊上吼,自然不是大草原上放羊時唱的悠揚的牧歌,而是腔不成腔、調不成調地亂吆喝。
這是之前,而現在爺爺開了菜園子門迎我,讓“大將軍”覺得自己成了園子的主人。
每天去幼兒園前和回家后,我便在癲狂中攆雞,有時身手太利落,還要捉了鄰家的雞給押送回去,討那雞主人的幾顆糖吃。
4
暑假,我帶上老貓去水田里撈一回魚,在菜園子里捉一遍菜青蟲,再攆幾次來偷食的雞,就過完了白天。晚上乘涼,看看螢火蟲,數上兩回星星,聽上一半個故事,眼皮一耷拉,就過完了黑夜。
不知是因為我這又強勢又活躍的執行力度,還是討糖吃的頻率,假期未完,鄰居們就將散養的雞全給圈養了起來。接下來的夏天,菜園子里除了偶爾路過的懶蛇進去曬太陽,再沒有其他動物進去打攪了。
5
夏日晝長夜短,我每天就守著個菜園子跑跳,這時,爺爺又想起了老夫子。他就講能讀書的好、讀書人的妙。講完,面子卻還磨不開,便說,去找老夫子玩的時候要安靜點,不要跟攆雞似的;老夫子說話也要好好聽著,不能梗著脖子老挑毛病。
我從菜園子里撤退,去了外公家。外公他們打長牌、摸骨牌的時候,我去收取輸了的人的玉米粒或者花生粒。超過100粒我就數不清了,有時他們笑我,我就干脆一把抓了“籌碼”吃到嘴里。他們也卜卦或念些書,我一聽就困,真沒有在菜園子里捉蟲自在。
6
我正式上學后,就不在爺爺的菜園子里擔任職務了,鄰家新長成的雞便只能在老貓的嘴里聽到我那些強悍的江湖傳說了。老貓去世后,江湖傳說也失傳了,雞們又開始撲騰。爺爺干脆將樹籬挖了,做成和別家一樣的竹籬笆。
一如時光,初始是青青綠綠,櫛風沐雨,慢慢地變成了暗黃,再風吹日曬,變成了疏疏落落的一片黑色。
不過陽雀花樹沒被挖掉,開花時,仍是黃燦燦的。
7
爺爺說他小時候缺食物,就吃陽雀花,那么多植物吃過來,就它的味道好些。
他大約是真心喜歡它的,他去世前夕,有一天問他想吃什么,他說,陽雀花。
那時陽雀花的花期已過,菜園子里的那一株早就開敗了,后來去了山里頭,找到還沒有完全凋落的摘了幾把回來。洗凈切碎,和了雞蛋調勻蒸熟,端給他,他吃了一口,說不是那個味道。爺爺以為這就是最好吃的,可不是小時候的那個味道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味道,畢竟他去世已10年。他小時候的味道是90多年前的事兒了。
8
有時我會夢到爺爺,在夢里我很清楚他已去世,但還是看他在菜園子里進出,他很年輕,我也很小。我去摘樹籬上的花,摔下來,踩斷了爺爺新種的菜苗,砸死了鄰居家進來偷食的小雞崽,怕他來訓我,正著急,醒了。
那天夢到他給了我4顆麥子,說兩顆滋潤,兩顆轉彎。
醒來還記得這句,不過脫離了夢境就不知所謂了。
9
現在我在螞蟻莊園里養雞,它去別人的莊園里偷吃被發現,揍它會隨機掉落飼料,所以它通常都會挨揍。每次它挨揍時,系統就會在首頁發一條提示,說“主人,有人揍你的雞”。
想一想,這完全是小時候我逮住雞去換糖吃時另一方立場的申訴。
可惜螞蟻森林的樹種里,沒有陽雀花,不然我還能建一個菜園子,栽一株,一有雞跑過籬笆,它就開一樹黃燦燦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