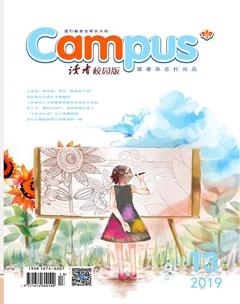蒲,暗夜的紅燭
馮杰
因植物命名,我所住的長垣這個地方曾經叫“蒲”,古代曾是衛的附屬小國。我搬著地理書不完全統計過,歷史上以“蒲”起首的地理符號有24個,長垣這里也算一個。先伸出一枝蒲。
在我的印象里,北中原的蒲大多在水中如約而至,是一種比夏夜月光都要柔韌的鄉間野草。平時靜靜立在水中,有點近似無數條修長的鶴腿,偶爾出來,就在端午節門前與艾枝并列掛著,斬一下看不見的小妖,便又急急回到水中。
我們那里說的“蒲席”,就是用蒲草葉子編的。我看到書上竟引申為“出身貧寒”。我姥爺在鄉間黃昏里講《三國演義》時,說劉備就是編蒲席出身,和我們村的那些編席匠人一樣,只是我們村里人沒有劉備“雙耳垂肩”的怪相,只能編一輩子蒲席。那一刻,我就準備如果考不上大學,就也去編蒲席,待日后一有風云,也有出息。
我的書房里至今還有一方鄉下姥娘編的蒲團,平時在上面心無旁騖地打坐、讀書。讀到陳眉公在《小窗幽記》里的一句“蒲團令人枯”,我一怔。蒲團思想簡潔。
“蒲棒槌”是我知道的菖蒲的另一個好處。在鄉間,我們的手指有時不小心被鐮刀割破,就取下“蒲棒槌”上的茸毛,按在傷口上,用以止血,效果極好,可以媲美著名的云南白藥。我還見到村中有人在秋后把“蒲棒槌”裝到枕頭里。我便好奇地問其緣由,答曰:“清腦。”
近幾年一到晚秋,在舊日的“蒲國”,我都要帶著孩子去一次黃河邊的濕地,去采割菖蒲,晾干后插到瓶子里,造一屋的清氣。獨坐之時,看到在暗夜的月光里,它們像擎起一叢一叢的紅燭,點燃了月光,一棵菖蒲,能在自己的光焰里睡去。
到了冬天,它會誰也不告訴,然后化整為零,飛翔,把細小的種子扎進另一片濕地。
少年時代,我從父親藏的一冊舊唐詩集里看到,菖蒲入詩。從唐詩里抽出的菖蒲很多,它們都一枝枝地從律詩或絕句的邊上斜斜抽出,盡管五顏六色,也極好鑒別。杜甫抽出一枝是綠色的,叫“細柳新蒲為誰綠”;白居易抽出一枝是青色的,叫“青羅裙帶展新蒲”;張籍抽出一枝是紫色的,叫“紫蒲生濕岸”……我都移栽到紙上過。
在屈原的道德標準里,菖蒲與野艾,可是有香草香木與惡草惡木之分的,雙方屬截然不同的兩個階級;到北中原,它們竟被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一下子都捆在一起,結成“端午同盟”。
我那一枝是曬干的,這么多年,高掛在門楣上。從現代回望古典,我的蒲在后面看著前面唐代的蒲,看著漢代的蒲、晉代的蒲,它面不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