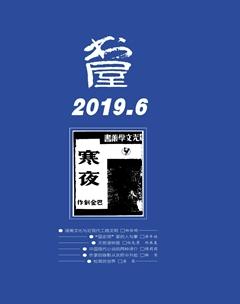人生苦樂皆陳跡
王澄霞
一
《盛氏家族·邵洵美與我》一書,是盛佩玉女士從七十歲開始動筆撰寫的回憶錄。盛佩玉系出豪門,其祖父即是著名的政治家、實業家兼慈善家,譽有“中國高等教育之父”的“清末首富”盛宣懷。而其丈夫邵洵美既是晚清政治家、外交家邵友濂之孫,又是盛宣懷外孫、盛佩玉四姑母之子,一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曾經頗受爭議的“唯美—頹廢派”代表詩人。
《盛氏家族·邵洵美與我》是一部個人口述史,作者盛佩玉按著時間流程,記錄她人生歷程中遭逢的重大事件或記憶深刻的人和事:四歲時對喪父之事的朦朧記憶;三年守孝期滿后父親諸多姨太太(包括自己生母在內)的被遣經過;“我”被交由大娘(父親正房)撫養后的生活日常;祖父聲勢浩大的喪葬過程及其間停靈、守夜、守孝等煩瑣禮儀;與邵洵美戀愛結婚的前后過程;邵洵美的文學創作、辦書店搞出版以及社交活動;生育九個子女的甘苦喜悲;抗戰、內戰期間的逃難奔突;1949年前后特別是十年浩劫期間的人世磨難和家庭變故,喪母、喪女和喪夫之痛接踵而至,全書止于“文革”結束后日趨平靜、簡單的晚年生活。
筆者以為,這部回憶錄以女性視角觀察世界,表現女性自身對生活的獨特感受,屬于典型的女性寫作,它呈現的是一個女性眼中的盛氏家族。這與有著“私人檔案第一藏”、“中國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寶庫”之稱的“盛宣懷檔案”顯然不同——宦海沉浮、商海角逐或朝廷權位更迭,這些盛氏家族的立身之本,哪怕是食指浩繁的生活開支,她并不了解也不關注。所以整部回憶錄聚焦于戀愛、結婚、生兒育女;家族女眷命運、游園購物、人情往來等家庭事務和生活日常,也是作者興趣所在。譬如,年過四十便病逝的父親:“他要了六個太太,還老是出去尋花問柳,不老而夭,是自己找的呀!”而五位姨太太得為他守孝三年后才被允許自尋出路;六姑母因婚姻不幸而精神失常,只得重又寄居娘家;五姑母、七姑母“為爭自身權益勇敢地跟兄弟們訴訟法庭”。男女不平等,居然連佛門和地獄都概莫能外,即使身為名門之女,對此也不能不感慨萬端:“女香客寫上‘×門×氏,男家姓寫在門字前面,女家姓寫在‘氏字前面。女人不寫自己的名字,連廟里都男女不平等。”“還有一種花樣叫作下‘血湖池,因為女人身上生孩子時有血,死后要進入‘血湖池中受難,所以在做七時要孝子為母親盡孝。……我們在廟中看到地獄世界的圖畫上,有些鬼上尖刀山,受火刑、磨刑,下‘血湖池受難。陰間閻王永遠在任上,他也永遠是男的,而女人比男子多一刑罰,男女永遠不會平等!傳統下來如此,女子生孩子就夠痛苦了,死后還要被他們做出這些花樣來,請問閻王你想過沒有?”
對丈夫的諸多朋友,這位邵家主婦筆下均以外貌勾勒為主:“外國音樂家派棲……矮胖個子,穿了白襯衫,外穿一套黑色‘燕尾服,活像一只‘企鵝。”梅蘭芳先生“穿了西裝,神采豐艷,在臺上可算一位佳人”,郁達夫“很瘦,削臉,高顴骨,小眼”。泰戈爾“身材高大,灰白的大胡子散在胸前。他穿著灰色的大袍,一頂黑色平圓頂的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在頭上,好像我看到過的大寺院中老方丈的打扮。老人態度嚴肅慈祥……他們的談話我不懂,覺得不是很流利”。而對年輕的同性,目光中更多了一份挑剔和審視,她筆下的項美麗“身材高高的,短黑色的卷頭發,面孔五官都好,但不是藍眼睛。靜靜地不大聲講話。她不瘦不胖,在曲線美上差些,就是臀部龐大”。王映霞“身高,體壯,尚文雅……我不大喜歡與她交談”。陸小曼“穿了一件粉紅衣,身材不高,瘦瘦的,不笑時還算美,笑時微露虎牙”。至于這些友人各自有著怎樣的專長或實力,作者未作簡單交代。
女性特有的眼光、口味、興趣和心理貫穿整部回憶錄。如觀看文明戲或話劇“看完后也不明白,根本沒進我腦子”。但是演員的行頭或裝扮,她卻眼不錯珠仔細研究:“皇后的那件披肩,大而長,拖在地上,全用銀鼠皮加上小黑貂皮尾巴做的,一頂皇冠也像真的閃閃發亮,是用白的水鉆加上幾粒紅寶石鑲制成的。”戲院包廂里某個交際花的穿著、長相、嵌了金剛鉆的牙齒乃至她臉上的刀疤及來由,作者都記憶清晰并詳加記錄。抗戰時期某些漢奸的闊太太如何在“打扮方面‘別苗頭,首飾方面勾心斗角地換花樣”,作者自然也是津津樂道:“衣服漂亮不稀奇,一粒大鉆石還算不了,要一套頭鉆石戒、鉆石耳環、鉆石別針、鉆石手鐲。或者要藍寶石的一套,或者是翡翠的一套……到戲院里看得到的。”洪深導演的《少奶奶的扇子》一劇能被提及,歸因于令她“既心痛又后悔”的深刻記憶:就是在觀看該戲時吃冰糖山楂,弄臟了一件心愛的藍緞子白紗邊新衣服。由是觀之,戲院或劇場,實為女性魅力的競技場。相形之下,舞臺上的劇情、演技、編導水平,她們根本無暇關注!這可真應了吳地諺語“看戲看的賣甘蔗”了!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對自己的容貌乃至笑容、眼神,作者顯然興趣濃厚,所以不厭其煩多次描繪:“我家親戚朋友中認我是唯一的美人,大家都關心我。”“我的笑原是很討人喜歡的。人家說我眼睛‘花,來奉承我。記得有次在外國照相館拍照,外國攝影師也贊美了我的眼神,便想攝出這種獨特的眼神來,照了好些特寫鏡頭,未成功,大約是燈光照明技術上還達不到理想效果。”“(密姬)有一次和我去拍了兩個人并肩的照片。在外國人開的一家照相館內拍的,攝影師是外國人,見我的臉覺得別致,特別是一笑的神態,他要攝出此神態,這可是我第二次遇到這種情況了。可是每次拍后沖出來,總感到不理想,大約是燈光打得太強,明暗對比度不夠之故吧!”“那些長輩們見到我總是喜歡輕輕拉一下我的手臂,叫我回頭看看。我心中有數,報以一笑,如她們的愿,她們說:‘茶寶一笑真像一朵茶花。”“我的生日在冬天,所以在秋天我提前去拍了照片,秋天衣服穿得少,可以照得好看些。這次的確照得很漂亮。我印了十吋的各兩張,兩個式樣的,馬上配了鏡框掛在墻上。”
另一個佐證是,書中寫到抗戰期間全家四處逃難,要將一些實用又笨重的家什暫存大麻子劉質夫家:“當他見到我時對我說:‘洵美嫂,我早就認識你的,在你還是小姐的時候,在新世界里,你真漂亮,我盯過你梢。你看到我嗎?我也答了:‘怎會不看到你呢?你有這樣的特征啊!”諸如此類的細節其實并無多少價值。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對這個大麻子盯梢者,盛佩玉女士不僅毫無厭惡或反感,反而將他作為自己昔日美貌的證人,載入盛氏回憶錄。女性對自身姿容的無限興趣及其自得自戀心理,此中一覽無遺。
二
邵洵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卓有影響的詩人、作家,同時又以出版家和西方文學翻譯家知名;既有“海上孟嘗君”之美譽,又被魯迅譏為“捐班作家”;因其曾經多次卷入現代文壇的流派紛爭和人事糾葛,以及“唯美—頹廢派”詩人的標簽,因而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現代文學研究中,邵洵美長期處于邊緣地位,他在中國二十世紀文壇上的活動與貢獻,未能得到公正的評價。
這部回憶錄的文學史價值,在于全面呈現了妻子眼中的丈夫邵洵美形象。
盛、邵的婚姻雖屬傳統的姑表結親,但兩人有情感基礎,系自由戀愛。按回憶錄所言:“我是屬蛇的,直到很久以后,我讀了洵美寫的《偶然想到的遺忘了的事情》才明白了我們早就有緣分”。“洵美追求我,從名字上就知道了。因我名佩玉,他就將原名‘云龍改為‘洵美。意取《詩經·鄭風》中《有女同車》‘佩玉鏘鏘,洵美且都之句。”于此也可見出兩人當時的熱戀情形。
盛佩玉沒有受過完整的現代教育,當年只是跟著家庭教師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礎。所以,邵洵美的才學、風采令她無比欽慕和欣賞,這在回憶錄中隨處可見:“洵美給我的印象是個聰明的人。文字好,人長得并不俊,長臉,身材矮了些。家里人說他七歲就能對出他外公盛杏蓀的對子。”留學劍橋時的邵洵美“穿著英式的高級西服,雙手交在腹前,很有紳士風度”。“洵美懂的事很多,學貫中西”,他二十多歲就到光華大學幫徐志摩代了一兩個月課,為此“特地去配了副金絲邊平光眼鏡,穿上長衫,活像一個大學教授”。妻子眼中的邵洵美愛好廣泛,“但他最愛的就是書。外文書很多,不講究是否精裝,故書架很多,放滿了長長短短大大小小沒有排列整齊的書。中文他還能寫,小時候家中練帖,他喜愛的碑帖有張黑女碑,也愛清何子貞的書法”。因此,盡管當初娘家男性朋輩反對這門親事,但“我”依然心志堅決。
邵洵美是當時上海文藝界和出版界非常活躍的出版家。詩人卞之琳在《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三期撰文《追憶邵洵美和一場文學小論爭》,曾如此評價邵洵美對出版的癡情,說他“賠完了巨萬家業”卻始終“衣帶漸寬終不悔”。盛氏回憶錄中就詳細記載了邵洵美廣羅人才“興致濃厚”搞出版的全過程:
文藝家們每天碰頭,洵美說:大家要尊重藝術,提高興趣。意氣相投,以致他們經常圍了一桌有說有笑,一面開動腦筋孕育出杰出的作品。這段時間里,洵美除了印《生活周刊》、《良友》外,自己先出版了《時代畫報》半月刊,由張光宇、張正宇、葉淺予、黃文農編輯;繼而又出版《時代漫畫》,由魯少飛、王敦慶編輯;另有《時代電影》,由包可華、席與群編輯;《時代文學》,儲安平編輯;《萬象》,張光宇編輯;《人言》周刊,邵洵美、顧蒼生、周壬林編輯;《十日談》,章克標、郭明(即邵洵美)編輯。此外還出版了巴金、張資平、沈從文、廬隱等作家的自傳。
在這些刊物上,洵美陸陸續續也寫了不少作品。有詩,也有雜文、短評、隨筆之類,他的筆名有浩文、紹文、邵浩文、郭明、逸名、邵年、閑大、初盦、荀枚等。
盛佩玉還記錄了1978年以后,施蟄存、秦瘦鷗、孫斯鳴、曾虛白先生等諸多友人對邵洵美的回憶,如秦瘦鷗在《從紈绔弟子到翻譯家》(上海《文匯報》1986年10月8日)一文中寫道:
我最初是在魯迅先生雜文中見到邵洵美這個名字的。
在《登龍術拾遺》一文內,魯迅用四句話對邵下定評:“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陪嫁錢,作文學資本。”
因此一般人都認為邵是一個依仗老婆有錢而舞文弄墨的紈绔子弟。
三十年代末,我在很偶然的情況下,巧遇邵洵美于美商中文《大美晚報》編輯部,發現他眉清目秀,長發隆準,儼然是個美男子,他穿的服裝質料高級,但并不成套,衣領和紐扣都不扣上,顯出一副落拓不羈而又很瀟灑的氣派,態度倒還平易近人,并不像一般貴家公子那樣目空一切。朋友們還說邵寫的詩很優美,外文水平也不低,譯過希臘女詩人莎弗的名作。
至此,必須提到1933年8月魯迅寫的兩篇雜文《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平心而論,魯迅先生目光如炬用筆如刀,但難免也會失察和意氣用事。如今看他對邵洵美的評判,就有失客觀公正:“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學者文人也不會折本……這又叫作‘名利雙收。不過先要能‘投資,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學士也就不大值錢了。而現在還值錢,所以也還會有人忙著做人名辭典,造文藝史,出作家論,編自傳。我想,倘作歷史的著作,是應該像將文人分為羅曼派、古典派一樣,另外分出一種‘捐班派來的,歷史要‘真,招些忌恨也只好硬挺,是不是?”“術曰:要登文壇,須闊太太,遺產必須,官司莫怕……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陪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隨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頭銜自來,贅婿雖能被婦家所輕,但一登文壇,即身價十倍,太太也就高興,不至于自打麻將,連眼梢也一動不動了。這就是‘交相為用。但其為文人也,又必須是唯美派,試看王爾德遺照,盤花紐扣,鑲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見猶憐,而況令閫……所以倘欲登龍,也要乘龍,‘書中自有黃金屋,早成古話,現在是‘金中自有文學家當令了。”
魯迅比邵洵美年長二十五歲,靠教書、寫作維持大家庭生計,畢生經濟負擔沉重;婚姻上雖與許廣平自由戀愛定居上海,但在北京畢竟還有“母親給我一件禮物”、名分上的妻子朱安他得“好好供養”。所以,洋裝少年邵洵美含著金鑰匙出生,情感上春風得意,外表又風度翩翩,堪比當下所謂的“高富帥”,魯迅對邵是否因此“羨慕嫉妒恨”?
盛佩玉在給秦瘦鷗的回信中,對秦先生用“落拓不羈而又很瀟灑”形容邵洵美的神采,表示贊賞表示感謝,另外也對魯迅當年的譏誚做了回應或反駁:“寫文章者一支筆下,有褒有貶,您提到魯迅的四句話,將洵美下在貶之中。他是見多識廣者,難道不懂,人之結為夫妻,便是共同生活。丈夫成家立業的基礎是要用錢。開了個小小的書店,他是知道的,也是可以的。這可以算是正當的作為吧!可被他貶為‘作文學資本,何必如此小題大做。句子也顧前不顧后。”
三
盛佩玉作為妻子,對丈夫可謂時時處處都維護有加。經濟上的全力支持自不待言,“我每次聽到他提出的要求只要是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事要花筆錢,我總會全盤接受。”盡管這位金枝玉葉其實也有捉襟見肘之時,就“只有將我的首飾拿到當鋪里去作押,以后便可再透支”。“洵美的事情多,他出去衣服等都要我漿洗燙平,胡子、頭發也要我端詳。他的胡子是小八字式,總是要我為他剪,因為胡子是一面厚,一面薄,要用小剪刀修得一樣薄,鬢角要一樣高低,哪怕是到理發店去理好了發,回來依舊要我修一下。中裝里里外外都由去我去做,連皮鞋尺寸也只有我知道,由我去買。只有西裝量尺寸他才不得不親自去西服店里走一趟”。一生生育了九個兒女,以家庭主婦為主業的這位大家閨秀,對丈夫體貼照顧可謂無微不至。
寫到丈夫的情人、美國著名雜志《紐約客》特約記者項美麗(Emily Hahn)時,盛佩玉用筆非常謹慎節制:“她和我是同年的,我羨慕她能寫文章獨立生活……我對她印象很好,她也一見如故。洵美懂的事很多,學貫中西,她找到洵美這條路是不差的。”回憶錄中寫了他們一家與項美麗的互相幫助,邵洵美幫助項美麗聯系采訪、收集和翻譯資料,使她順利完成其重要著作《宋氏三姐妹》;項美麗則利用其美國公民身份,在戰火中幫著邵家將價格昂貴的“印刷機”轉移至安全區。有些文章認為舊式家庭出身的大家閨秀盛佩玉對邵洵美項美麗的婚外情“從不拈酸潑醋,而是和睦相處”。其實,作為妻子她當然苦衷難言,不過表露得比較含蓄委婉罷了。試看這段文字:“項是單身女子,自由得很。洵美,我又不好不放他出去,我應當要防一手的。因此我向洵美提出抗議,我說:‘我不能跟著你走,你不能放棄對事業的管理,也不該對其他朋友疏遠交往……現在我只有這種辦法,下這個警告給你,如果夜里過了十一點你還不到家,那么不怪我模仿沈大娘的做法,打到你那里去。所以他記著,不敢誤卯。沈大娘是一戲中人物,為挽救婚姻,打上門去怒斥第三者。”
這種警告背后,透露出多少無奈和痛苦!盡管與邵洵美婚前有過約法三章,但是盛佩玉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吸煙、娶妾是那個時代的風氣,我家可以講像傳染病一樣的盛行。叔叔們還自我解嘲說:‘我們風流不下流。為自己的行為辯解。”這種家庭氛圍,恐怕也是她能夠容忍或接納丈夫情人的一個原因吧!即便如此,她還處處為丈夫開脫:“洵美和我過的日子是窮而又煩躁的。生病!添孩子!弄得他腦子不得安靜……其實他是一籌莫展、愁悶在心,才會這樣子的!”
朋友兼辦刊合作者的章克標先生則認為:“我覺得洵美一個人有三個人格,一是詩人,二是大少爺,三是出版家。他一生在這三個人格當中穿梭往來,盤回往復,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調和,因之,他這個人實在是很難以捉牢的,也就是很難以抒寫的。”這不由讓人聯想到,盛家叔長們當初并不贊成這門婚姻,理由就是他們認定“洵美是滑頭”,這倒與章克標的評價似乎存在某種暗合。
回憶錄中,即使面對家產被強行沒收、丈夫無辜而入獄,居委會得寸進尺的支使盤剝,盛佩玉從未出過惡聲。她的溫婉性格和中國傳統女性的良好教養,在“說勿清”、“弄勿懂”、“辦勿到”、“救勿了”、“來勿及”、“天勿亮”、“寫勿靈”、“很厭氣”(很難受很吃力之意)等等吳儂軟語中,都可見出一斑。丈夫出軌,家庭經濟每況愈下,在今天都足以導致夫妻交惡婚姻破裂。因此,盛佩玉這個新舊觀念兼容并包的大家閨秀,著實有其令人欽敬處。
盛佩玉的顯赫出身,還賦予了這部口述史另外一些特別意義。首先,它是中國晚近以來一代名門望族興衰變遷的生動見證。隨著盛家長子、“我”父親的早亡和祖父、祖母的相繼離世,為了爭奪“兩千萬兩銀子的遺產”,兄弟勃谿對簿公堂;叔父和哥哥忙著娶妾玩樂;守成無望,特別是七七事變后抗日或媚日的家族裂變,煊赫多時的“清末首富”已然“屋倒瓦散”。
其次,它也折射出晚近以來“冒險家的樂園”——上海的現代都市化進程。譬如,交通工具由馬車、輪船而火車、電車和私家汽車,電燈、電話、照相機漸次進入滬上大家;跑馬廳、跑狗場、輪盤賭場、體育館到高爾夫球場,新世界、大世界、電影院到舞廳和西餐館,競一時之秀;從全日制寄讀學校到“讀古文,念英文,音樂、美術、體育并重”的世界學校、“中西女中”和“光華大學”、“大同大學”等等,教育機構日趨現代完備;上海以海納百川的胸襟,迎接世界各地的文人墨客俊秀豪杰,在音樂會、戲院或文藝沙龍交游往還……
回憶錄中還披露了一些文壇舊聞,譬如,徐志摩、陸小曼夫婦1929年3月接待第二次到訪的泰戈爾時,老人要求住在主人家的中式臥房,結果夫妻倆原先專門為他精心布置的印度式房間,只能留給他們自己住。還有,當年徐志摩因欽佩丁玲女士的勇敢,故“寫了短篇小說《珰女士》發表在《新月》第五卷第十一期上”。徐志摩出事后,邵洵美先在《人言》周刊發表《徐志摩的〈珰女士〉一文》,后又親自“續編”了當年徐志摩這篇一萬多字的未完稿,在《人言》“一氣連載了三十期”,表達他對這位摯友兼師長的無限懷念。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變幻的風云,在這位名媛家長里短、衣食住行的敘述間隙,也不時飄過。
作者在“楔子”中申明:“我今年已經七十歲了……我的親人們,我記這些,絕不是留戀和夸耀富貴之家,為的是在我腦子還清醒時,分辨好壞。”人生苦樂皆陳跡,往事紛紛何足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