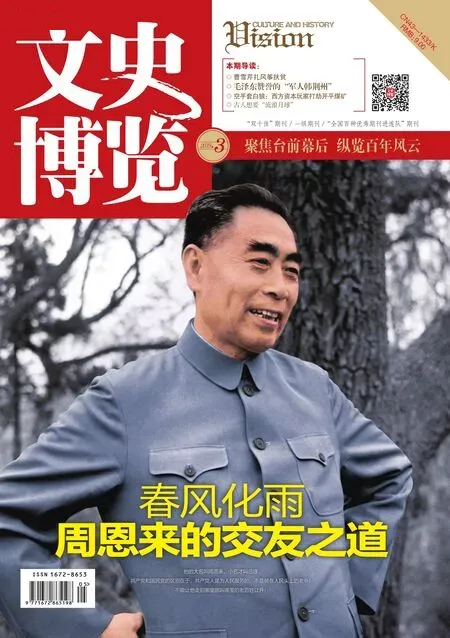我給江青當了一年秘書,關了七年半監獄
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我正好給江青做了一年的秘書。有人問我:“后來怎么失寵了?”其實,我從來就沒有被“寵”過。
女演員的一封信
1967年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轉給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個電影制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來的。信很長,有十幾頁,上萬字。我因為忙,不斷地收發文件和接電話,對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幾次看完的。信中,這位女演員講了她的從藝經歷,說她也曾經叫“江青”這個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說,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為黨費交給組織;再說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沖擊,以及贊揚江青等等。
這個女演員寫信來無非是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以減輕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沖擊。可我以為寫信的人會和江青有什么關系,怕處理錯了,負不起責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張條子送去。我是這樣寫的:“江青同志: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說,這人是不是與您有什么關系——當然,這是我誤會了,這位寫信人以及她寫的內容和江青根本沒有什么關系。可我萬萬沒有想到,一場滅頂之災由此就降到我頭上。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會議室,當著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著臉,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厲聲責問我:“為什么要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么?”我嚇呆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低頭一看,原來是這封信不該送給她。我膽怯地說:“我怕來信人和您有什么關系……”江青怒氣沖沖地說:“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沒動過窩?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來看看!”
在江青嚴厲斥責后,我確實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說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文藝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漢、重慶,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屬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沒講到她的名字。
盡管江青嚴厲地斥責,但我心中無鬼,所以并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對我的態度卻變了,一個星期不按鈴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發文件。這期間,恰好楊銀祿又回老家奔喪了。1968年1月8日晚,楊銀祿奔喪歸來,第二天上午我即領著楊去見江青(楊還未單獨見過江青)。我報告說:“江青同志,楊銀祿同志回來了。”江青沒好氣地大聲說:“他回來了,你還上來干什么?你馬上把文件清點給楊銀祿同志。”我只得沒趣地離開了江青辦公室。
就在這一天,我向楊銀祿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點鐘,陳伯達、汪東興找我談話。陳伯達說:“你是搞文字工作的,還是回辦事組工作吧。”汪東興說:“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續,這是工作人員離開首長身邊時的規矩。”汪東興讓我收拾一下自己的東西,然后把我送到釣魚臺警衛連連部。在路上,汪東興很和藹地對我說:“你沒事,你的檔案我都看過,你是我挑來的。”我也很坦然,認為自己既沒歷史問題,也沒現行問題,表示不怕例行手續。送到警衛連連部,汪東興就走了。
從此,汪東興再也不來了,直到“文革”后汪東興告訴我:江青后來不讓他管我的事了。
淪為“階下囚”的日子
1968年1月9日,我淪為“階下囚”,這一天對我來說終生難忘:一年前,我隨戚本禹來到江青身邊時也是1月9日。
在警衛連開始幾天,雖被看管,但并不知道自己要反省,就開始讀《毛選》和歷史書,心想不叫當秘書,就回去搞我的歷史研究嘛。反正當秘書也不是我要來的,而是組織上分派的。
大概是我被隔離的第三天晚上,陳伯達和姚文元、謝富治來了。陳伯達問:“你在干什么?”我說:“在看書。”陳伯達操著濃重的福建口音說:“你還看什么書啊,要深刻檢查自己的問題。”接著又慢慢地說,“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是壞人……”把這三個人連在一起并稱“壞人”,我是第一次聽到。這時姚文元立即指著我補上一句:“你就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我一聽這話,腦袋炸了,這不把我看成“特務”了嗎?
當時,我還沒有想到會坐牢,心想,我這樣一個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驚動黨、政、軍三方這樣重要的人來找我?我只覺得頭在嗡嗡作響,不知說什么好。這時謝富治對我說:“江青同志對你不錯嘛,你應該有什么問題就交代什么問題……”我也沒怎么聽清,只模模糊糊覺得他是勸我老實交代問題,我連連點頭說:“好,好,我有什么就交代什么。”接著,陳伯達又讓我按照他的口授,給我妻子寫了一封信:“XX: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現派人來取回。你們住的地方,按照組織的安排搬到XX……”
第二天,我被告知:“給你換個地方。”這一換,我就被換到秦城監獄去了。
監獄是殘酷的。列寧在沙皇的監獄里能寫書;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監獄里也能寫書,如方志敏就寫了《可愛的中國》。而我被關起來,開始書、報都不給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著。
為了打發時間,我就翻來覆去數床頭暖氣罩上的孔兒,1、2、3、4、5……我后來找到一種消磨時間的辦法,就是反復背誦熟悉的毛澤東詩詞以及唐詩宋詞,同時自己也學著做詩——也許不能叫詩,只能叫順口溜,因為我不懂平仄格律。這順口溜我做了很多,我把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都編成了順口溜。
關于《矛盾論》的順口溜有一萬多字,可現在不記得了;關于《實踐論》的有兩千多字,因為出監獄后追記下來,現在還保存著,如開頭幾句:“人的思想哪里來?馬列主義有言申,不是天公憑空造,亦非腦中自相蘊……”如果當時把這些順口溜都記錄下來,也許還有點意思呢。
在秦城監獄待了七年多,我最渴望的是提審,因為提審可以與人對話。1975年5月22日,專案組來到監獄,突然對我宣布:“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釋放你,送你到湖南某農場勞動,等待結論。”這個決定對我連念了兩遍。當時,我特別高興,也不管到遙遠而陌生的湖南某農場勞改是什么滋味,因為我終于可以跨出牢籠了。
在農場生活近五年后,我的案子方才被轉到中組部,中組部又把案子轉到紅旗雜志社。1979年9月,紅旗雜志社黨委終于給我“徹底平反”,并決定將我調回紅旗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