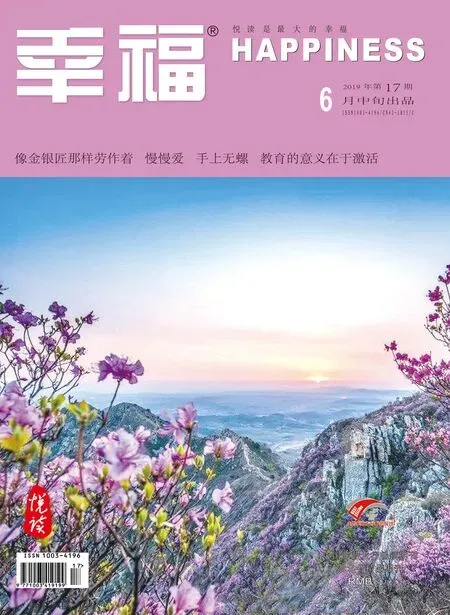栽樹
文/南在南方
祖父一輩子喜歡栽樹,清明上墳要給栽幾根小柏樹,蒼松翠柏,墳園怎么看,都簡靜貞寧。
至于門前屋后,他栽野梨樹,野李樹,柰樹,長三兩年,去別家剪了雪梨枝甜李枝蘋果枝,回來嫁接,有些當年就能掛果,著實可喜。果木樹里頭,櫻桃樹的確難栽,祖父栽了許多年,總算是栽活了一棵,一樹的花,他高興,一樹的櫻桃,他也高興。
至于平時要用的木材,山上也有,總不如手植用得順手,紅椿樹是首選,肯長,標直,十來年就能當頂梁柱了。
我小時跟著祖父栽樹,只是栽樹,等到有一天,我忽然想著自己要栽一棵樹,不要人幫忙,自己找樹苗,自己選地方挖坑。
是棵紅椿,就栽在院壩邊上,一年一年過去,長高長粗,仰著頭看,樹梢上頭有個喜鵲窩,兩只鳥兒,飛來飛去,有一只它們飛下來啄曬著的棉絮,用力啄下去,使勁擺腦袋,嘴里一團白,飛回窩里,不久,就有小喜鵲的喳喳叫聲,嫩嫩的綠綠的樣子……
日子是一天一天過的,只是回過頭,有點浮光掠影,好像我們吃化肥似的長大了,開始背井離鄉,可老家的景物,卻像是栽在腦子里,從來沒有如此清晰。那些樹,和它們的枝葉,像是跟著我,經過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
總是要回老家,像是得到了巨大安慰,其實有許多傷感,比如祖母離世,新鮮的墓地,我們栽樹,除了柏樹雪松,一架刺玫……我忽然從屋后移栽一棵木瓜,這棵木瓜是幾年前我從六十里外二姑家扛回來的。我后來跟二姑說了,二姑流眼淚說,栽得好呀,就像是我陪著一樣。是啊,是一棵木瓜,也是一份心意。
不幾年,祖父離去,好像除了栽樹,我們沒有別的辦法來面對那些潔白如新的石頭,好像那些小小的綠樹能夠打扮傷感。
許多路走著走著就沒法走了,可是看著樹,那些祖父栽的樹,好像他回來了。他去世時,那兩棵栽在一起的白蠟樹還只是茶杯粗,十年之后,這兩棵樹神奇地長在一起成了一棵樹,四季常青,站在路口……
父親花甲時,請木匠做了壽枋,這是個講究,從此往后某天不在了,就是壽終正寢,做壽枋像是志賀。
我們坐在院子里,一只鳥飛過去,我抬頭看了看,看見了我小時栽的那棵椿樹高入云端,如今兩個人合抱都抱不住了。
我問父親,這棵樹等我老了,做個棺材,夠不夠料?父親抬起頭看,一截一截地看,他會木匠活兒。父親肯定地說,夠!說完這句,父親笑了一下說,你還小,不該問這個話嘛。
有一天看余懷的《板橋雜記》,它寫明末秦淮河的脂粉人物,其中有一位李十娘,有女兒叫媚姐,當時相處甚洽,兵禍一來,物是人非,多年之后,遇到媚姐。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為菜圃。”問:“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為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
已不是人是物非,而是人非物非,讓人唏噓不已。
后來,我不止一次想著這棵紅椿,我不能確切它將來會做成什么,只是每次看著它,它更粗了,蒼黃的樹皮開始裂開,時間的味道出來了,想起一些有關樹的詩,像庾信的: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想起曹操的: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想起蘇東坡的:明月夜,短松岡。這短松是他手植的,他千里扶靈回到眉山,守孝三年,栽了一千多棵松樹……
時間深情,祖母祖父的墓地已經郁郁蔥蔥,雪松如蓋,刺玫爬上樹頂,看上去像是個小小的花園,這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想起栽樹,想著落葉歸根,好像有點頹敗,其實恰好有一點興味,那些葉子長了,然后落在地上,有點像送還,人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