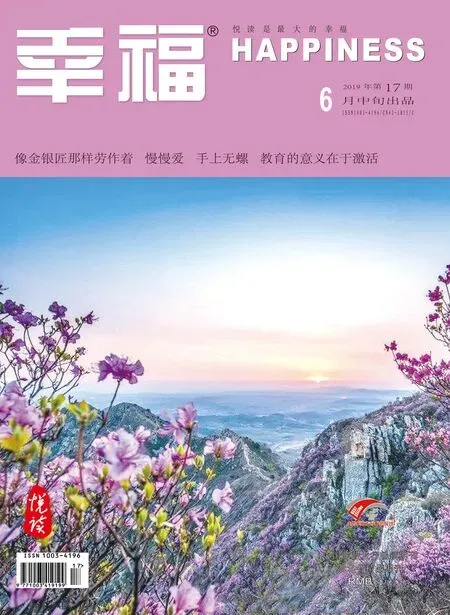像金銀匠那樣勞作著
文/劉建農
任蒙在《詩廊漫步》中說:哲學極力用“概括”的抽象去包羅“個別”,詩卻極力用“個別”的形象去反映“概括”。理論的終極目標是來到實踐者的手中,藝術的終極目標是走進欣賞者的心靈。
翻開這本書,其目錄的精美鮮活,首先吸引住你的眼球,如“詩是生活中最絢麗的色彩”、“詩人像金銀匠那樣勞作著”、“敏銳的眼睛比靈巧的筆更重要”、“靈感,是對‘能源’的點火”、“有多少詩人就有多少條詩的道路”。有的是對詩歌個性內涵的精確解讀,有的是對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學形式共性的獨到見解。
任蒙從什么是詩、詩的形象、語言、結構、詩人的靈感、精神素質、詩人與讀者的相互關系等多方面,闡述自己獨特的創作觀和審美鑒賞理論。
把詩歌小心翼翼地解剖開來,每個字都力求精準、每個詞都仔細拿捏。美、色彩、形象、能源、想象、敏銳、靈感、含蓄、朦朧、風格、個性、概括、讀者……一組跳躍的文字魔方構成了詩的“蒙太奇”。任蒙希望將這些代表詩人性格的文字演繹成哲人的語言奉獻給讀者,并以此證明自己的結論——“詩人,也是哲人!”
書中深入淺出、形象生動的表述,給人聯想和領悟,這大概是讀鴻篇巨制時難以得到的。
“詩是什么?怎么寫詩?”這是詩歌入門級的問題,也是詩歌中最難解答的問題。看似很初級、很淺顯,實際上有很多著作等身的人,也未必能說清。
任蒙在書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版面,分四個部分,重點探討了“詩是什么”的問題。“把人們都能看到的真善美收集陳列出來,會令人贊嘆;把被紛雜的表象掩蓋著的真善美發掘出來,更會令人驚異。”這是作者對詩的獨到見解,更是作者對生活感悟的文字升華。詩歌之美,被作者一次次地多角度把玩,并讓讀者一次次地多角度感知。詩歌之美,被反復展示的同時,還被打開合上,并賦予了許多全新的定義和詮釋。
談詩和交流如何寫詩的文字,在我們這個詩的“高產國”里可謂汗牛充棟。但是,“光知道看守祖宗遺產的人,是最不爭氣的子孫”。
關于“怎么寫詩”,古人有太多明示猶在耳邊。宋人楊萬里說:“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說的是詩來自征行——“生活”;唐人劉禹錫認為:“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里,工于詩者能之。”說的是詩要言簡而富于想象。
《詩廊漫步》吸收了古詩論的精髓,化腐朽為神奇,以平實易懂的語言來求解學術尖端的難題。
“形象,是固定文學作品特性的質。沒有形象,就沒有詩。沒有形象思維功能的詩人,只能稱為‘鋸匠’——善于把本來應該長行的文字‘鋸’成短行。”如此這般分析、暗喻、解構“詩歌該怎么樣寫”的句子在書中比比皆是。引文至此,金人元好問《論詩》中的一句詩閃現眼前:“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任蒙對詩歌創作的解讀,不正是以“真淳”打動人,以“一語天然”的新穎視角打動人嗎?
“詩的形象來自作者對自己感覺的把握。臧克家在病中寫的‘天花板是一頁讀膩了的書’,這個‘膩’字準確地把握了詩人病中的情態。于是,就尋到了一個很貼切的比喻——書。新鮮、貼切的比喻,給予讀者的不是比喻的形象,而是被比喻的形象。從臧克家這句詩里,人們想到了天花板,想到了病人的眼神和臉色,也不知不覺地走進病房來探望了。”
“怎么寫詩?”這個簡單的千古難題,被任蒙多角度地一一解開,他甚至教會讀者掌控才情:“對于詩人,感情的隨意流溢無疑是一種浪費。還是儲積在水壩中,讓他在必要的時候,突突地涌注出來,去沖動發電機,去淘刷污穢,去澆灌良田。”
魯迅先生說:“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但是,任蒙卻偏偏找尋以“哲學和智力”見長的高手過招,以突顯詩歌的魅力。
當年,《青年文摘》以近兩個頁碼的篇幅,轉載任蒙發表在《寫作》雜志上的《詩廊漫步》。任蒙無意間將本來很枯燥的文學理論推向了這種通俗性雜志,推向了數以萬計的詩歌愛好者,可見其影響巨大。該書出版30年了,還有人在找尋、傳抄,甚至以書中的句子來教育子女為文做人。
在新詩暖風陣陣的今天,很多讀者在網絡上重提、重讀《詩廊漫步》,顯然具有更深層次的時代意義,因為詩歌是語言的皇冠,是智慧的閃電,文明中國正呼喚詩歌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