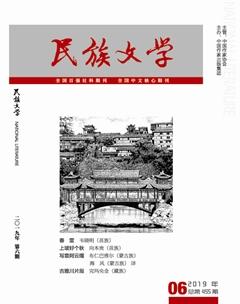百年吟誦從未遠
張愛眾(土家族)
一
回溯百年,張家界市永定區王家坪泰山廟前山風推搡,松濤如嘯。清瘦的李堯夜闌披衣而立,日間與文友吟詩潑墨、投壺燕射的情形猶在眼前。命運多舛、仕途不暢的李堯在家鄉泰山廟創辦天香詩社以來,鄰近各縣的文人墨客和社會名流從者云集。一朝浮沉,千年文事。《天香詩集》終于面世,人們爭相傳抄,一時洛陽紙貴。李堯以自己的文章道德遏止了流言譏語,開啟宏盛文風。
天香詩社十年磨卷,李堯以文入世,近天命之年中光緒丙戌科進士,遠赴云南羅次縣居官十余年。
山水有靈性,李堯他們的吟誦讓承載了天香詩社的這塊土地日益厚重。文風日盛,人才輩出,百余年前當政知府親題“九都文化之鄉”匾額,對這方鐘靈毓秀的土地著意褒獎。
二
先賢們留下的印記已成為這一方土地不可湮滅的刻痕。文化只會以一定的形式蟄伏或延續,絕不會消亡和遺失。如同冬眠的種粒培進春天的沃土,如同散亂的音符黏合美妙的樂章。王家坪,一個受困于地理偏狹、資源匱乏、勞作單一的山鄉,一直在百年文脈的旗幟下發酵、突圍、著色,從“九都文化之鄉”蝶變為“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
走進王家坪,很多思想可找到源頭,很多力量有了出處。闖進眼前的風雨橋、吊腳樓、水碾房、榨油坊,縈繞耳際的山歌、號子、漁鼓、道情,心里欽慕的耕讀習氣、淳樸風俗,在這里都被一一接納。任何一種符號都沒有陌生感和排異性,它們在田間地壟徐徐行走,在階前屋后歡快跳躍,在炊煙暮色中不停閃現。
一嗓子山歌亮開,王家坪的臉面就露出來了。歌調子是約定俗成的,詞作大多由歌手信手拈來,即興創編。站在田地里的男女老少直起身子擦一把汗水立刻就是儀態萬方的歌手。眾多的歌手血液中流淌著先祖的直率和謙遜,他們觸景生情借物喻人以事說理,他們的歌謠節奏明快,動人心弦。祝酒歌、放排歌、打夯歌、洗衣歌、哭嫁歌,盤歌、情歌、壽歌、喜歌、喪歌,氣勢豪放,表白含蓄,謙遜大方。這些歌,沒有消沉只有自豪,沒有自私只有大愛。聽到歌,節日的吉祥、豐收的祝福、團聚的欣喜突然撲面而來。
舞蹈是歌謠的天然伴侶。王家坪人都是與生俱來的舞者,他們的勞動、祭祀、休憩都是舞蹈的語言。俯仰天地,薅草敲鑼把火辣辣的太陽壓住了;舉手投足,采茶舞把嫩生生的茶葉咬住了;眉目傳情,抬花轎把羞答答的新娘娶來了。揚叉、背簍、提籃、索擔、鐮刀都是不朽的道具。這些從祖輩傳下來的肢體語言,把他們帶進了穿越遠古的熟悉場景,講述了祖先的生產生活。所有的苦難都在“哦哦咳”中消解,所有的技能都在“喲嗬嗬”中體現。舞蹈之后,他們和祖先一樣無所畏懼。
對祖先的崇拜需要記憶和藍本。一些神秘的習俗被發掘出來,并貼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標簽。高花燈、土家糊倉、土地戲、草龍燈,蔓延大地,根錯節,和莊稼一樣拔節繁盛。高花燈轉起來,竹篾和糙紙扎起五彩燈,四周綴滿了人物和故事,東起西落,進去“半邊月”,出來“大團圓”,“太極圈”“九連環”“織籬笆”,變幻無窮的陣形寓意深奧。糊倉表述著質樸、簡單、明了的愿景,綠油油的秧苗栽滿田畝,人們爭相往別人身上涂上馨香的泥土,那是互致勞動的敬意,那是關于秋天收成的祝頌。在莊嚴的儀式和優美的舞蹈中灑播良好的祝愿,堅硬的生活柔柔地軟化了。
三
單薄的風景在冷峻的注視下,會因為冷卻而遺忘。此時,文化就是一襲御寒的大氅,一脈加溫的暖流。它們相擁、互補、融合,風景開始有了聲音,有了色彩,有了嚼勁,有了念想。文化開始流動、聚合、進化。
王家坪九都文化綿長的生命力和獨有的感召力,喚起了人們內心的認同感歸屬感,眾多的人涌入這塊沉寂已久的土地,百年文淵一絲一縷清出脈絡,李堯們釋卷長吟的場面漸次還原。土地開始生動而活躍。
那么漫長的路,那么繁多的史冊,從沒有缺失文化的行吟者。或苦旅,或長隱,或傲立。詠揚情懷,嘆惋聚合,感慨風云。愈是周遭的暗淡,吟誦愈是成為一抹亮光火星。歷經千年不屈不撓不消不沉的吟哦,鑄就了內心堅韌的固守防堤和錚亮的青銅劍氣。
遠隔了千重山萬重水,一根鄉弦就穿透時空的蕭墻;面臨了堅船利炮殺伐聲近,一聲吶喊就警醒沉睡的雄獅。大至封疆固土,小到凝聚人心。總有一種深沉而厚重的沉積堅實地根植于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方土地,讓我們的時代沸騰、民族振興、土地溫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