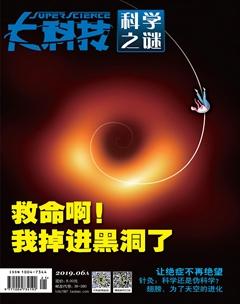讓絕癥不再絕望
穆婕
戴著眼鏡、一頭卷發、胡須凌亂的詹姆斯·艾利森看上去睿智而隨和。他是癌癥免疫療法的推進者之一,也是打破傳統的科學家,他成功為癌癥患者開辟了一條治癌新路。這條新路的開端,是艾利森那濃烈的好奇心。
好奇是科學的開端
1948年,艾利森出生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南部的一個小鎮上。他的父親是一名醫生,而母親是一位家庭主婦,他和他的兩個哥哥一同長大。
小時候的艾利森就表現得非常與眾不同,他對一切事物都充滿了好奇:為了解青蛙的內部構造,他花了很多時間解剖青蛙;他還制造小型炸藥,然后在樹林里引爆(請勿模仿);他還喜歡擺弄化學實驗用的瓶瓶罐罐……
起初,艾利森打算和父親一樣成為一名醫生,但在13歲的時候,他濃烈的好奇心引起了老師們的關注,他們鼓勵艾利森學習科學,并培養他對科學的認知和興趣。
1965年,艾利森從高中提前畢業,并前往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進行深造。在艾利森還是大學生的時候,艾利森就對免疫系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決定將畢生精力投入到研究免疫系統是如何工作當中。在艾利森的研究生時期,他做了一次特別的實驗,加深了他對免疫系統工作機理的好奇。
艾利森注意到,把癌細胞注射進小鼠體內,待小鼠長出腫瘤后,如果把天門冬酰胺酶注射到患癌小鼠體內的話,小鼠體內的癌細胞就會被破壞,腫瘤會漸漸壞死直至徹底消失。而第二次注射癌細胞后,什么都沒有發生,小鼠沒有長出腫瘤。
“第二次注射癌細胞的時候,我甚至給它們注射了10倍的癌細胞劑量,它們都沒有再次患癌,簡直是太神奇了!”艾利森說。他相信,這一定和免疫系統有著密切聯系。基于此次實驗,他認為免疫系統一定有一套對付癌癥的獨特機制。
換個角度去思考
其實,艾利森對癌癥并不陌生。在他11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就因淋巴瘤去世;15歲時,他的一個叔叔死于前列腺癌,另一個死于黑色素瘤。他親眼目睹母親和叔叔們為了對抗癌癥,承受了難以想象的痛苦。
當時有三種治療癌癥的主要方法:切、燒、毒。切是指利用手術切除腫瘤;燒是用α射線、β射線、γ射線、X線及各類加速器產生的電子束、快中子、質子束等放射線照射腫瘤,達到殺死癌細胞、消除腫瘤的目的;而毒是指用化學藥物進行治療,即化療(1946年,芥子毒氣的一種衍生物就被用于殺死癌細胞)。因為這三種方法不會區別對待正常細胞和癌細胞,會對所有細胞進行一頓狂轟亂炸,無一生還,這才導致人體出現不良反應,如化療會帶來毛發脫落、食欲不振等。
因此,這場人類和癌癥的較量從來沒有真正成功過。但現在,艾利森從不同角度出發,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方法——癌癥免疫療法,它不直接作用于癌細胞,而是作用于自身的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是人體內一種十分高效的疾病防御系統。它的組成極其復雜,有骨髓、脾臟、淋巴結和一系列免疫細胞和免疫活性物質等。雖然組成復雜,卻有著一個看似簡單的任務:找到身體里不應該存在的東西,比如細菌、病毒等使我們生病的外來入侵者,和一些已經凋亡、退役的衰老細胞,然后消滅它們。這些入侵者和衰老細胞的出現會觸發免疫系統建立免疫部隊消滅它們,進而保護人體。艾利森認為,癌細胞也會觸發免疫系統,但癌細胞很“聰明”,它進化出了一種神秘機制,使得免疫系統無法識別它。
但這樣的想法似乎遭到了許多科學家的質疑。
在質疑中前進
長久以來,許多研究人員一直無法解答“免疫系統為什么不能像對抗普通感冒那樣對抗癌癥”這個問題。而且大多數人支持免疫系統無法阻止癌癥,他們的論點是:癌癥由失控的正常細胞引發,雖然細胞失控,但它依然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既不是外來物,也不是退役的衰老細胞,因此不會觸發免疫系統發揮免疫作用。艾利森的癌癥免疫療法也被譴責為一個古怪而毫無根據的幻想。
盡管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嘲笑艾利森那稀奇古怪的想法,但艾利森仍堅持自己的看法,并開始尋找癌細胞抵御免疫系統識別的神秘機制。
20世紀70年代,艾利森對T細胞(一種免疫細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認為T細胞是可以識別并殺死癌細胞的,但是他的老師比爾曼迪教授卻告訴艾利森,他并不相信T細胞對癌細胞的作用,這反而使得艾利森對T細胞更加上心。
當時,人們僅僅知道T細胞可以識別外來入侵者的抗原(外來物的特殊蛋白質)并殺死外來入侵者,但關于T細胞是如何識別外來侵入者的抗原,以及為什么它無法識別癌細胞,仍然無從知曉。為了了解T細胞,艾利森研讀了所有他能找到的關于T細胞的論文。
當時關于T細胞如何識別抗原有一個非常合理的理論:T細胞表面上有一種由特定蛋白質組成的、延伸出來的受體,它能識別某種特定抗原。當抗原和受體相匹配時,T細胞就會啟動,并攻擊產生這種抗原的入侵者(目前認為,抗原呈遞細胞(APC)是一種可以提取和傳遞抗原的細胞,其中就包括DC細胞。抗原呈遞細胞可以加工處理抗原,T細胞上的受體可以識別這種抗原,進而被激活)。雖然理論很合理,但從來沒有人發現過T細胞上的受體,如果真的找到它,將是科學界一次巨大的突破。艾利森立志要成為第一個找到這種受體的人。
1982年,艾利森寫了一篇關于T細胞受體的突破性文章,講述了T細胞上一種疑似受體的蛋白質。但艾利森受到了質疑,沒有一本專業的一流期刊愿意發表他的研究成果。最后,艾利森只得在一本新雜志上發表。文章發表后,艾利森的實驗被其他科學家證實,這位長期受到質疑的年輕學者也終于在科學界嶄露頭角。
合作鑄就成功
嶄露頭角的艾利森得到了資金和一個獨立的實驗室,這也是他下一個里程碑的開始。
20世紀80年代中期,科學家們對T細胞有了更深層次的了解,他們發現T細胞的啟動機制更加復雜:T細胞像是一臺微型汽車,抗原與受體匹配,就像鑰匙插入汽車點火開關能發動汽車一樣,但只有同時踩下油門,汽車才能前進,T細胞也是一樣。
1988年,艾利森的研究團隊證明T細胞的“油門”實際上是其表面上一種叫CD28的分子。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他們發現,即使有了油門,汽車也不一定前進,當T細胞有了匹配的抗原和CD28分子后,也不一定激發攻擊狀態。艾利森認為,肯定存在另外一種分子,阻止了T細胞的行動,就像汽車剎車一樣。
那么阻止T細胞行動的分子,即汽車的剎車在哪兒呢?這時,艾利森的實驗室迎來了一名叫馬克斯·克魯梅爾的研究生,他發現這可能是T細胞受體的另一種分子——CTLA-4。
最初,克魯梅爾觀察到,含有CD28和CTLA-4的T細胞都很活躍。因此,他認為CTLA-4可能是另一種“油門”。但艾利森提醒他:“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汽車動起來,一種是踩油門,一種是松開剎車。”克魯梅爾猶如醍醐灌頂,又開始反復研究,最后終于得出結論:CTLA-4實際上是一種“剎車”分子,由于有了這個“剎車”分子,T細胞進入了“休眠”狀態,無論怎樣都不會啟動。
結合了克魯梅爾的實驗記錄,艾利森假設癌細胞可能進化出了能激活CTLA-4分子的抗原,阻止了T細胞的啟動。
克魯梅爾除了發現CTLA-4是一種“剎車”分子外,還研制出了阻斷CTLA-4的抗體。艾利森和研究團隊將這種抗體注入患癌小鼠體內,發現只要利用抗體阻止了CTLA-4的活性,患癌小鼠就會被治愈,這說明癌細胞只要沒能激活CTLA-4這種“剎車”分子,它就阻止不了T細胞的啟動,啟動了的T細胞就可以殺死癌細胞。
艾利森經過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終于在2010年開發出了作用于T細胞的新藥。臨床試驗結果表明,這種藥能顯著延長一些癌癥患者的生命,療效也很長。艾利森沒有用手術刀、放射線或有毒化學物質,而是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統拯救了患者,癌癥免疫療法也成為癌癥治療的第四大支柱。
在艾利森研究癌癥免疫療法的過程中,雖然獲得了信任和合作,但也遭遇了很多質疑和困難。無論遇到什么,他都堅持自己的看法,并為此付諸行動。像艾利森這樣對事物充滿好奇、遇到困難不屈不撓的人,才能突破傳統科學,讓普通人聆聽科學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