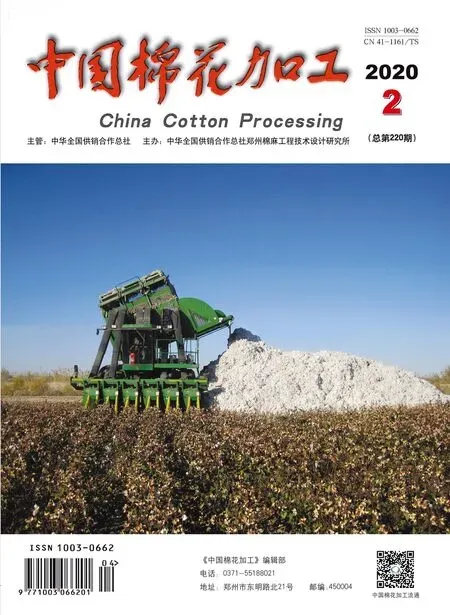淺談棉農增產增收措施
〔塔城地區纖維檢驗所,新疆烏蘇833000〕
前言
這個春天異常特殊,脫貧攻堅本來就是一場硬仗,突如其來的疫情又帶來了新的困難和挑戰!作為新疆民族聚集地的一名駐村干部,如何與村鎮領導一起,帶領村民在現有條件下穩脫貧、真增收,成為擺在眼前的一項實實在在的課題。
一、所在鄉村的概況及現狀
鐵木真蒙古民族鄉是一個少數民族聚集地,該鄉成立于1984年,全鄉總人口5 220人,由漢、蒙、回、哈、維、東鄉六個民族組成。該鄉位于天山北坡,烏蘇市區以西45公里處,奎賽高速公路和313國道并行從鄉村北部穿過。
截至2019年底,鐵木真蒙古民族鄉行政區域內有可耕地3 400 hm2(5.1萬畝),農業人口4 800人,全鄉轄9個行政村。目前,鐵木真蒙古民族鄉年人均收入1.6萬元,在烏蘇市處于中等水平,村民的主要經濟來源為畜牧業,所占比例達30%,農村活羊存欄數達到3.3萬只,可以說家家有養殖,其中500~1 000只的中大戶占到70%。種植業以棉花、番茄、玉米為主,棉花種植占60%,其余番茄和玉米各占20%。
鐵木真蒙古民族鄉下轄地區9個行政村,可耕地達到3 400 hm2(5.1萬畝),棉花種植用地約為2 666.67 hm2(4萬畝),比例達到78.43%;棉花平均產量為5 250 kg/hm2(350 kg/畝),在烏蘇處于中等偏下水平。簡言之,鐵木真蒙古民族鄉農民用近80%的土地帶來了不足50%的經濟收入,這主要是因為鐵木真蒙古民族鄉靠近山區,9個村隊中除了4隊、5隊、8隊和9隊土地相對略好外,其余均為石頭地或沙梁子地(占到近60%),而且大多是零散地塊,比較大的也就在1.33 hm2~2 hm2(20畝~30畝)。由于地不好且零散導致種植收益偏低,因此,鐵木真蒙古民族鄉農民大多采取把土地轉包出去的形式種植棉花。烏蘇市烏伊公路以南(含鐵木真蒙古民族鄉)土地上繳提留為3 000元/hm2(200元/畝),轉包費4 500元/hm2~10 050元/hm2(300元/畝~670元/畝),轉包土地多用來種植棉花。農民以此來獲得國家對棉花種植補貼和轉包土地的差價來增加收入。
顯然,鐵木真蒙古民族鄉農民在棉花種植方面的提質增效和增產增收迫在眉睫。
二、棉花種植及質量現狀
(一)棉花種植、產量等情況
2019年塔城地區棉花種植面積約為24.33萬hm2(365萬畝),涉及28 711戶基本農戶、4 207個農業經營單位。烏蘇沙灣轄區棉花種植面積為23.53萬hm2(352.96萬畝)(其中烏蘇11.58萬hm2、95%機采棉,沙灣11.95萬hm2、100%機采棉)。烏蘇、沙灣2020年種植面積都比2019年減少了1 333.33hm2(2萬畝)左右,主栽品種是新陸早67、新陸早45,搭配品種為新陸早70、新陸早83號等。
2019年由于水價、農資、土地承包費等價格上漲(1 500元/hm2~3 000元/hm2上漲到4 200元/hm2),棉花種植成本比2019年略有提高。機采棉成本價格在23 250 元/hm2(1 550 元/畝),手摘 棉成本 價 約為34 500元/hm2(2 300元/畝);2020年塔城地區棉花平均 產 量5 700kg/hm2~6 000kg/hm2(380kg/畝~400kg/畝),個別地區如烏蘇鐵木真鄉的石頭地、沙梁子地產量在5 250kg/hm2(350 kg/畝),但烏蘇車排子鎮因土地肥沃、積溫高、品種好(魯研棉24),畝產能達到6 750kg/hm2~7 500kg/hm2(450 kg/畝~500 kg/畝)。
(二)棉花收購、加工情況
2019年7月和8月天氣持續高溫,干熱風對棉花坐桃產生不利影響。9月10日前后噴施落葉劑后未出現高溫天氣,致使棉桃未能按照預期依次開放,到10月中旬籽棉出桃開花率才到達60%左右。通過走訪企業了解,正常開秤收購期間為9月25日,因特殊情況實際開秤時間在10月8日左右。因為2019年采棉機數量增加,所以塔城地區棉花出現“集中開放、集中采摘、集中拉運、集中交售”情況,棉價較2018年低迷。棉農紛紛表示,“2019年棉花產量和收入與2019年持平已經是非常好的了。”
據了解,南疆棉花加工企業手摘棉43.2%衣分收購價為5.62元/kg,如果折成40%衣分,收購價為5.3元/kg。尉犁縣某加工廠40%衣分,收購價為5.5元/kg;奎屯地區手摘棉收購價在6.1元/kg~6.3元/kg。
(三)棉花儀器化公證檢驗情況
近兩年,所屬專業技術機構塔城地區棉花儀器化公證檢驗的數量和質量逐年提升。2017年度棉花儀器化公證檢驗歷時6個多月,公檢量達到192萬包、7 873批、43.36萬t。2018年度棉花儀器化公檢歷時10個月共對130家棉花企業、228.2萬包皮棉實施包包檢驗,年度檢驗量達到51.4萬t,同比增加19%,再創歷史新高。從入庫公檢的皮棉指標來看,2018年度棉花指標優于2017年:長度28 mm、29 mm、馬克隆值B2、白棉三為主,所占比例均在78%~80%。棉花檢測相符率為長度70.6%、整齊度82.4%、斷裂比強度77%、馬克隆值80%、Rd(反射率)值79.5%、+b(黃度值)90%、軋工質量98%,上述綜合指標相符率在全國同類實驗室名列前茅,各項指標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18年度烏蘇實驗室每天檢驗量在140批左右,5 000多t。2019年塔城地區經自治區發改委公示的新體制棉花收購加工企業一共有138家,轄區棉花儀器化公證檢驗因采摘、收購、加工時間都比較集中,專業纖維檢驗機構新購進了2臺當今世界最先進的美國進口大容量棉花快速檢測儀,使得塔城地區唯一一家專業纖檢機構的棉花每日檢驗量可以持續在6 000 t左右。
2020年1月~3月,塔城地區棉花儀器化公檢皮棉3.5萬t、15.5萬包、950批,累計2019棉花年度檢驗皮棉48.48萬t、215.9萬包、11 600多批,檢驗總量位居全國第4,檢驗效率同比提高5%,檢驗質量同比大幅度提升。目前,中國纖維檢測中心已隨機抽檢樣品11 600余包,抽檢相符率各項指標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整體檢驗抽檢相符率位居全國第三。
塔城地區纖檢所為企業提供科學、公正的檢驗數據,在商品交易中提供強有力數據支撐。塔城地區138家棉花加工企業中大部分在春節前就徹底結束了2019年度的加工,目前約有10家企業尚有少量籽棉庫存。受2020年春節疫情影響,棉花收加企業復工復產延遲,塔城地區纖維檢驗所在3月15日正式開始檢驗,據統計剩余皮棉檢驗量約在1.5萬多t,2019年整體檢驗量可達50萬t左右,2019棉花年度公檢工作預計在2020年4月底結束。
三、當地棉花優質高產的制約因素
隨著近年來棉花質量監督工作和棉花儀器化公證檢驗工作的不斷加強,一些長期困擾我們的棉花質量問題,如在棉花中摻雜使假、以次充好、使用“兩小一土”設備違法加工棉花等現象基本已經消除,棉花質量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然而,一些長期以來影響當地棉花質量較為突出的問題仍然存在,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是制約棉花質量水平進一步提高的主要問題。
(一)土地零散、土壤肥力低下,嚴重影響棉花產量
棉田土壤的理化、生物屬性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棉花的產量和品質。土壤水分、養分、溫度、空氣、鹽堿含量、質地等均對棉花生長有很大的影響。
鐵木真鄉位于天山北坡最南邊的村子,距離山區不足兩公里,9個村隊2 666.67 hm2(4萬畝)土地中石頭地、沙梁子地占到近60%,土壤沙性大,肥力低下、保水保肥性差。棉花種植后,前期發展進度緩慢,中期易旺長,后期易早衰,這都影響棉花產量的提高。由于鐵木真鄉棉田多為開墾地,大多是零散地塊,比較大的地塊也就在1.33 hm2~2 hm2(20畝~30畝),嚴重制約了棉田的機械化操作,棉花生產規模化、現代化水平有待提高。
(二)棉花品種多、繁、雜,影響了棉花優質高產
近年來,隨著棉花種子市場的放開,棉種市場的競爭愈演愈烈甚至達到白熱化的程度,各種棉花品種紛紛走向市場造成棉種多、亂、雜的現象。據不完全統計,鐵木真鄉種子銷售站有20余家,銷售棉花品種以新陸中26、新陸中36、中棉40、中棉43、魯棉系列等畝產高、衣分高的主栽品種多達十五六個,各種試驗種植、繁育的品種不下幾十個,嚴重影響了棉花生產的健康發展,影響了棉花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影響棉農增產增收。
(三)棉田殘膜污染嚴重造成耕地質量下降、作物減產
自20世紀80年代地膜覆蓋技術引入新疆棉花種植以來,地膜覆蓋以其增溫保墑、抑制雜草生長、增加農作物產量等特點被廣泛應用于棉花種植,但是該技術在帶來顯著經濟效益的同時,大面積的地膜使用也造成新疆棉田嚴重的白色污染。新疆棉花種植的覆膜率已經達到100%,2019年鐵木真鄉棉花種植全部采用地膜覆蓋技術。
由于地膜持續使用,殘留地膜回收率低,因此,土壤中殘膜量逐步增加,造成土壤結構被破壞、耕地質量下降、作物減產等一系列問題。同時,隨著機采棉收獲過程中,大量地表、棉株上的碎膜摻雜在原棉中在加工過程中難以清除,嚴重影響了紡織產品的質量,殘膜污染嚴重影響自然環境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白色革命”變成了“白色污染”。
(四)棉農存在小我意識,容易固步自封
鐵木真鄉鄉政府也曾為提高棉花產量聘請有經驗的技術專家來村隊指導,但當地棉農有許多曾為牧民,存在一定的小我意識,總覺得自己做的已經足夠好,對管理標準化管理、科技化種植不認同,不愿意接受新鮮事物,有時候覺得把土地轉包出去,拿上轉包費、國家棉花種植補貼就很滿意了,而不愿意嘗試冒險去想辦法提高棉花產量和質量。
四、提高棉花質量的對策和措施
(一)選種打基礎
建議專業纖維檢驗機構至少用三年時間對5~10個可繁育性品種做監測,采取收購前監測播種、施肥、打頂等各工序,收購后按指標分類堆放、加工,然后將監測數據利用大數據平臺對比、分析,積累數據,挑選出適合當地土壤、氣候及棉農種植習慣的棉種,從基礎上提高棉花一致性。
(二)種植降成本
以基層鄉、鎮為主體,積極引導有條件的棉花種植戶成立合作社,使棉花種植從小片土地向大片土地,從人工結合機械種植、管理到以機械種植、管理為主,人工為輔過渡,最終實現規模化、機械化種植、管理。積極采用先進的種植管理技術,不斷提高棉花單產,促進棉農增收。
可以借鑒烏蘇市西湖鎮大灣村土地競標流轉的方法,通過互換整合的方式整合土地,促進農業集約化發展。通過鼓勵村民成立合作社,讓合作社和企業參與到土地管理中來的方式,推進土地集約化,進一步降低成本,增加農民收入。村民可以將自己的零散土地通過全村競標的方式發包出去,如此以來不必擔心年成不好虧本,想出去打工或給包地的老板打工都可以,不但地里有穩定的收入,而且能掙第二份錢,比自己種地賺得多。
為順利推進土地流轉工作,一方面用大量事實和數據向老百姓分析土地分散經營的風險和土地整合、土地流轉的好處;另一方面與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就怎樣包地能讓雙方達到利益最大化進行協商,取得了共同的意向后再進行招投標。同時,村委會可以組織村民開展廚師、農機具、電焊、刺繡等技能培訓,切實做好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勞動力的二次增收。
(三)推廣液態膜和降解膜
目前,當地棉農常用的地膜為9元/kg~12元/kg,技術站推廣的可降解地膜為30元/kg,國家補貼20元/kg。但是,當地棉農對可降解地膜使用效果和使用后補貼發放均存在質疑,從而造成可降解地膜推廣慢的現狀。工作隊員與村隊干部可積極做好可降解膜的推廣使用,促進棉農植棉觀念和模式的改變,使棉農從思想根源上認識到實施無膜棉技術種植或使用可降解膜是一項長期效益工程。同時,要讓棉農切切實實感受到,通過揭膜還能夠提高機采棉品質,有效處理利用殘渣廢膜也可以提高來年耕地的利用效率,從而促進棉農采用適期揭膜技術,使液態膜、降解膜逐步得以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