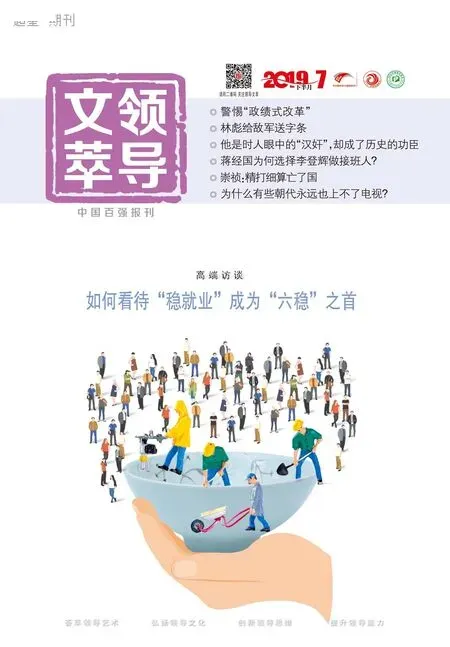素人政治緣何方興未艾?
和靜鈞
素人政治的興起,是國際社會求變的強烈信號,至少近一段時間之內,會延燒開來。
近期舉行的烏克蘭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中,按民調顯示,喜劇演員澤連斯基支持率高達73.3%,大幅領先于尋求連任的現任總統波羅申科。波羅申科承認敗選,并向澤連斯基表達祝賀。
五年前“巧克力大王”波羅申科當選總統,可謂烏克蘭素人政治“第一波”,波羅申科是在2004年“橙色革命”爆發后崛起政治大佬尤先科、季莫申科及2014年陷入烏克蘭危機被民眾無情拋棄的資深建制派人物亞努科維奇之后,走上國家權力第一線的人物。他雖然短暫在政府中擔任過要職,但他的身份仍然是有政治熱情的糖果公司福布斯榜上的億萬富翁,是根深蒂固的腐敗政治系統的局外人。他的面孔是新穎的,與傳統的政治家密室權謀、為政黨利益而鉤心斗角所具有的丑陋形象不一樣,被視為解構和改變的希望。而今天澤連斯基的當選,應屬于繼續在烏克蘭盛行的素人政治“第二波”,民眾一方面對“第一波”人物的施政表現失望,另一方面又重申了對素人政治的肯定及對建制政治的厭惡,再次把毫無政府工作經驗的影視明星推上了總統寶座。他們不是鬧著玩的,他們是認真的。
素人政治的興起,是近幾年來的特有現象。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及之后向歐債危機的遷延,和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的出版,幾乎是這一時代新思潮降臨的序言。西方社會中產階層的萎縮,社會財富分配懸殊,貧富分化嚴重,從美國風靡一時的“占領華盛頓”運動及不依不饒的法國“黃背心運動”上可見一斑。傳統的權力模式正受到民眾的嘲笑,民粹思潮在網絡社交空間上泛濫,它們已經結合成了一股解構力量,重構政治權力,重新定義政治人物,“素人做得不會差”的觀念,已經在選民意識中確立。
素人政治的時間稍遠點可以從印度的莫迪算起,再遠點甚至可以追溯到德國默克爾的崛起。不論是莫迪,還是默克爾,在傳統的選舉政治中他們是不起眼的,莫迪相較于背景濃厚的國大黨權貴家族,來自東德的默克爾比起西德原政治勢力,他們都幾乎不可能有獲勝的機會,但是他們,贏得了最后的勝利。以默克爾為例,她應該是自冷戰結束以來德國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
但不論是莫迪還是默克爾,他們算在“政治素人”行列中的主要原因,是他們相較于那些被傳統和腐敗雙重蝕化的資深建制派政治人物來得干凈與稚嫩,但他們走上國家第一權力中心之前,也算是頗有成就的政治家了,所以,他們的成功,準確地說是“半素人政治的成功”,是反傳統、反精英的初步勝利。
特朗普的當選,是素人政治在西方發達國家里正式現實化的標志性事件。今天,在意大利,有“五星運動”興起而誕生的“教授總理”,一個教書先生,一轉身就成了政府總理,就像烏克蘭的澤連斯基在《人民公仆》劇中扮演的歷史教師瓦夏一樣。在巴西,受盡了資深政治領袖們如盧拉、魯塞夫、特梅爾等人的腐敗行為之害,并把這幫政治領袖一一送進監獄后,選民干脆以非常高的支持率,選擇了政治素人博爾索納羅擔任總統。2019年3月底,幾乎沒有從政經驗的單親母親蘇珊娜卡普托娃贏得了58.3%的選票,成為斯洛伐克首位女總統。
素人政治也并非就是選庸才政治。素人政治中脫穎而出的人物,往往更擅長使用社交媒體,有出眾的辯論和演說能力,競選綱領上更接地氣,更接近中下層民眾的疾苦,他們本身就是素人面孔存在的精英人物。當然了,素人們要是做不好,任期一到,也會無情地被新的政治素人或被別人代替。素人政治的興起,是國際社會求變的強烈信號,至少近一段時間之內,會延燒開來。
(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