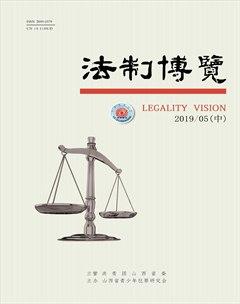中國存托憑證法律制度研究
摘 要:中國存托憑證最早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被提出用于當時香港“紅籌股”公司在內地資本市場上市進行融資,但最終因各方面機制不夠完善而未能推出。2018年6月6日晚間,中國證監會正式發布實施《CDR管理辦法》,給中國存托憑證的發行與交易等行為提供了相應的制度指引。中國存托憑證的試行有利于拓寬境內投資者的投資渠道,還利于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但是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的缺陷及外匯管制的限制,CDR的運行制度與監管制度均有待于進一步的完善。
關鍵詞:存托憑證;中國存托憑證;CDR
中圖分類號:D922.28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9)14-0131-02
作者簡介:熊超(1993-),男,漢族,重慶人,重慶工商大學,研究生在讀,金融法專業。
一、中國存托憑證試行法律制度所存在的問題
(一)主體法律關系制度的障礙
依據《管理辦法》的規定:“存托憑證持有人依法享有存托憑證所代表的境外基礎證券的權益,并且按照存托協議的約定,通過存托機構行使其所享有的權利。”而《管理辦法》在第20條中規定如何適用我國《證券法》關于股東信息披露義務時,使用了“持有或者通過持有境內外存托憑證而間接持有境外基礎證券發行人股份的投資者”的概念。結合上述一系列規定可見,存托機構僅僅是境外基礎證券的名義持有人,投資者作為CDR持有人才是該基礎證券的實際權益人,存托機構與CDR投資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屬于“代持關系”。另一方面,《管理辦法》在第31條第1款中規定存托機構與托管機構應當忠實勤勉地履行各項職責與義務;第32條又規定存托機構應當將存托憑證的基礎資產單獨立戶,將自有資產與存托憑證的基礎資產有效隔離。此等信托法概念又將存托機構與投資者之間的法律關系解釋為“信托關系”。因此,現階段我國存托憑證相關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究竟屬于代持關系或信托關系有待進一步明確。
(二)投資者爭議解決機制的困境
我國證券投資者集團訴訟制度的困境。我國在1991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了兩種代表人訴訟,且均屬于加入制集團訴訟。①由于我國特殊的大環境以及人民法院排斥證券集團訴訟的司法政策②,我國到目前為止沒有通過代表人訴訟處理的證券集團訴訟案件。③有學者認為,雖然目前證券領域代表人訴訟制度的運行不成熟,但其在民事及行政訴訟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集團訴訟”性質的代表人訴訟制度的預期效果也可能隨著法治的健全日益顯示出其特有的法律價值。④鑒于此,有學者提出需要引入“退出制”⑤的證券集團訴訟制度,以規范上市公司企業行為并加強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⑥
(三)基礎財產破產隔離的困境
《管理辦法》明確規定,存托機構應當將中國存托憑證的基礎資產單獨立戶,將其自有資產與中國存托憑證的基礎資產有效隔離。這與我國《信托法》第十六條有關于信托財產破產隔離的規定不謀而合。所謂破產隔離,是指在信托財產委托人或是受托人在到期不能償還債務或是破產時,受益人仍然能夠就該部分財產保持其受益的權利,可以對抗委托人及受托人的普通債權人。依據前文分析可知,基礎證券是否具有信托財產屬性仍然缺乏相關法律制度進行明確。《管理辦法》規定由存托機構代表CDR投資者對境外基礎證券發行人行使權利,因此存托機構是CDR基礎證券的實際持有人,所以該基礎證券及相應的財產利益在法律意義上屬于存托機構的財產范圍。
(四)CDR與基礎證券相互轉換的障礙
CDR與基礎證券能相互轉換是中國存托憑證發行交易機制得以正常運行的前提條件。而在我國目前不允許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進行自由兌換的外匯管理體制下,CDR與境外基礎證券之間能否自由轉換以及通過發行CDR所融得資金能否匯兌出境便成為了目前運行CDR所存在的現實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境外基礎證券與CDR之間的轉換問題在證監會《管理辦法》中也并未得到有關條例的明確指引,僅僅在《管理辦法》第八章附則第五十七條中籠統地表述到:“中國存托憑證與境外基礎證券之間的轉換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中國存托憑證的不可轉換模式將減少CDR與基礎證券之間的聯系并造成境內資本市場與境外資本市場相互割裂的局面,進而導致CDR與基礎證券之間出現流動性風險以及較大的折價或溢價的風險。
二、美國存托憑證(ADR)的制度分析與借鑒
(一)主體法律關系制度
雖然關于美國存托憑證法律關系屬于何種性質在學界仍有不少爭議,但大部分學者的觀點均認為存托憑證法律制度基本上符合信托制度的構成要件。筆者同樣認為存托憑證法律制度就是在現代信托制度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但是存托憑證法律關系制度的基本結構與一般的信托制度基本結構又存在一定差異。普通的信托法律關系是基于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的信任關系而建立的,委托人將信托財產轉移登記于受托人名下,并由受托人以其自身名義處理信托財產項下的事務而不得委托其他主體代為進行處理。但在存托憑證制度中,存托機構作為信托關系的受托人還將與托管機構簽訂保管協議,將原本由其占有、管理、處分的信托財產委托于托管機構進行保管,這種“經營與保管相分離的原則”與一般的信托法理論相背離。但經營與保管的相互分離對一般的信托理論與實踐均不存在沖突,僅僅是增加了托管機構作為信托關系項下的受托人。綜上,美國存托憑證法律制度的基礎結構仍然是一個包含涉外因素的信托結構。
(二)投資者糾紛解決機制的成熟
證券集團訴訟制度。證券集團訴訟,是指由單個或部分投資者代表全體被侵權的投資者,以集團的形式向法院提起民事侵權損害賠償的訴訟行為。該制度有以下幾個優勢:第一是便于中小投資者集中力量維護權益。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中小股東分散性較強,訴訟成本的高昂與特殊的證券市場環境不利于個人小股東維權,而證券集團訴訟便把各中小投資者集合起來共同維護權益。第二是證券集團訴訟的舉證責任與一般民事訴訟程序中“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不同,美國證券法將證券民事訴訟程序中的證券欺詐侵權行為歸為特殊侵權行為的種類之中,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三)基礎證券的破產隔離機制
基礎證券由存托銀行實際占有,ADR投資者僅能通過存托銀行間接占有、通過存托銀行獲取紅利或股息。當存托銀行破產時未將紅利支付給ADR投資者時,ADR所代表的那部分財產則屬于存托機構的財產,可以受到破產財產清算以及債權人的追索。因此,美國存托憑證制度依據信托法律制度中的信托財產獨立性原則實現基礎證券及ADR的破產隔離。信托財產獨立性原則在制度上要求存托機構與托管機構必須將信托財產與他們自己公司的所有財產相互隔離,也即是將ADR和基礎證券作為獨立于存托機構與托管機構自有財產以外的財產,從而分別管理、分別記賬。另外,對于不同基礎證券所指向的ADR仍應當用不同的賬戶分別管理、分別記賬。此外,存托機構與托管機構在實踐中簽訂關于基礎證券的保管協議時也會約定托管機構必須將自有財產與基礎證券分開保管,具體由存托機構在托管機構開設一個專用賬戶對基礎證券進行管理,托管機構不得擅自處分該基礎證券賬戶的任何財產。
三、完善中國存托憑證法律制度的建議
(一)信托法律關系的構建
完善相應規定以采用信托法律制度的模式來構建CDR法律關系制度,并將存托協議的法律性質定性為信托合同。盡管信托法律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國家,但我國也于2001年首次頒布實施了《信托法》,該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信托,是指基于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的信任關系,委托人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受托人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對信托財產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本質上可將存托憑證視為是一種信托憑證。此外,在實踐中我國已經引入了證券投資基金,其同樣是一種以信托制度為基本法律結構的金融衍生工具,并且已經在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中賦予了證券投資基金中所指向的信托財產的獨立性并確立了信托財產經營與保管相分離的原則。由此可見,中國存托憑證法律制度的構建可以適當借鑒證券投資基金的制度構建。但鑒于CDR較強的涉外性,立法機關在制定其理論制度與具體實施制度時應更加完備。
(二)投資者糾紛解決機制的完善
推進證券投資者集團訴訟制度建設,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首先,通過立法或國家層面的認可切實推進證券集團訴訟制度的建設,讓證券集團訴訟為投資者利益提供救濟渠道。其次,可以效仿現有的知識產權法院,在證券交易所所在地設立專門法院或法庭對證券集團訴訟案件進行統一管轄。國家的重視程度高有利于建立一支審理證券案件的高水平法官隊伍,便于和專業的證券交易所進行溝通、獲取審理案件所需的材料,也利于將分散于各地的投資者集中起來、實現案件的統一審理,最終達到維護各中小投資者權益并節約法院訴訟資源的目的。
(三)構建CDR與基礎資產的破產隔離制度
通過完善信托財產獨立性原則構建破產隔離機制。目前,我國信托財產獨立性原則的規定仍存在一些不足,應當完善委托人與受托人共同承擔的關于信托財產公示的義務。此外,還應明確基礎證券及其衍生利益不屬于存托機構的破產財產,強調該部分權益不受破產清算及債權人的追索。完善信托財產的獨立性原則利于《管理辦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得以實施,在理論上支持存托機構將中國存托憑證的基礎資產單獨立戶,將其自有資產與中國存托憑證的基礎資產有效隔離、分別管理并分別記賬,以達到實現破產隔離的法律效果。
(四)外匯管理制度的完善
逐步允許CDR與基礎證券在一定限額內的雙向自由轉換。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將會有更多在境內沒有實體運營企業的境外基礎證券發行公司有意愿在我國境內發行CDR以達到融資的目的。因此,當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較為成熟以及CDR試行效果良好時,進一步允許CDR與基礎證券在一定限額內的雙向自由轉換。一定限額內的雙向自由轉換利于平抑CDR與基礎證券之間的價格,防止兩者價格的異常波動;設置一定的額度還利于監管機構對其進行控制,避免出現資本與外匯的大量外流。
[ 注 釋 ]
①加入制集團訴訟,是指一個潛在的集團成員為了稱為集團的一員,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采取措施肯定地參加集團訴訟,并承擔在共同的問題上受到判決或和解的后果,以此作為從集團訴訟中獲益的前提.
②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對于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人民法院應當采取單獨或者共同訴訟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團訴訟的形式受理.”
③章武生.我國證券集團訴訟的模式選擇與制度重構[J].中國法學,2017(2):286.
④肖鋼.我國大陸資本市場監管執法面臨的形勢和挑戰[J].求是,2013(15).
⑤退出制,是指默認所有相關成員稱為集團成員,如果不想受到生效裁判的約束則必須明示退出.
⑥章武生.我國證券集團訴訟的模式選擇與制度重構[J].中國法學,2017(2):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