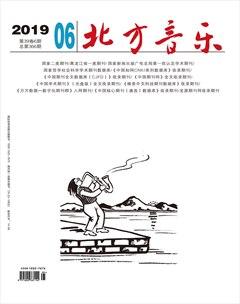華鎮音樂美學思想研究
張軍
【摘要】華鎮,號云溪居士,有《云溪居士集》殘本傳世,為北宋中期的著名文人。通過考證,《云溪居士集》中有大量音樂著述資料,有書、劄子、論等多種文體,體現出華鎮對于古代音樂發展、宋代雅樂建設需繼承先秦禮樂制度與音樂對于教化之用等觀點。
【關鍵詞】華鎮;《云溪居士集》;雅樂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一、華鎮與其音樂著述
華鎮是北宋時期的文學家、詩人,有《云溪居士集》殘本傳世。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有“《云溪居士集》,宋華鎮撰,鎮字安仁,防稽人,元豐二年進士,官至朝奉大夫,知漳州軍事。鎮原集本一百卷。”[1]其人主要生活在仁宗至神宗期間,此時正屬于宋朝由盛轉衰時期,社會矛盾日益突出。
華鎮詩文影響頗大,受到當時和后世諸多贊譽。 宋朝樓炤在《云溪居士集原序》中評價其“君之文精深典贍,而詩遒麗逸發,其它眾制爛然皆有體,則非涵養蓄蘊之厚,不能發之如此。”[2]從現存《云溪居士集》《全宋文》等相關書籍中,考其音樂著述有“上侍從書三”“乞頒降州軍大樂劄子”“禮樂論”“樂論上”“樂論下”“《治論上》”“《變論》”等。
除此之外,在華鎮其他文章中,尚有零散音樂的論述。存于《上國子豐祭酒書一》《上蔡樞密書》《上淮東閭提刑書》《治論上》《變論》等文。
華鎮流傳至今的詩文總數并不為少,音樂著述也占了不少的比例。上述圖表和相關文字記載表明華安仁對于音樂著述頗豐,無論篇數還是字數在宋代諸多文人中均不為少。
關于華鎮的相關記載,重點存于《云溪居士集》之中。《全宋詩》《全宋文》等宋代大型總集的編撰,基本保留了華鎮流傳至今的詩文。對于華鎮音樂美學思想研究,這是筆者重點參考的資料來源。對于其人的研究而言,學界關注較少。姜亮夫先生曾有“華安仁(鎮)疑年考”稿本,但可惜已經不見;鄭尚書先生有“華鎮生年考”一文,考證出華鎮生于仁宗皇祐四年(1052)。
二、華鎮音樂美學思想產生與時代背景
宋代市民經濟繁榮,各種娛樂方式盛行,說書、雜技、舞蹈等多種表演形式均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在官方與士大夫之間,仍然以推崇雅樂為主,而且較之隋、唐時期更為崇古。唐太宗李世民對于胡樂、燕樂等仍然堅持兼收并蓄,但在宋朝期間,君主堅持雅樂正統。僅在北宋期間,朝廷就曾組織過六次定律,因此產生了王樸樂、和峴樂、李照樂、阮逸與胡瑗樂、楊杰與劉幾樂、魏漢津樂。華鎮所屬音樂著述以雅樂為主,并未涉及宋代俗樂之事,因此對其音樂思想的分析,要從宋代雅樂發展來看。
自陳橋兵變后,趙匡胤從后周禪讓得到江山。對于江山的正統性,宋朝歷代統治者極為重視,宋代文人也多次發表看法,以“《正統論》”為題的論述文較多。以北宋和南宋時期對于“三國正統”的看法亦可看出,北宋時期,政府與文人一般堅持魏晉正統論;到了南宋時期,以朱熹為代表的士大夫重申“蜀漢正統論”,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極大的關系。這也是導致為什么宋代對于禮樂之事尤為重視,宋代江山由后周禪讓而來,因此特重其正統性。禮樂制度對于標榜一個朝代的正統性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華鎮所處時期以北宋中期為主,此時天下承平已久,國運處于繁盛時期,對于禮樂制度的建設成為國之大事。朝廷多次征召懂得樂律之人參與宋代官方定律。在景祐年間,宋仁宗特下《訪曉雅樂人詔》,言“……如有能曉達古今雅樂,制作法度,及考正鐘律,音調得失,灰琯測候此第,并許稱薦或自經官司投狀,未得發遣赴闕,仰具姓名并所供事狀,候敕到限兩月奏聽指揮。”[3]除此詔外,仁宗時期尚有《博求善候氣及曉律者詔》、《采磬石訪古尺律詔》等。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文人也多談禮樂、定律之事。
在這種環境之下,華鎮也同樣堅守雅樂為上的理念,對于以“鄭衛之音”為代表的俗樂持摒棄觀念。對于宋代市民音樂,對其無相關文字記載。由此可見,在華安仁心中,堅持認為俗樂并不登大雅之堂,不當進入文人士大夫討論范圍之中。
三、華鎮音樂美學思想
華鎮音樂思想,首先便為推崇上古雅樂。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很大關系,前文已有論述。在《上侍從書三》中,所舉之例為舜時的后夔作韶樂、孔子聽韶之事;在《乞頒降州軍大樂劄子》以三代之盛,以雅頌之樂聞于邦國為例,希望將大樂局所制之樂傳及州縣;《禮樂論》中同樣以孔子聞韶而展開述說;《樂論上》中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此六七君子者,皆圣人之徳,據崇髙之勢者也。”[4]進行評析;《樂論下》中用“故云、咸、英、莖、章、韶、濩、武,皆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蕩滌流淫,召集和粹,移風昜俗,鼓舞而不知其所以然。”[5]分析音樂教化之用。音樂著述的主要內容以崇上古雅樂為主。
華鎮音樂思想中最為重要的便是禮樂治國,雅樂具有極為重要的教化之用。在其《治論上》中“進禮樂之教,退刑法之政,暢醇厚之風,懲刻薄之俗,示之以君臣父子之論,風之以孝悌忠順之義,循理者異之,不率者放棄之,則民善矣。”[6]禮樂教化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華鎮在其文章中亦繼承了這種思想,并且是對于治國安民真正提出的解決方案。“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4]音樂可以在潛移默化中規范百姓行為,使其向善,培養仁義忠順等傳統封建社會倫理價值觀念。在歷代王朝中,對于禮樂的重視都是放在極為重要的地步,這也與音樂之用有較大關系。
推崇上古雅樂是否一定要重歸上古禮樂制度。關于這個問題,華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變論》中“昔齊宣王好世俗之樂,孟子謂之今猶古也。夫鄭衛之音與雅頌之音遠矣,孟子引而同之,豈為佞乎?急其本而緩其末也。夫與民同樂者,樂之本;聲容節奏者,樂之末。使孟子進雅頌而退俗樂,則雅頌未必見售,而與民同樂之樂不得明;引而同之,則宣王遂好之矣。”[8]好雅樂,好崇古,最終目的是應與民同樂。聲容節奏是雅樂之末,而非雅樂之本,因此對于官方多次定律而無功之事,華鎮雖未直接批判,但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這與范仲淹《今樂猶古樂賦》觀點相同,“古之樂兮所以化人,今之樂兮亦和民。在上下之感樂,豈今昔之殊倫?”[9]在當時北宋雅樂多次定律大背景之下,大多數文人均有關于音樂的討論,對其觀點還是有所爭議。較為正統與主流的一方,是站在經書之中,逐句考證,妄圖恢復到上古禮樂。但也有部分文人重點看到音樂之用,而非音樂之體,只要能夠達到教化百姓目的的音樂均是雅樂。華鎮便是這一派的代表。
華鎮的音樂美學閃光點在于重點看到音樂之用,雅樂之用。雅樂不是只在官方呼喊的正統口號,更應利用上古禮樂制度,充分發揮音樂教化百姓之能,將所制雅樂積極推行,建立太平社會,達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空泛地繼承上古禮樂,并不能真正使得國家安定,音樂之用是禮樂制度的核心,只有官方與百姓真正與民同樂,那么禮樂制作才真正更有意義。在崇古的外衣之外,更應看到今樂的價值,因此可以說華鎮并不是一個復古主義者,在音樂思想領域,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宋代官方對于雅樂的重視,造成這個時期多數文人對于音樂之事的積極參與,在客觀上亦推動了中國雅樂本身的發展。華鎮作為其中士大夫談論音樂的代表,從中可以看出對于雅樂的積極看法和現實意義。士大夫廣泛地參與此事,對于宋代禮樂制度建設而言也提出了諸多可供實踐的意見,雙方的互動從另一方面推動了宋代禮樂制度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永瑢.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
[2]司義祖校點.宋大詔令集[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曾棗莊,劉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4]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